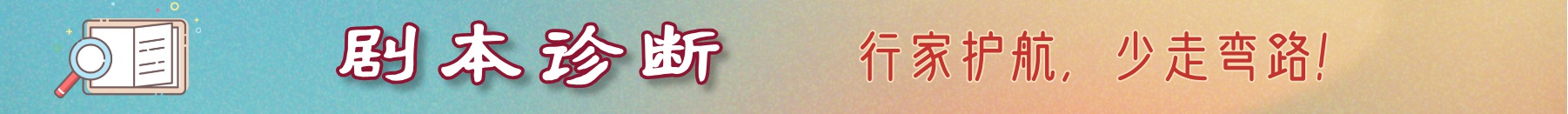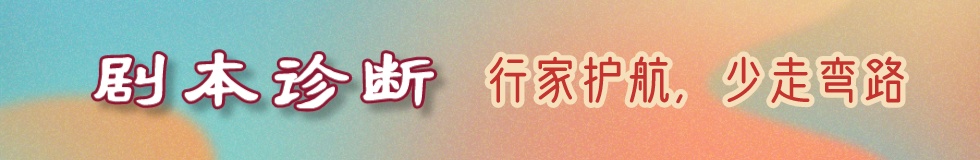权属:原创
字数:4930
阅读:4533
发表:2020/3/15
其他作品
朝鲜,那段值得记忆的日子-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军62周年之际
引 子
时间的指针刚刚指向凌晨四点,班长一声令下,我们十几位战士,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背包,像猫一样摸黑沿着已经走得烂熟的羊肠小道下山了。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三八线非军事区一个叫北阳线出入口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已经汇集了从各哨卡撤下来的战友们。 吃过自身携带的干粮,坐上排着长蛇阵的卡车, 一路向东,迎着初升的太阳,浩浩荡荡踏上了归国之路。 此时的时间,定格在1958年3月15日早晨八点整。
62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段亲身经历,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是留恋,还是自豪?说不清楚,抑或兼而有之吧!
人的一生走过很多的路,有上坡,也有下坡。 有直道,也有弯道。 然而,一段特殊的路程,总是令人永生难忘。 这就是今天本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军62周年之际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
前线的召唤
1957年11月初的一天,连里突然通知我去一个叫做” 民警大队”的单位报到。 到那儿才知道,这是一个直属于驻朝陆军第23军派驻在三八线非军事区我方一侧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 既然是部队,为什么叫”民警”?这您得去问志愿军总部了。
由于是在直面敌人的环境下执行任务,调入这个部队的人,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个头要在1米7以上,二是长相要好。 穿戴上: 所有成员,上身都是四个兜的军官服,下身马裤马靴,再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很是威武。 武器配备: 每人一支刚出厂,国内外我军所有部队均未装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那枪新得枪托上的护漆能照出人的眉毛。 有一次下山,一位朝鲜人民军上将,拿着我的枪反复看了足足十分钟,仍爱不释手。 口中不停的念叨: ”好枪,好枪,将来我们也会有的,会有的”。 除此之外,每人还配有五四式手枪一支,匕首一把和四枚手榴弹,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新调入这支部队的人员,要经过两个星期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策纪律教育。 集训期间,我和另外两位战友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这家四口人,老两口,儿子和一个刚过门的儿媳妇。 儿子从军了,我们六个人就挤在这间不大的土炕上。 阿爸吉(大爷或老爸的意思) 为了表示欢迎我们进驻,去的当天便从炕头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土罐子, 从中摸出两块地瓜,放在火盆边上慢慢烘烤起来。 地瓜烤好以后,我们满以为是老两口自己吃,哪知阿巴吉把这两块热腾腾的地瓜,全都放在我们的手里, 用不很熟练的汉语说: “孩子, 吃吧! 这是去年留下来的,留给你们的”。 阿爸吉的话,把原本是两块普通的地瓜,立刻变成了两颗滚烫的心, 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有这种水乳交融的军民情谊垫底儿,我们的军队,没有不打胜仗的理由!
集训的最后一项科目是步枪一百米半身胸环靶实弹射击考核,我打了优秀。 这是入伍近一年来仅有的两次实弹射击考核打的第二个优秀。 第一次是新兵连集训。 我们连一共去了五个新兵,我是唯一1个打了优秀的, 也是入伍仅三个多月,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而获得记录档案的第一次嘉奖。 集训结束后,我留在大队部当通信员。 干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通信员的活,就是每天早晨天不亮,把灌满开水的暖瓶,分别送进大队领导们的家里。 除此,便是坐下来讨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学习。 这多没劲! 于是,我提出去一线哨所的要求。 我的请求很快被批准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坐上去前线送寄养的马车,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在日落前,来到三八线非军事区北阳线入口处停了下来,接着,跟下山接我的同志上山去了。
临津江畔的日日夜夜
为了保密和便于管理,哨所是按照百家姓中的赵,钱, 孙, 李,周, 吴, 郑, 王等百家姓中的姓氏排位作为代号而起的名字。 我所在的哨所是赵庄,作为百家姓中的首姓, 赵庄显然是这支部队中的第一个哨所。 全部成员一个加强班,约20人。
此山不太高,估计海拔三四百米, 但它的战略位置却十分突出。 自山顶哨所往下走,30度左右的坡度,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的临津江边。 一条可以通行车辆的土路自北向南顺江而下,直指200米外非军事区南北分界线的中间线。 一辆被打坏的美军坦克,孤零零地趴在离土路不远的半山坡上, 似乎在告诉人们,当年这里的战斗是何等激烈。 临津江的西岸,刀削般的山峦与英雄阵地马良山主峰紧密相连。 由此可见,此处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山上没有水源,解决用水的唯一办法, 是去山下的临津江里取水,因此,每隔两三天,就得派人去江中取一次水。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这样的活动只能在夜间进行。 到哨所不两天,我便跟随战友们去山下的江中取水。 这是个寒冷的冬季,我们走到江中心, 用钢钎撞开厚厚的冰层,取出冰块放进麻袋里背上山,放进锅里化成水以备生活之用。
哨所每天必须完成的三项任务: 观察哨,巡逻哨和伏击哨。 除此之没有别的活动。 看军犬训练,就成了我们唯一的乐趣。 随着军犬引导员(现在称训导员)的声声口令,这条曾因抓捕越境特务而立过三等功的德国黑贝犬,以它骄健的身姿, 时而跃起,时而狂奔,时而坐卧,时而匍匐。 那敏捷而又有节奏的动作,着实让人有一种快乐和安全感。 不过,也有让人揪心的时候。 三八线里面由于长期无人居住,野生动物较多。 一天夜里,可能受到野生动物的干扰,这只犬连叫了两声,第二天一大早,看到自己的主人手持皮鞭生气的站在犬舍外面,自知犯了军纪,便主动走出犬舍, 蜷缩在地上任主人鞭打。 打完以后,坐起来伸出前爪与主人握了握”手”,此事才算了结。
春节快到了,哨所里过年没法和后方相比,可也总得有所表示呀!于是,班长决定在哨所大门外边搭建一个彩门。 一听说采松枝搭彩门,我一个高跳出战壕,欲到十多米外的小松林里采松枝。 刚出战壕就被班长喊了回来,原来,我的胳膊上没有带黄色袖箍。 班长严肃的告诉我:” 这样出去被敌人一枪打死白白送死”。 说着,便把印有中朝两国文字” 民警” 的黄袖箍戴在我的左胳膊上。 这时我才明白黄袖箍竟是如此重要。 因为它是朝鲜停战委员会规定的,南北当事双方共同认可的合法标志。
就在这天夜里,我们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突然,阵地上传来紧急情况。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全部进入了阵地。 由于平时准备充分,进入阵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平时放在掩体里的一箱手榴弹,搬放在掩体边沿并迅速打开箱盖,将手榴弹摆放在战壕前沿,熟练地打开保险盖,拉出安全绳, 放在眼前随时备用。 一切准备妥当,便静静趴在掩体里观察阵地前面的动静。 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后半夜三四点钟,仍没见对面的敌人有动静,这才决定撤出阵地。
生死一瞬间
在赵庄执勤一个多月后,我被调到了孙庄。 相比赵庄,孙庄的地域相对宽阔平缓。 同样是三项任务,这里负责的面要大一些。 观察哨可一直看到约两公里外著名的老秃山山脚下。 一天,我和一位战友正在哨位上按照规定由左至右,由近到远举着望远镜进行观察搜索,突然发现老秃山山脚下的草丛里有一个黑点在移动。 仔细辨认,发现是一个人。 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班长。 班长核实情况以后,立即向后方作了汇报,并派出一个三人抓捕小组 迅速向事发地出击。 我方的行动,或已被敌方发现,待抓捕小组到达后,敌特已不知去向。 但一位参与抓捕的战友,却在事发地捡到一只”中华” 牌钢笔。
巡逻哨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三个人走在非军事区荒漠的小路上,不时有野猪,狍子和野兔之类的动物从前面跑过,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缺乏生活情调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有趣的调味品吧!
最困难的要算伏击哨了。 天黑出去,一夜要换三四个伏击点,每个伏击点一趴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 别的好说,两三个小时趴着一动不动,这困劲儿一上来哪受得了啊! 刚开始参加伏击,由于心情紧张, 两只眼瞪得比平时大一圈,参加伏击的次数多了,往那儿一趴不到十分钟眼睛就睁不开了。 为了撵走困劲儿,用手掐自己的脸,咬手指头,抓周边的雪擦眼睛, 揉鼻子,往脖子里塞雪块。 总之,能用的招都用了, 还时不时的打个盹儿。 有一次,在幽静的山谷里, 天上静静的飘着雪花,没有一丝风。 为了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我们的羊毛军皮大衣都是毛朝外反穿着。 在掩体里趴了大约半个小时,正困得睁不开眼的时候,在我掩体前面两米多处的草丛里,一只野鸡突然吼叫起来。 在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响声的环境里,这突如其来的叫声,相信几公里之外都能听到,何况这叫声就在自己的眼前。 也正是这一声吼叫,直到撤离阵地之前,困劲儿再也没来过。
还有一次,班长带着我们两个人,在山脚下的掩体里打伏击,刚进入伏击点不久,就听得半山腰荆棘丛中像是有人走动的声音。 于是,班长立刻命令: “打开保险,(我们的枪支一天24小时都上了膛的,打开保险即可击发。 ) 准备战斗! ” 话音刚落,我们三人同时跃出战壕,端起刺刀,排成”一” 字散兵队形,向事发地大步冲去。 搜索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估计是那些该死的野生动物搞的鬼。 由于过早的暴露了自己,只得提前返回营区。 就在我们刚躺下不久,只听房舍后面一阵激烈的搏击声,其间还有动物的惨叫声。 次日早晨一看,原来是一只野生狍子被另一只动物咬掉了舌头,死挺挺躺在房屋后面的小路旁。 这下我们可乐坏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死狍子拎回厨房,全班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俗话说: 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就在我们撤出阵地的前几天,班长带领我们两个战士巡逻回来的路上,在距离营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走在前面的班长突然被一根细麻绳绊了一下,随即,一个拳头大小的铁疙瘩从路边的草丛里滚了出来,班长回头捡起来一看,立刻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这个手榴弹大小的铁家伙,是一颗跳雷。 什么叫跳雷?就是当这颗雷的保险销被拔出以后,他不会立即爆炸,而是从地上跳起一米高再爆炸。 当时,我们三个人是沿着这条小路成纵队行进的,人与人之间的前后距离为三至五米。 当班长被绊以后,到此雷跳起的瞬间,刚好在我眼前爆炸,其后果可想而知。 可为什么这颗雷没有爆炸呢? 一看才知道,由于此雷被放在露天草丛里的时间比较长,插在跳雷手柄上的插销与弹柄孔外缘的接合部有点锈蚀。 尽管如此,保险销仍被拉出四分之三, 仅有韭菜叶宽的一段保险销没被拔出,这一点点没被拔出的保险销,却使我们三个人逃过生死一劫, 真是人不该死天相助啊! 此事, 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
两军友谊 地久天长
志愿军撤军的消息,两天前已经传达到我们的耳朵里,但你看不出每个人脸上的喜悦和激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此以后,很难再有机会守护这片曾经用战友们的鲜血染成的热土了。
一天晚上, 朝鲜人民军一个班前来接访。 两军战友相见,犹如久别的亲人格外热情。在仅有的两天时间里,我们一起上观察哨,一起巡逻,晚上一起伏击。 大家虽然语言不通,肢体语言和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人民军对志愿军的感激之情和对对面敌人的切骨之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下山的头一天,一位人民军战士,把自己身穿军装的照片送给我,用手指了指天, 指了指地,又指着他本人和我,说出 ”友谊”两个字。 哦!我明白了, 他是在说,我们的友谊和天地一样长久。 还有一位人民军战士,他没有自己的照片,却把自己姐姐的照片送给我作永久留念。 这些照片,至今我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相册里。 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
临下山的头一天晚上,班长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和另一位战友把包括一位中校军官在内的约20位人民军人员送到钱庄去,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这是我在三八线撤出阵地之前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
尾 声
3月15日早晨8点,我们的车队准时出发了。 下午3点多钟,车队来到朝鲜东海岸的元山港。 远远望去,人声沸鼎,彩旗飘飘,热闹非凡。 广场中央,高高搭起的舞台上,悠扬的舞曲声声悦耳,让人陶醉。 车队的领导,高声呼喊着要我们下车去跳舞,于是,我们纷纷跳下车去,不一会儿, 便消失在欢乐的海洋中去了。 从这里开始,在一路欢歌一路舞中,我学会了朝鲜民间舞蹈 – - “道拉几”。 也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由乘坐卡车,转乘军用专列 (俗称闷罐子车 ) 一路北上。 3月18日清晨一觉醒来,我们的军列已经静静停靠在齐齐哈尔市东站的铁轨上了。
随着这支部队在中国境内安营扎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光荣称号,也跟着走到了它的终点。
归国以后的民警大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曾经是其成员的我们,又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我被分配到陆军第六十九师师部侦察连。 同年12月30日,同该师另外12位战友一道,共同走进了人民空军长春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的大门。 自此, 这条长达27年的歼击机飞行员之路,一直伴我走到1985年。
再见了朝鲜,我曾经驻守过的美丽国度! ,
再见了三八线,我曾经熟悉过的那片热土!
2020年3月15日追记
时间的指针刚刚指向凌晨四点,班长一声令下,我们十几位战士,背起早已准备好的背包,像猫一样摸黑沿着已经走得烂熟的羊肠小道下山了。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三八线非军事区一个叫北阳线出入口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已经汇集了从各哨卡撤下来的战友们。 吃过自身携带的干粮,坐上排着长蛇阵的卡车, 一路向东,迎着初升的太阳,浩浩荡荡踏上了归国之路。 此时的时间,定格在1958年3月15日早晨八点整。
62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段亲身经历,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是留恋,还是自豪?说不清楚,抑或兼而有之吧!
人的一生走过很多的路,有上坡,也有下坡。 有直道,也有弯道。 然而,一段特殊的路程,总是令人永生难忘。 这就是今天本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军62周年之际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
前线的召唤
1957年11月初的一天,连里突然通知我去一个叫做” 民警大队”的单位报到。 到那儿才知道,这是一个直属于驻朝陆军第23军派驻在三八线非军事区我方一侧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 既然是部队,为什么叫”民警”?这您得去问志愿军总部了。
由于是在直面敌人的环境下执行任务,调入这个部队的人,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个头要在1米7以上,二是长相要好。 穿戴上: 所有成员,上身都是四个兜的军官服,下身马裤马靴,再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很是威武。 武器配备: 每人一支刚出厂,国内外我军所有部队均未装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那枪新得枪托上的护漆能照出人的眉毛。 有一次下山,一位朝鲜人民军上将,拿着我的枪反复看了足足十分钟,仍爱不释手。 口中不停的念叨: ”好枪,好枪,将来我们也会有的,会有的”。 除此之外,每人还配有五四式手枪一支,匕首一把和四枚手榴弹,可谓武装到了牙齿。
新调入这支部队的人员,要经过两个星期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策纪律教育。 集训期间,我和另外两位战友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这家四口人,老两口,儿子和一个刚过门的儿媳妇。 儿子从军了,我们六个人就挤在这间不大的土炕上。 阿爸吉(大爷或老爸的意思) 为了表示欢迎我们进驻,去的当天便从炕头的柜子里拿出一个土罐子, 从中摸出两块地瓜,放在火盆边上慢慢烘烤起来。 地瓜烤好以后,我们满以为是老两口自己吃,哪知阿巴吉把这两块热腾腾的地瓜,全都放在我们的手里, 用不很熟练的汉语说: “孩子, 吃吧! 这是去年留下来的,留给你们的”。 阿爸吉的话,把原本是两块普通的地瓜,立刻变成了两颗滚烫的心, 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有这种水乳交融的军民情谊垫底儿,我们的军队,没有不打胜仗的理由!
集训的最后一项科目是步枪一百米半身胸环靶实弹射击考核,我打了优秀。 这是入伍近一年来仅有的两次实弹射击考核打的第二个优秀。 第一次是新兵连集训。 我们连一共去了五个新兵,我是唯一1个打了优秀的, 也是入伍仅三个多月,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而获得记录档案的第一次嘉奖。 集训结束后,我留在大队部当通信员。 干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通信员的活,就是每天早晨天不亮,把灌满开水的暖瓶,分别送进大队领导们的家里。 除此,便是坐下来讨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学习。 这多没劲! 于是,我提出去一线哨所的要求。 我的请求很快被批准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坐上去前线送寄养的马车,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在日落前,来到三八线非军事区北阳线入口处停了下来,接着,跟下山接我的同志上山去了。
临津江畔的日日夜夜
为了保密和便于管理,哨所是按照百家姓中的赵,钱, 孙, 李,周, 吴, 郑, 王等百家姓中的姓氏排位作为代号而起的名字。 我所在的哨所是赵庄,作为百家姓中的首姓, 赵庄显然是这支部队中的第一个哨所。 全部成员一个加强班,约20人。
此山不太高,估计海拔三四百米, 但它的战略位置却十分突出。 自山顶哨所往下走,30度左右的坡度,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的临津江边。 一条可以通行车辆的土路自北向南顺江而下,直指200米外非军事区南北分界线的中间线。 一辆被打坏的美军坦克,孤零零地趴在离土路不远的半山坡上, 似乎在告诉人们,当年这里的战斗是何等激烈。 临津江的西岸,刀削般的山峦与英雄阵地马良山主峰紧密相连。 由此可见,此处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山上没有水源,解决用水的唯一办法, 是去山下的临津江里取水,因此,每隔两三天,就得派人去江中取一次水。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这样的活动只能在夜间进行。 到哨所不两天,我便跟随战友们去山下的江中取水。 这是个寒冷的冬季,我们走到江中心, 用钢钎撞开厚厚的冰层,取出冰块放进麻袋里背上山,放进锅里化成水以备生活之用。
哨所每天必须完成的三项任务: 观察哨,巡逻哨和伏击哨。 除此之没有别的活动。 看军犬训练,就成了我们唯一的乐趣。 随着军犬引导员(现在称训导员)的声声口令,这条曾因抓捕越境特务而立过三等功的德国黑贝犬,以它骄健的身姿, 时而跃起,时而狂奔,时而坐卧,时而匍匐。 那敏捷而又有节奏的动作,着实让人有一种快乐和安全感。 不过,也有让人揪心的时候。 三八线里面由于长期无人居住,野生动物较多。 一天夜里,可能受到野生动物的干扰,这只犬连叫了两声,第二天一大早,看到自己的主人手持皮鞭生气的站在犬舍外面,自知犯了军纪,便主动走出犬舍, 蜷缩在地上任主人鞭打。 打完以后,坐起来伸出前爪与主人握了握”手”,此事才算了结。
春节快到了,哨所里过年没法和后方相比,可也总得有所表示呀!于是,班长决定在哨所大门外边搭建一个彩门。 一听说采松枝搭彩门,我一个高跳出战壕,欲到十多米外的小松林里采松枝。 刚出战壕就被班长喊了回来,原来,我的胳膊上没有带黄色袖箍。 班长严肃的告诉我:” 这样出去被敌人一枪打死白白送死”。 说着,便把印有中朝两国文字” 民警” 的黄袖箍戴在我的左胳膊上。 这时我才明白黄袖箍竟是如此重要。 因为它是朝鲜停战委员会规定的,南北当事双方共同认可的合法标志。
就在这天夜里,我们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突然,阵地上传来紧急情况。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我们全部进入了阵地。 由于平时准备充分,进入阵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平时放在掩体里的一箱手榴弹,搬放在掩体边沿并迅速打开箱盖,将手榴弹摆放在战壕前沿,熟练地打开保险盖,拉出安全绳, 放在眼前随时备用。 一切准备妥当,便静静趴在掩体里观察阵地前面的动静。 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后半夜三四点钟,仍没见对面的敌人有动静,这才决定撤出阵地。
生死一瞬间
在赵庄执勤一个多月后,我被调到了孙庄。 相比赵庄,孙庄的地域相对宽阔平缓。 同样是三项任务,这里负责的面要大一些。 观察哨可一直看到约两公里外著名的老秃山山脚下。 一天,我和一位战友正在哨位上按照规定由左至右,由近到远举着望远镜进行观察搜索,突然发现老秃山山脚下的草丛里有一个黑点在移动。 仔细辨认,发现是一个人。 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班长。 班长核实情况以后,立即向后方作了汇报,并派出一个三人抓捕小组 迅速向事发地出击。 我方的行动,或已被敌方发现,待抓捕小组到达后,敌特已不知去向。 但一位参与抓捕的战友,却在事发地捡到一只”中华” 牌钢笔。
巡逻哨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三个人走在非军事区荒漠的小路上,不时有野猪,狍子和野兔之类的动物从前面跑过,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缺乏生活情调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有趣的调味品吧!
最困难的要算伏击哨了。 天黑出去,一夜要换三四个伏击点,每个伏击点一趴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 别的好说,两三个小时趴着一动不动,这困劲儿一上来哪受得了啊! 刚开始参加伏击,由于心情紧张, 两只眼瞪得比平时大一圈,参加伏击的次数多了,往那儿一趴不到十分钟眼睛就睁不开了。 为了撵走困劲儿,用手掐自己的脸,咬手指头,抓周边的雪擦眼睛, 揉鼻子,往脖子里塞雪块。 总之,能用的招都用了, 还时不时的打个盹儿。 有一次,在幽静的山谷里, 天上静静的飘着雪花,没有一丝风。 为了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我们的羊毛军皮大衣都是毛朝外反穿着。 在掩体里趴了大约半个小时,正困得睁不开眼的时候,在我掩体前面两米多处的草丛里,一只野鸡突然吼叫起来。 在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响声的环境里,这突如其来的叫声,相信几公里之外都能听到,何况这叫声就在自己的眼前。 也正是这一声吼叫,直到撤离阵地之前,困劲儿再也没来过。
还有一次,班长带着我们两个人,在山脚下的掩体里打伏击,刚进入伏击点不久,就听得半山腰荆棘丛中像是有人走动的声音。 于是,班长立刻命令: “打开保险,(我们的枪支一天24小时都上了膛的,打开保险即可击发。 ) 准备战斗! ” 话音刚落,我们三人同时跃出战壕,端起刺刀,排成”一” 字散兵队形,向事发地大步冲去。 搜索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估计是那些该死的野生动物搞的鬼。 由于过早的暴露了自己,只得提前返回营区。 就在我们刚躺下不久,只听房舍后面一阵激烈的搏击声,其间还有动物的惨叫声。 次日早晨一看,原来是一只野生狍子被另一只动物咬掉了舌头,死挺挺躺在房屋后面的小路旁。 这下我们可乐坏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死狍子拎回厨房,全班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俗话说: 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就在我们撤出阵地的前几天,班长带领我们两个战士巡逻回来的路上,在距离营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走在前面的班长突然被一根细麻绳绊了一下,随即,一个拳头大小的铁疙瘩从路边的草丛里滚了出来,班长回头捡起来一看,立刻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这个手榴弹大小的铁家伙,是一颗跳雷。 什么叫跳雷?就是当这颗雷的保险销被拔出以后,他不会立即爆炸,而是从地上跳起一米高再爆炸。 当时,我们三个人是沿着这条小路成纵队行进的,人与人之间的前后距离为三至五米。 当班长被绊以后,到此雷跳起的瞬间,刚好在我眼前爆炸,其后果可想而知。 可为什么这颗雷没有爆炸呢? 一看才知道,由于此雷被放在露天草丛里的时间比较长,插在跳雷手柄上的插销与弹柄孔外缘的接合部有点锈蚀。 尽管如此,保险销仍被拉出四分之三, 仅有韭菜叶宽的一段保险销没被拔出,这一点点没被拔出的保险销,却使我们三个人逃过生死一劫, 真是人不该死天相助啊! 此事, 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
两军友谊 地久天长
志愿军撤军的消息,两天前已经传达到我们的耳朵里,但你看不出每个人脸上的喜悦和激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此以后,很难再有机会守护这片曾经用战友们的鲜血染成的热土了。
一天晚上, 朝鲜人民军一个班前来接访。 两军战友相见,犹如久别的亲人格外热情。在仅有的两天时间里,我们一起上观察哨,一起巡逻,晚上一起伏击。 大家虽然语言不通,肢体语言和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人民军对志愿军的感激之情和对对面敌人的切骨之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下山的头一天,一位人民军战士,把自己身穿军装的照片送给我,用手指了指天, 指了指地,又指着他本人和我,说出 ”友谊”两个字。 哦!我明白了, 他是在说,我们的友谊和天地一样长久。 还有一位人民军战士,他没有自己的照片,却把自己姐姐的照片送给我作永久留念。 这些照片,至今我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相册里。 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
临下山的头一天晚上,班长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和另一位战友把包括一位中校军官在内的约20位人民军人员送到钱庄去,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这是我在三八线撤出阵地之前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
尾 声
3月15日早晨8点,我们的车队准时出发了。 下午3点多钟,车队来到朝鲜东海岸的元山港。 远远望去,人声沸鼎,彩旗飘飘,热闹非凡。 广场中央,高高搭起的舞台上,悠扬的舞曲声声悦耳,让人陶醉。 车队的领导,高声呼喊着要我们下车去跳舞,于是,我们纷纷跳下车去,不一会儿, 便消失在欢乐的海洋中去了。 从这里开始,在一路欢歌一路舞中,我学会了朝鲜民间舞蹈 – - “道拉几”。 也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由乘坐卡车,转乘军用专列 (俗称闷罐子车 ) 一路北上。 3月18日清晨一觉醒来,我们的军列已经静静停靠在齐齐哈尔市东站的铁轨上了。
随着这支部队在中国境内安营扎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光荣称号,也跟着走到了它的终点。
归国以后的民警大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曾经是其成员的我们,又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我被分配到陆军第六十九师师部侦察连。 同年12月30日,同该师另外12位战友一道,共同走进了人民空军长春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的大门。 自此, 这条长达27年的歼击机飞行员之路,一直伴我走到1985年。
再见了朝鲜,我曾经驻守过的美丽国度! ,
再见了三八线,我曾经熟悉过的那片热土!
2020年3月15日追记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