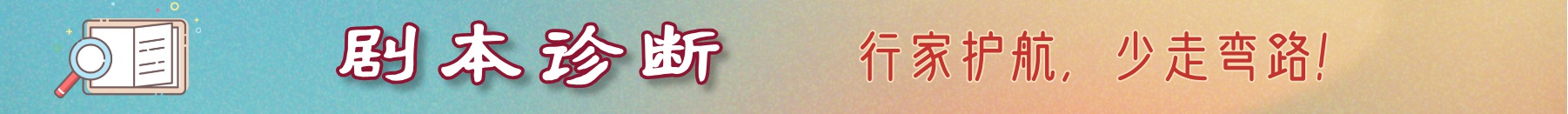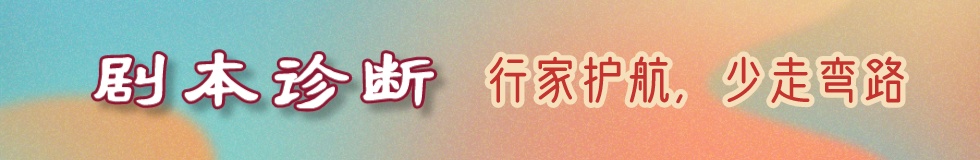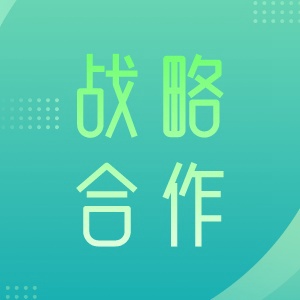权属:原创 · 独家授权
字数:24236
成片时长:约16分钟/集
阅读:11306
发表:2014/5/2
修改:2014/5/4
27集 古装 网剧剧本
《被遗弃的补天石》第22-26集
1-6
7-11
12-16
17-21
22-26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李驎:“两位大师既是出家人,寺院正可颐养天年,为何要自盖房屋?”
石涛:“此中缘由,说来话长,我看李先生是个性情中人物,虽然初次见面,却如故友重逢一般,我们兄弟俩的出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待以后细细告知。我们想在附近找一块地皮,不知李先生能否帮忙。”
李驎:“这不难,这里民风醇厚,村民与我都有交往。这样,我把学生放了学,带两位出去走走,看上那块地,我替你们打听并交涉。”
李驎到教室里收好孩子们的作业,嘱咐孩子们放学回家,下午再来上学。于是带着喝涛与石涛往外走。村庄南面有一条小溪流过,为了巩固河岸,岸边砌着大块石头,沿河种着些垂杨柳,风景优美,还时有摇橹小船通过。
石涛:“真是个好地方,这条河是不是运河?”
李驎:“这是绕过扬州城里的一条小河,最后流入运河。”
石涛:“这地方好,师兄,你说是不是?在河边不远处盖一座房子,面对小河,多有意思。李先生,雨季河水会不会泛滥?”
李驎:“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了,河水从来没有泛滥过,因其下游通到大运河,水流畅通,不会泛滥。”
喝涛:“我看这里的确不错,就在这里吧!何况这里有一个好朋友李驎先生为邻居。”
李驎:“好,你们看好地,我可以到村里打听是谁家的地,买下来,两位大师想要盖什么样的房子,可以画个草图,我可以找人帮助设计建造,两位只要常来看看就是了。我的房子就是到这里后,在村民的帮助下盖的。”
石涛大喜:“好极了,多谢李兄!”
【3】北京密云白衣庵中,曹钰与红梅在一起思念石涛。
曹钰:“红梅姐,你说先生要靠画画为生,靠卖画的钱自己盖一座房子,这可能吗?不会把先生给累坏了?”
红梅:“唉!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终究已经年过半百,不是年轻人了。不过,我了解阿长弟,他从小就很固执,想干一件事时,不管多难,他一定要干成,他的性格与他父亲一样。”
曹钰:“你很了解他与他的父亲?”
红梅:“我父母都生活在靖江王府,我父亲原来是给靖江王办些文案工作。靖江王爷因见我父文才不错,就让他做阿长的老师,我也就跟着一起认识些字。我离开靖江王府时只有五岁,什么也不懂,后来听我母亲常常说起,其实靖江王爷要是不去作那个监国,带着全家安安静静地找一个地方隐居,阿长也不会只有四岁就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
曹钰:“红梅姐,这我就与你有不同的看法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明亡清兴,是异族侵占我中华大地,多少汉族有志之士奋起抗争,作为大明封据一方的王爷,是必须要勇敢起来担当复明的任务的。问题是同为明朝王室,却不团结一致,而相互残杀,酿成悲剧。”
红梅:“你说得对,一个人要是窝窝囊囊地,也不像是个男子汉。”
曹钰:“先生自幼失去父母、失去家,但很坚强。他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二十多年前我在紫阳书院听先生讲课,听得我入了迷,他作画就反对墨守成规,有自己创造性的画论。他的画不是真山河的模写,好像都是从心底流露出来的心声。我想他想做一件事,就只有成功而后已,绝不会半途而废。”
红梅:“你真是阿长的红颜知己,我想他要在扬州建一个家,也一定会成功的,我们耐心等着好消息吧!”
【4】乙亥年,即1695年秋天,江宁织造府中,曹寅在看朱赤霞作画。
曹寅:“我看你们朱明的子孙,都有作画的天才。石涛、八大山人不用说,已是当代著名画家,我看你的画也很不错。”
朱赤霞:“啊呀呀,你就别笑话我了。我这那里算得上作画,只能算涂鸦而已,我有空就画了一些花卉,我主要是想要你在画上题诗,我很喜欢你的诗,也喜欢看你推敲诗句时摇头晃脑的样子。”
曹寅:“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去扬州找到石涛了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朱赤霞:“我到天宁寺去找他,天宁寺的和尚告诉我他已经搬出天宁寺,现在居无定所,要打听到他的行踪,可以去找大东门外大东庄一个名叫李驎的塾师。”
曹寅:“你找到那位塾师了吗?”
朱赤霞:“找到了。那位李驎塾师倒是一位风雅人物,是前朝一个大官的孙子,隐居在扬州,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他告诉我,他已经替石涛选好一块地,帮助石涛在那里盖一所房子。石涛为了筹聚盖房费用,四处给人作画,听说应合肥李容斋相国与太宁张见阳两先生相招,已在今年夏天到合肥去了。”
【5】因天宁寺僧众知道石涛已经无心佛事,未免有些风言风语,石涛既已决心离开僧界,便不愿意在寺庙里多逗留,“到处茅亭借得住”,随遇而安。为了盖房子用钱,一反过去的矜持,谁要他的画就给谁画。喝涛也就又回到南京报恩寺去栖歇。
不久,石涛接受李容斋相国与太宁张见阳两人的邀请,到合肥去,被安排在已去世的安徽著名书画家龚鼎孽(号芝麓)先生的‘稻香楼’居住。但石涛满心惦记着扬州李驎给自己盖房子的事,不能在合肥逗留太久。辞别李相国与张太守,由水路回扬州。过巢湖时,被风浪所阻,旅客都在岸边一旅舍休息。石涛心里很烦,想自己已经头白垂老,还在为营造一个家而四处奔波。看着巢湖的汹涌波涛像是自己内心的写照。百无聊懒,在行囊中取出文房四宝,画了一幅巢湖图,上面写上三篇题跋,其中第一段写着:
百八巢湖百八愁,游人至此不轻游;无边山色排靑影,一派涛声卷白头。且踏浮云登凤阁,慢寻浊酒问仙舟……
将此画托人送送给张见阳。
【6】石涛回到扬州,连忙赶到大东门外,去找到李驎。
李驎:“石涛弟,您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正想找您商量呢!”
石涛:“怎么样?房子盖好了吗?”
李驎:“走,我们看看去,还有什么需要增加或修改的。”
走到小河边,一座小巧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前院两室一厅,厅门面对小溪,后院有东西两厢房,再后是一些生活用房,用房边一个后门,通向田野。虽然简朴,却应有尽有。石涛大喜过望,对李驎千恩万谢。
石涛:“李兄,谢谢您。要没有您的帮忙,我自己要盖这样一座房子真不可想象。”
李驎:“石兄是当今名士,有幸来本地落户,实在是蓬荜生辉,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
石涛:“李兄,希望你能替我找两个人,帮我干点杂活。”
李庄主:“这好办,我已经替您物色好了,我村有一对夫妻,男的姓赵,四十多岁,无儿无女,人老实可靠,可以让他们搬到你后院小房中住,可以为你做烧饭、买菜等事。你房子后面的空地,可以种菜,房前可以种花,这些活他们都能干的。”
石涛:“真感谢李兄。我自幼出家为僧,都在寺院里生活,只会拿着笔画画,在生活上一窍不通,没人帮忙,我连自己肚子也填不饱。”
李驎:“石兄,你想好给新居起一个什么名字了吗?”
石涛:“我想好了,叫‘大涤堂’,给我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号‘大涤子’。我要自下而上一起涤,将一辈子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都洗涤掉,恢复我本来面貌。”
李驎:“好!好极了!”
石涛很激动:“我不是和尚,我要脱去僧袍,还我本来面貌。我是‘阿长’,‘赞之十世孙阿长’,我是‘若极’,我是‘靖江王王子朱若极’!”
李驎:“石兄要把自己真实面目公诸于世,我一定为你写一本《大涤子传》!”
【7】石涛正在思索如何把北京的何红梅与曹钰接来扬州,找博尔都帮忙呢还是?正巧朱赤霞来了。朱赤霞看到已经脱去僧袍,头上已经略有些头发的石涛,连忙打招呼。排起辈分,石涛其实比朱赤霞还小几辈,但石涛比朱赤霞年纪大,第一次见面时,石涛还是个和尚,朱赤霞尊称石涛为‘石涛上人’,现在石涛已经离开僧界,就称呼石涛为‘石公’或‘先生’。
朱赤霞:“石公,我已经来找过您好几次了,我现在在江宁织造府工作,曹寅待我很好,他也很记挂着您,常要我打听您回扬州没有。每次来碰到李驎先生,李先生也都说在盼着您回来。终于把房子盖好了,什么时候去接何小姐与曹小姐来?”
石涛:“我正在伤脑筋哪,让她们自己来,两个女流之辈经那么远的路途,实在不放心。请博尔都帮忙吧,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而且,这两个人,还说不定推三阻四地,不会痛快地说来就来。人言可畏,她们还以为我还是个和尚呢!”
朱赤霞:“这样,我去接她们来。”
石涛:“你们织造府不是很忙的吗?你怎么有时间去北京呢?”
朱赤霞:“织造府正要送一批贡品进京,我让曹寅派我这个差事,顺便我去接两位小姐来。我会说服她们,让她们明白,先生已经出僧还道,非常需要有一个家庭,没有她们不行。”
石涛:“好,好,只有拜托你了。”
第二十四集完
第二十五集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时间】1697—1700年,康熙三十六——三十九年,
【地点】扬州大涤堂,
【人物】石涛,56——59岁,
曹钰,42——45岁,
红梅,57——60岁,
喝涛,76——79岁,
朱赤霞,39——42岁,
曹寅,40——41岁,
李驎,64——67岁,
【1】朱赤霞已经把红梅与曹钰从北京接到扬州,曹钰来扬州不久,在喝涛与何红梅主持下与石涛成亲。大涤堂中,面河朝南的一溜三间房子,东面一间屋为石涛与曹钰的新房;中间一间屋为客厅,平时大家闲谈或吃饭都在客厅;西边一间屋作为石涛的画室。何红梅住东厢房,喝涛住西厢房。后门旁两间房子,一间是厨房,另一间老赵夫妇居住。石涛已经完全像个道士,留了头发,戴上黄冠。喝涛也脱去僧衣,但因喝涛年逾古稀,头上根本没有几根头发,剃不剃头没有什么差别。这样一家子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何红梅俨然是一家之主,石涛卖画得来的钱都交给红梅管理。喝涛住到这里后喜欢出去散步,也结交了一些老年朋友,常常与朋友们拿着钓竿在河边钓鱼。
石涛:“红梅姐,辛苦您啦,钱还够用吗?我多画一些画,不让大家跟着我受苦,老师呢?老师一大早出去散步啦?”
红梅:“父亲他坐不住,他现在迷上钓鱼啦,一早就拿着钓竿到河边去了。他说钓鱼很好玩,也有经济利益,钓上了鱼可以改善大家伙食。”
【2】石涛与曹钰新婚燕尔,两人在青年时期相恋,经过将近三十年的两地相思,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对老年新婚夫妻,恩爱无比。这天,吃了早饭后两人到了画室。石涛在画桌上铺上了画纸,曹钰在画桌旁替石涛研墨。石涛抬头看着曹钰,眼前出现了紫阳书院的情境
【回放】……
石涛:“那您也摊开纸画一张,看我们两人心目中的新安山水是不是一样。”
曹钰:“不,我不能画,我心中没有装下新安山水。”
石涛吃了一惊:“那您心中装下什么啦?”
曹钰红了脸,轻轻地说:“我、我装下了一个、一个对着山水指指点点的——先生——你!”
石涛:“啊!┄┄”
曹钰:“先生,说真的,我很愿意一直替您研墨,替您摊纸,替您洗笔,看先生画画,您愿意收我在身边做您的书童吗?”
……
曹钰:“先生,你不开始画,尽看着我干什么?”
石涛:“二十多年过去了,钰妹还是原来样子,只是那时候你穿着男装,我可不行了,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
曹钰:“先生取笑了。先生不老,人不能用岁月来计算,主要看精神,二十多年前,先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现在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比在紫阳书院时还显得年轻呢!那时候…”
石涛:“那时候怎么样?”
曹钰抿着嘴笑着轻轻说:“那时候我对先生又爱又怕…”
石涛一把攥住曹钰的手,将她拉近自己身旁:“现在呢?现在还怕我吗?”
曹钰不好意思:“你说呢?怕你我还会到扬州来?!”
石涛大笑:“哈哈!”
石涛摊开纸,画了一幅《石竹水仙图》上题诗云:
冰姿雪色奈双钩,淡淡丰神隔水羞。
一啸凝脂低粉面,天然玉质趁风流。
早春争秀芳兰并,带露凌空洛浦俦。
灯下但将文竹补,管夫人*醉得搔头。
(*注:管夫人,即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一字瑶姬,德清县茅山村人,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自幼聪慧,能诗善画,嫁赵孟頫,册封魏国夫人。元延裆六年五月十日病卒,葬东衡里戏台山。擅画墨竹,笔意清绝。又工山水、佛像、诗文书法,尤擅墨竹兰梅,笔意清绝,负盛名,世称管夫人。)
曹钰:“先生把水仙看成美人了,把文竹看成管夫人了,管夫人怎么醉得搔头呢?”
石涛调皮地搔搔自己的头说:“管夫人陪伴着自己心爱的水仙,已经无酒自醉了,哈哈!”
曹钰想了一下,醒悟过来,原来石涛把自己比作了水仙,不觉羞红了脸。
【3】石涛虽然与八大山人没有见过面,但两人心仪已久。大涤堂堂建成后,石涛就写信请八大山人替他画一幅大涤堂图,信中要求:‘……平地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八大山人画好后,让朱赤霞送给石涛,除了大涤堂图,还送了石涛一幅《桃石双禽图》上题着“丙子夏日写 八大山人”
朱赤霞:“八大山人说大涤堂图是按先生信中要求画的,先生要求大涤堂里要画上您大涤子本人,他画了两个,一个是大涤子先生您,一个是他八大山人,他说,‘两人身居两地,无缘在一起切磋画义,只能在图中略表寸意了。”
石涛:“好极了,我与八大老兄不能当面交谈,在画中互诉衷肠,也未尝不是很好的补偿。上次送我的是两只鹌鹑在一起交谈,现在真是两个老人在一起了。这幅《桃石双禽图》是送我的?两只鸟,不会又是在同室操戈吧?这两只鸟却不像在吵架。”
朱赤霞:“不是,这是去年(丙子年)夏日八大先生闻听您成家时特地画了送您的。石头、红桃象征着石涛先生与曹钰小姐,双鸟意味着琴瑟和鸣。”
石涛:“真要谢谢八大老兄。”
石涛继续细看八大山人的两幅画,看到《大涤堂图》上又画了一个花押(如图所示)
石涛:“八大先生在他的画上总喜欢画上一个花押,我在他的很多山水画上都看到过,我百思不得其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朱赤霞:“我开始也不懂,既不是他常用的号‘八大山人’,又不是他的号‘个山’与‘雪个’,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是四个字,是每个朱明子孙都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个山与雪个都是八大山人的号。)
石涛思索了一会儿说:“啊!我明白了,是‘三月十九’四个字,三与月连在一起,而且横倒写,十与九连在一起。三月十九,这是崇祯殉难的日子,天崩地裂的日子!怪不得雪个老兄在山水画上总是喜欢画上这个花押,是告诉大家这一天山河变色了啊!唉!雪个老兄真是‘金枝玉叶老遗民’,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应该学习的榜样。”石涛随手拿起一张纸,写下了如下四句:
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
兴到写花如戏影,眼空兜率是前身。
朱赤霞:“个山前辈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有时故意装成疯疯癫癫的样子,其实是满心苦闷,有人评论他的画是;‘墨点无多泪点多。’”
(注:诗“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描写八大山人而写的,郑板桥(1693—1765年),是八大山人与石涛等的后人,当时朱赤霞不可能读到这首诗。但我觉得当时八大山人的友人对他的画的评价都会感到这点,写出这样的话的。)
石涛:“好一个‘墨点无多泪点多’!真是八大山人的知音。”
石涛沉思了好一会儿,朱赤霞也默默无言,两个朱明皇朝的子孙深深为这天崩地裂而沉痛,为自己无力补天而愧疚。
石涛:“我很想写一本书,怀念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用我们的一生遭遇来痛斥南明那些不肖的子孙。”
朱赤霞:“我同此心,先生要写,我一定尽绵薄之力。但这要有技巧,现在文禁还是很凶,不能直白地写。”
石涛:“最近我在一幅《竹笋》的画上题了一首诗:‘出头原可上青天,奇节灵棍反不然,珍重一生浑是玉,白云堆里万峰边。’我觉得我们写书,要像竹笋那样,把白玉一样的笋包裹在笋壳中,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包裹在外壳故事里,让表面的故事在云里雾里、青山绿水中辗转,而真实的思想却在关键的地方隐藏起来,一旦被后人发现,就像笋尖一样可以直冲青天。”
朱赤霞:“这很难写,先生先写着试试吧!我看这书名可以叫《红楼梦》,朱明子孙怀念朱明天下的梦。”
石涛:“不妥,应该叫《被遗弃的补天石》?不,这也不妥。”
朱赤霞:“还是叫《石头记》吧?可以用一个神话开头,一块被遗弃的补天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在石头上。”
石涛:“好,这个好,我先试着写写看。”
朱赤霞:“先生很忙,您只要把关键之处写好,表面的故事情节想个大概,我来执笔。”
石涛:“你在曹寅织造府工作,不能花费太多时间。这样,我初步计划了内容,可以说给曹钰听,她有些文才,让她写个初稿,再交给您修改润色。”
朱赤霞:“就这样。”
石涛:“此中缘由,说来话长,我看李先生是个性情中人物,虽然初次见面,却如故友重逢一般,我们兄弟俩的出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待以后细细告知。我们想在附近找一块地皮,不知李先生能否帮忙。”
李驎:“这不难,这里民风醇厚,村民与我都有交往。这样,我把学生放了学,带两位出去走走,看上那块地,我替你们打听并交涉。”
李驎到教室里收好孩子们的作业,嘱咐孩子们放学回家,下午再来上学。于是带着喝涛与石涛往外走。村庄南面有一条小溪流过,为了巩固河岸,岸边砌着大块石头,沿河种着些垂杨柳,风景优美,还时有摇橹小船通过。
石涛:“真是个好地方,这条河是不是运河?”
李驎:“这是绕过扬州城里的一条小河,最后流入运河。”
石涛:“这地方好,师兄,你说是不是?在河边不远处盖一座房子,面对小河,多有意思。李先生,雨季河水会不会泛滥?”
李驎:“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了,河水从来没有泛滥过,因其下游通到大运河,水流畅通,不会泛滥。”
喝涛:“我看这里的确不错,就在这里吧!何况这里有一个好朋友李驎先生为邻居。”
李驎:“好,你们看好地,我可以到村里打听是谁家的地,买下来,两位大师想要盖什么样的房子,可以画个草图,我可以找人帮助设计建造,两位只要常来看看就是了。我的房子就是到这里后,在村民的帮助下盖的。”
石涛大喜:“好极了,多谢李兄!”
【3】北京密云白衣庵中,曹钰与红梅在一起思念石涛。
曹钰:“红梅姐,你说先生要靠画画为生,靠卖画的钱自己盖一座房子,这可能吗?不会把先生给累坏了?”
红梅:“唉!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终究已经年过半百,不是年轻人了。不过,我了解阿长弟,他从小就很固执,想干一件事时,不管多难,他一定要干成,他的性格与他父亲一样。”
曹钰:“你很了解他与他的父亲?”
红梅:“我父母都生活在靖江王府,我父亲原来是给靖江王办些文案工作。靖江王爷因见我父文才不错,就让他做阿长的老师,我也就跟着一起认识些字。我离开靖江王府时只有五岁,什么也不懂,后来听我母亲常常说起,其实靖江王爷要是不去作那个监国,带着全家安安静静地找一个地方隐居,阿长也不会只有四岁就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
曹钰:“红梅姐,这我就与你有不同的看法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明亡清兴,是异族侵占我中华大地,多少汉族有志之士奋起抗争,作为大明封据一方的王爷,是必须要勇敢起来担当复明的任务的。问题是同为明朝王室,却不团结一致,而相互残杀,酿成悲剧。”
红梅:“你说得对,一个人要是窝窝囊囊地,也不像是个男子汉。”
曹钰:“先生自幼失去父母、失去家,但很坚强。他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二十多年前我在紫阳书院听先生讲课,听得我入了迷,他作画就反对墨守成规,有自己创造性的画论。他的画不是真山河的模写,好像都是从心底流露出来的心声。我想他想做一件事,就只有成功而后已,绝不会半途而废。”
红梅:“你真是阿长的红颜知己,我想他要在扬州建一个家,也一定会成功的,我们耐心等着好消息吧!”
【4】乙亥年,即1695年秋天,江宁织造府中,曹寅在看朱赤霞作画。
曹寅:“我看你们朱明的子孙,都有作画的天才。石涛、八大山人不用说,已是当代著名画家,我看你的画也很不错。”
朱赤霞:“啊呀呀,你就别笑话我了。我这那里算得上作画,只能算涂鸦而已,我有空就画了一些花卉,我主要是想要你在画上题诗,我很喜欢你的诗,也喜欢看你推敲诗句时摇头晃脑的样子。”
曹寅:“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去扬州找到石涛了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朱赤霞:“我到天宁寺去找他,天宁寺的和尚告诉我他已经搬出天宁寺,现在居无定所,要打听到他的行踪,可以去找大东门外大东庄一个名叫李驎的塾师。”
曹寅:“你找到那位塾师了吗?”
朱赤霞:“找到了。那位李驎塾师倒是一位风雅人物,是前朝一个大官的孙子,隐居在扬州,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他告诉我,他已经替石涛选好一块地,帮助石涛在那里盖一所房子。石涛为了筹聚盖房费用,四处给人作画,听说应合肥李容斋相国与太宁张见阳两先生相招,已在今年夏天到合肥去了。”
【5】因天宁寺僧众知道石涛已经无心佛事,未免有些风言风语,石涛既已决心离开僧界,便不愿意在寺庙里多逗留,“到处茅亭借得住”,随遇而安。为了盖房子用钱,一反过去的矜持,谁要他的画就给谁画。喝涛也就又回到南京报恩寺去栖歇。
不久,石涛接受李容斋相国与太宁张见阳两人的邀请,到合肥去,被安排在已去世的安徽著名书画家龚鼎孽(号芝麓)先生的‘稻香楼’居住。但石涛满心惦记着扬州李驎给自己盖房子的事,不能在合肥逗留太久。辞别李相国与张太守,由水路回扬州。过巢湖时,被风浪所阻,旅客都在岸边一旅舍休息。石涛心里很烦,想自己已经头白垂老,还在为营造一个家而四处奔波。看着巢湖的汹涌波涛像是自己内心的写照。百无聊懒,在行囊中取出文房四宝,画了一幅巢湖图,上面写上三篇题跋,其中第一段写着:
百八巢湖百八愁,游人至此不轻游;无边山色排靑影,一派涛声卷白头。且踏浮云登凤阁,慢寻浊酒问仙舟……
将此画托人送送给张见阳。
【6】石涛回到扬州,连忙赶到大东门外,去找到李驎。
李驎:“石涛弟,您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正想找您商量呢!”
石涛:“怎么样?房子盖好了吗?”
李驎:“走,我们看看去,还有什么需要增加或修改的。”
走到小河边,一座小巧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前院两室一厅,厅门面对小溪,后院有东西两厢房,再后是一些生活用房,用房边一个后门,通向田野。虽然简朴,却应有尽有。石涛大喜过望,对李驎千恩万谢。
石涛:“李兄,谢谢您。要没有您的帮忙,我自己要盖这样一座房子真不可想象。”
李驎:“石兄是当今名士,有幸来本地落户,实在是蓬荜生辉,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
石涛:“李兄,希望你能替我找两个人,帮我干点杂活。”
李庄主:“这好办,我已经替您物色好了,我村有一对夫妻,男的姓赵,四十多岁,无儿无女,人老实可靠,可以让他们搬到你后院小房中住,可以为你做烧饭、买菜等事。你房子后面的空地,可以种菜,房前可以种花,这些活他们都能干的。”
石涛:“真感谢李兄。我自幼出家为僧,都在寺院里生活,只会拿着笔画画,在生活上一窍不通,没人帮忙,我连自己肚子也填不饱。”
李驎:“石兄,你想好给新居起一个什么名字了吗?”
石涛:“我想好了,叫‘大涤堂’,给我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号‘大涤子’。我要自下而上一起涤,将一辈子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都洗涤掉,恢复我本来面貌。”
李驎:“好!好极了!”
石涛很激动:“我不是和尚,我要脱去僧袍,还我本来面貌。我是‘阿长’,‘赞之十世孙阿长’,我是‘若极’,我是‘靖江王王子朱若极’!”
李驎:“石兄要把自己真实面目公诸于世,我一定为你写一本《大涤子传》!”
【7】石涛正在思索如何把北京的何红梅与曹钰接来扬州,找博尔都帮忙呢还是?正巧朱赤霞来了。朱赤霞看到已经脱去僧袍,头上已经略有些头发的石涛,连忙打招呼。排起辈分,石涛其实比朱赤霞还小几辈,但石涛比朱赤霞年纪大,第一次见面时,石涛还是个和尚,朱赤霞尊称石涛为‘石涛上人’,现在石涛已经离开僧界,就称呼石涛为‘石公’或‘先生’。
朱赤霞:“石公,我已经来找过您好几次了,我现在在江宁织造府工作,曹寅待我很好,他也很记挂着您,常要我打听您回扬州没有。每次来碰到李驎先生,李先生也都说在盼着您回来。终于把房子盖好了,什么时候去接何小姐与曹小姐来?”
石涛:“我正在伤脑筋哪,让她们自己来,两个女流之辈经那么远的路途,实在不放心。请博尔都帮忙吧,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而且,这两个人,还说不定推三阻四地,不会痛快地说来就来。人言可畏,她们还以为我还是个和尚呢!”
朱赤霞:“这样,我去接她们来。”
石涛:“你们织造府不是很忙的吗?你怎么有时间去北京呢?”
朱赤霞:“织造府正要送一批贡品进京,我让曹寅派我这个差事,顺便我去接两位小姐来。我会说服她们,让她们明白,先生已经出僧还道,非常需要有一个家庭,没有她们不行。”
石涛:“好,好,只有拜托你了。”
第二十四集完
第二十五集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时间】1697—1700年,康熙三十六——三十九年,
【地点】扬州大涤堂,
【人物】石涛,56——59岁,
曹钰,42——45岁,
红梅,57——60岁,
喝涛,76——79岁,
朱赤霞,39——42岁,
曹寅,40——41岁,
李驎,64——67岁,
【1】朱赤霞已经把红梅与曹钰从北京接到扬州,曹钰来扬州不久,在喝涛与何红梅主持下与石涛成亲。大涤堂中,面河朝南的一溜三间房子,东面一间屋为石涛与曹钰的新房;中间一间屋为客厅,平时大家闲谈或吃饭都在客厅;西边一间屋作为石涛的画室。何红梅住东厢房,喝涛住西厢房。后门旁两间房子,一间是厨房,另一间老赵夫妇居住。石涛已经完全像个道士,留了头发,戴上黄冠。喝涛也脱去僧衣,但因喝涛年逾古稀,头上根本没有几根头发,剃不剃头没有什么差别。这样一家子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何红梅俨然是一家之主,石涛卖画得来的钱都交给红梅管理。喝涛住到这里后喜欢出去散步,也结交了一些老年朋友,常常与朋友们拿着钓竿在河边钓鱼。
石涛:“红梅姐,辛苦您啦,钱还够用吗?我多画一些画,不让大家跟着我受苦,老师呢?老师一大早出去散步啦?”
红梅:“父亲他坐不住,他现在迷上钓鱼啦,一早就拿着钓竿到河边去了。他说钓鱼很好玩,也有经济利益,钓上了鱼可以改善大家伙食。”
【2】石涛与曹钰新婚燕尔,两人在青年时期相恋,经过将近三十年的两地相思,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对老年新婚夫妻,恩爱无比。这天,吃了早饭后两人到了画室。石涛在画桌上铺上了画纸,曹钰在画桌旁替石涛研墨。石涛抬头看着曹钰,眼前出现了紫阳书院的情境
【回放】……
石涛:“那您也摊开纸画一张,看我们两人心目中的新安山水是不是一样。”
曹钰:“不,我不能画,我心中没有装下新安山水。”
石涛吃了一惊:“那您心中装下什么啦?”
曹钰红了脸,轻轻地说:“我、我装下了一个、一个对着山水指指点点的——先生——你!”
石涛:“啊!┄┄”
曹钰:“先生,说真的,我很愿意一直替您研墨,替您摊纸,替您洗笔,看先生画画,您愿意收我在身边做您的书童吗?”
……
曹钰:“先生,你不开始画,尽看着我干什么?”
石涛:“二十多年过去了,钰妹还是原来样子,只是那时候你穿着男装,我可不行了,老了,头发胡子都白了。”
曹钰:“先生取笑了。先生不老,人不能用岁月来计算,主要看精神,二十多年前,先生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现在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比在紫阳书院时还显得年轻呢!那时候…”
石涛:“那时候怎么样?”
曹钰抿着嘴笑着轻轻说:“那时候我对先生又爱又怕…”
石涛一把攥住曹钰的手,将她拉近自己身旁:“现在呢?现在还怕我吗?”
曹钰不好意思:“你说呢?怕你我还会到扬州来?!”
石涛大笑:“哈哈!”
石涛摊开纸,画了一幅《石竹水仙图》上题诗云:
冰姿雪色奈双钩,淡淡丰神隔水羞。
一啸凝脂低粉面,天然玉质趁风流。
早春争秀芳兰并,带露凌空洛浦俦。
灯下但将文竹补,管夫人*醉得搔头。
(*注:管夫人,即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一字瑶姬,德清县茅山村人,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自幼聪慧,能诗善画,嫁赵孟頫,册封魏国夫人。元延裆六年五月十日病卒,葬东衡里戏台山。擅画墨竹,笔意清绝。又工山水、佛像、诗文书法,尤擅墨竹兰梅,笔意清绝,负盛名,世称管夫人。)
曹钰:“先生把水仙看成美人了,把文竹看成管夫人了,管夫人怎么醉得搔头呢?”
石涛调皮地搔搔自己的头说:“管夫人陪伴着自己心爱的水仙,已经无酒自醉了,哈哈!”
曹钰想了一下,醒悟过来,原来石涛把自己比作了水仙,不觉羞红了脸。
【3】石涛虽然与八大山人没有见过面,但两人心仪已久。大涤堂堂建成后,石涛就写信请八大山人替他画一幅大涤堂图,信中要求:‘……平地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八大山人画好后,让朱赤霞送给石涛,除了大涤堂图,还送了石涛一幅《桃石双禽图》上题着“丙子夏日写 八大山人”
朱赤霞:“八大山人说大涤堂图是按先生信中要求画的,先生要求大涤堂里要画上您大涤子本人,他画了两个,一个是大涤子先生您,一个是他八大山人,他说,‘两人身居两地,无缘在一起切磋画义,只能在图中略表寸意了。”
石涛:“好极了,我与八大老兄不能当面交谈,在画中互诉衷肠,也未尝不是很好的补偿。上次送我的是两只鹌鹑在一起交谈,现在真是两个老人在一起了。这幅《桃石双禽图》是送我的?两只鸟,不会又是在同室操戈吧?这两只鸟却不像在吵架。”
朱赤霞:“不是,这是去年(丙子年)夏日八大先生闻听您成家时特地画了送您的。石头、红桃象征着石涛先生与曹钰小姐,双鸟意味着琴瑟和鸣。”
石涛:“真要谢谢八大老兄。”
石涛继续细看八大山人的两幅画,看到《大涤堂图》上又画了一个花押(如图所示)
石涛:“八大先生在他的画上总喜欢画上一个花押,我在他的很多山水画上都看到过,我百思不得其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朱赤霞:“我开始也不懂,既不是他常用的号‘八大山人’,又不是他的号‘个山’与‘雪个’,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是四个字,是每个朱明子孙都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个山与雪个都是八大山人的号。)
石涛思索了一会儿说:“啊!我明白了,是‘三月十九’四个字,三与月连在一起,而且横倒写,十与九连在一起。三月十九,这是崇祯殉难的日子,天崩地裂的日子!怪不得雪个老兄在山水画上总是喜欢画上这个花押,是告诉大家这一天山河变色了啊!唉!雪个老兄真是‘金枝玉叶老遗民’,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应该学习的榜样。”石涛随手拿起一张纸,写下了如下四句:
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
兴到写花如戏影,眼空兜率是前身。
朱赤霞:“个山前辈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有时故意装成疯疯癫癫的样子,其实是满心苦闷,有人评论他的画是;‘墨点无多泪点多。’”
(注:诗“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描写八大山人而写的,郑板桥(1693—1765年),是八大山人与石涛等的后人,当时朱赤霞不可能读到这首诗。但我觉得当时八大山人的友人对他的画的评价都会感到这点,写出这样的话的。)
石涛:“好一个‘墨点无多泪点多’!真是八大山人的知音。”
石涛沉思了好一会儿,朱赤霞也默默无言,两个朱明皇朝的子孙深深为这天崩地裂而沉痛,为自己无力补天而愧疚。
石涛:“我很想写一本书,怀念我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用我们的一生遭遇来痛斥南明那些不肖的子孙。”
朱赤霞:“我同此心,先生要写,我一定尽绵薄之力。但这要有技巧,现在文禁还是很凶,不能直白地写。”
石涛:“最近我在一幅《竹笋》的画上题了一首诗:‘出头原可上青天,奇节灵棍反不然,珍重一生浑是玉,白云堆里万峰边。’我觉得我们写书,要像竹笋那样,把白玉一样的笋包裹在笋壳中,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包裹在外壳故事里,让表面的故事在云里雾里、青山绿水中辗转,而真实的思想却在关键的地方隐藏起来,一旦被后人发现,就像笋尖一样可以直冲青天。”
朱赤霞:“这很难写,先生先写着试试吧!我看这书名可以叫《红楼梦》,朱明子孙怀念朱明天下的梦。”
石涛:“不妥,应该叫《被遗弃的补天石》?不,这也不妥。”
朱赤霞:“还是叫《石头记》吧?可以用一个神话开头,一块被遗弃的补天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在石头上。”
石涛:“好,这个好,我先试着写写看。”
朱赤霞:“先生很忙,您只要把关键之处写好,表面的故事情节想个大概,我来执笔。”
石涛:“你在曹寅织造府工作,不能花费太多时间。这样,我初步计划了内容,可以说给曹钰听,她有些文才,让她写个初稿,再交给您修改润色。”
朱赤霞:“就这样。”
上一集
到底了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