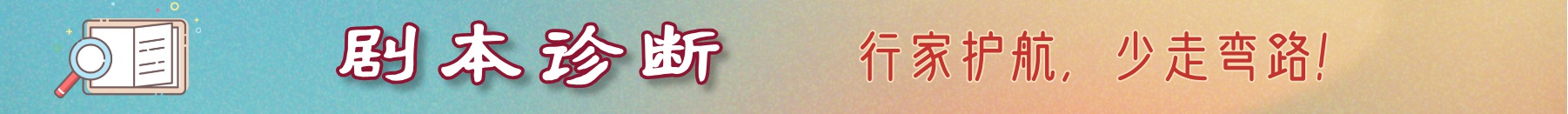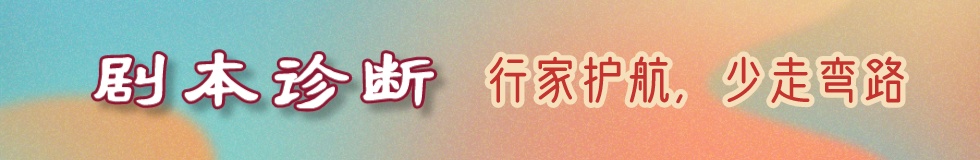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普通授权
字数:34160
成片时长:约109分钟
阅读:15324
发表:2013/8/20
爱情,农村
电影剧本
五个知青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片头
字幕: 谨以此片献给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青
天安门广场,1966年,夏,白天。
整个广场,像一片沸腾的海洋。
字幕:1966年。
红旗、红卫兵袖标、红皮语录本以及数十上百万青年人穿着的草绿色军装,构成这片海洋的主要色调。
人们都手举语录本,仰望着天安门城楼,跳跃着,有节律地呼喊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登上城楼。
大红灯笼之下和城楼廊柱之间,人们簇拥着毛主席。
城楼上,还有许多中央领导。
有个男青年,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标。
毛主席向广场招手。
北京54中教室,1967年,秋,白天。
一大群红卫兵开会。
有人说“‘无敌派’污蔑咱们‘暴风派’阶级队伍不纯!”
有人说“别怪人家,咱‘暴风’红卫兵造反兵团本来有富农子女嘛。”
有人激烈地喊叫“大富农!不能带红卫兵袖标!”
有人附和“对!对!清理队伍!”
低头坐在课桌边的卫迎煦,突然站起,眼含委屈的泪水,摘下红卫兵袖标装进口袋,捂着脸,痛苦地跑出教学楼。
54中校园,1968年,冬,白天。
大操场上,有面横幅,上书:黑龙江建设兵团报名点。
很多学生拥挤着报名。
卫迎煦挤进报名台前,递上户口本。
戴着红色领章帽徽的兵团干部,看看户口本,又看看卫迎煦说“富农不能去兵团。”
靠边的篮球场上,也有面横幅,上书:插队陕北知青报名点。
零星学生在那报名。
卫迎煦过去报名。
接待干部递个报名表给她。
在填写报名表“出身”栏时,她手有点颤抖,写上“富农”。
卫迎煦家内,晚上。
卫迎煦拿着《知青上山下乡光荣证》给妈妈看。
妈妈说“陕北?学校不是有人去郊区农场吗?”
卫迎煦说“妈妈,我想走得远一点。”
妈妈轻轻地叹气,伤感而且无奈。
北京火车站,1968年底,白天。
站台上热闹非凡,喧嚣一片。
一队队即将启程远行的人,一群群赶来送行的人,把站台挤得满满当当。
英气勃勃的青年人有组织地走进来了,他们手里擎着乘车证,泪水和欢笑,同时聚在脸上。
不少做妈妈的妇女,呜呜哭起来了。
站台上的大喇叭里,播放着激昂雄壮的乐曲,和着播音员浑厚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些家长,因为找不见自己的孩子,急得扯着嗓子大声呼喊,他们的呼喊声,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掩没在一片嘈杂中。
弟弟妹妹帮姐姐卫迎煦背着背包网兜,和一只旧绿色帆布箱,在人群中挤着。
在站台一个角落,解晓光、许蓉、费秀华喊叫“卫迎煦!”
卫迎煦向他们挤过去。
车窗口,站在外面的弟弟妹妹,与车厢内的卫迎煦握手“姐,我们以后一定要去兵团!”
开车的铃声响了。
让人揪心的呼喊声、哭叫声,混和着激越的鼓乐声,轰然响作一片。
黑压压的人群向火车尾部滑去,有人跟着火车奔跑。
火车的速度渐渐加快,把黑压压的人群甩在后边,越甩越远……
(推出片名:五个知青)
车厢。
广播喇叭响起来,传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
1
扇坡村全景,下午。
字幕:1968年底。
荒芜的土山坡,一条“之”形、层级渐升的土路,错落散布着许多土窑洞。
山脚平地,有更多的青色砖房,建筑在三、四条村路边。
村中央,有个不规则的广场。
村边低地,有条枯干的小溪。
寂寥之中,突然传来锣鼓声,而且越来越响亮。
村口。
七、八个社员,毛巾裹头,正在敲锣打鼓吹唢呐。
一条横幅,挂在墙壁上,写着:热烈欢迎北京知青!
一群小孩追逐嬉闹着。
一棵老柳树,粗大的树干半面枯朽。有小孩骑在树枝上。
村外土路上。
一辆马车正颠簸着前进。
“奏(就)到哩!奏到哩!”
驾车的中年汉子程队长,手指着前面说。
村口。
马车停下。
二男二女四个知青跳下马车,向大家摆手:“乡亲们好!”
程队长指着迎上来的中年人介绍说“这似(是)杨书记,村革委会主任。”
杨书记满脸堆笑,伸出手来。
梳着短发、右边头发用橡皮筋扎起来的漂亮女知青主动与杨书记握手“杨书记您好,我叫许蓉。”
穿着“仿军装”的男知青与杨书记握手“我,解晓光。”
背着个用红丝线绣着“忠于毛主席”黄书包、胸前带着毛主席像章的清秀女知青与杨书记握手“我叫卫迎煦。”
瘦小的男知青与杨书记握手“我,我叫费秀华。”
杨书记边逐个握手,边重复着“欢迎啊!热烈欢迎啊!”
村路。
程队长牵引着马缰绳,边走边指点介绍:
“这搭(这儿)哩,坡下,是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四小队,那搭坡上,是五小队、六小队。你们奏(就)分在俄(我)们六小队。”
几个知青好奇地前后左右张望着。
村中央广场。
知青们从大队部、破旧的戏台前经过。
山坡上,程队长家院落边。
程队长说“这似俄(是我)家。”
有个中年妇女,正在院落内搭起的灶台前做饭。
程队长说“这似俄婆姨(妻)。”
那“婆姨”在围裙上擦手,满面笑容打招呼“待会来吃面。”
大车继续前行,上个小坡,进入一个没有围墙的院落。
知青院落。
土坎下,有三孔窑洞。
院落倒还宽敞,虽然没有院墙,却有个破旧的柴门。院落前面边缘,是个土坎。柴门开在左侧,门外小土坡连着村路。院内角落长着一棵畸形小树,碗口粗细,树身疤疤节节,弯折扭曲,几近扑倒在地。
程队长说“这奏似(就是)你们的家哩。”
知青们有点兴奋地到处看着。
程队长说“后生(男的)住左间,女子住右间,当旮旯(中间)奏做厨房。”
知青们看那窑洞,青砖的正面墙壁上,左右分别竖排写着:“广阔天地”和“大有作为”。看样子是用毛刷蘸着白灰刚刷上去的。
程队长说“卸车吧。先把东西放进窑里,然后到俄(我)家吃饭。”
程队长家院落。
“婆姨”手脚麻利,在灶台上做荞面碗坨。
几个知青觉得新鲜,围拢在她身边观看。
卫迎煦说“阿姨辛苦了。”
“婆姨”说“不敢叫阿姨,你们叫俄(我)秋云嫂吧。”说着,秋云嫂拿起一片已经看不出本色的肮脏抹布,麻利地先擦锅台,擦饭桌,再用它擦饭碗、擦筷子,擦得很细,把每个碗的里里外外都擦到。擦完后,每人盛上一碗荞面碗坨,摆在桌上。
看着擦得干干净净的碗和筷子,许蓉直皱眉头。
秋云嫂说“吃吧,这似(是)荞面碗坨,好吃着哩!”
卫迎煦、解晓光、费秀华等围桌坐下,津津有味吃起来。
许蓉勉强地尝了一点。
“吃碗坨哩!看,知青吃碗坨哩!”
一直趴在矮墙边的、衣着破烂的七、八个小孩,惊叫。
程队长挥手驱逐他们“可(去)!匪(调皮)猴娃!”
小孩们跳着跑散,叫喊着,像要将一个重大新闻通告全村。
村背后山坡,黄昏。
沟壑边,有条曲折山路通往山顶。
路边有稀疏的荆棘。
几个知青爬向山顶。
站在山顶几棵树下,他们前后左右张望。
解晓光指着东北边远处一条发亮的带状区域,叫喊“看,黄河!”
许蓉兴奋地叫“那边,是北京方向!”
卫迎煦不做声,可眼睛发亮。
大家又转过身来,看相反方向。
山坡下的扇坡村尽入眼帘。
村庄笼罩在黝黑寂寞之中,点点光亮犹如萤火虫,那是庄户人家窗纸透出的点点煤油灯光。
偶尔穿来三两声狗叫。
大家小声议论“真安静啊!”
北京卫迎煦家外/内,白天。
杂乱狭窄的四合院。
靠边的一个简朴厅堂。
妈妈拿着铝制的饭盒,从中一样一样地拿出粮本、煤本、布票、肉票、豆腐票……以及一些零钱,摆在饭桌上。
字幕: 谨以此片献给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青
天安门广场,1966年,夏,白天。
整个广场,像一片沸腾的海洋。
字幕:1966年。
红旗、红卫兵袖标、红皮语录本以及数十上百万青年人穿着的草绿色军装,构成这片海洋的主要色调。
人们都手举语录本,仰望着天安门城楼,跳跃着,有节律地呼喊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登上城楼。
大红灯笼之下和城楼廊柱之间,人们簇拥着毛主席。
城楼上,还有许多中央领导。
有个男青年,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标。
毛主席向广场招手。
北京54中教室,1967年,秋,白天。
一大群红卫兵开会。
有人说“‘无敌派’污蔑咱们‘暴风派’阶级队伍不纯!”
有人说“别怪人家,咱‘暴风’红卫兵造反兵团本来有富农子女嘛。”
有人激烈地喊叫“大富农!不能带红卫兵袖标!”
有人附和“对!对!清理队伍!”
低头坐在课桌边的卫迎煦,突然站起,眼含委屈的泪水,摘下红卫兵袖标装进口袋,捂着脸,痛苦地跑出教学楼。
54中校园,1968年,冬,白天。
大操场上,有面横幅,上书:黑龙江建设兵团报名点。
很多学生拥挤着报名。
卫迎煦挤进报名台前,递上户口本。
戴着红色领章帽徽的兵团干部,看看户口本,又看看卫迎煦说“富农不能去兵团。”
靠边的篮球场上,也有面横幅,上书:插队陕北知青报名点。
零星学生在那报名。
卫迎煦过去报名。
接待干部递个报名表给她。
在填写报名表“出身”栏时,她手有点颤抖,写上“富农”。
卫迎煦家内,晚上。
卫迎煦拿着《知青上山下乡光荣证》给妈妈看。
妈妈说“陕北?学校不是有人去郊区农场吗?”
卫迎煦说“妈妈,我想走得远一点。”
妈妈轻轻地叹气,伤感而且无奈。
北京火车站,1968年底,白天。
站台上热闹非凡,喧嚣一片。
一队队即将启程远行的人,一群群赶来送行的人,把站台挤得满满当当。
英气勃勃的青年人有组织地走进来了,他们手里擎着乘车证,泪水和欢笑,同时聚在脸上。
不少做妈妈的妇女,呜呜哭起来了。
站台上的大喇叭里,播放着激昂雄壮的乐曲,和着播音员浑厚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些家长,因为找不见自己的孩子,急得扯着嗓子大声呼喊,他们的呼喊声,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掩没在一片嘈杂中。
弟弟妹妹帮姐姐卫迎煦背着背包网兜,和一只旧绿色帆布箱,在人群中挤着。
在站台一个角落,解晓光、许蓉、费秀华喊叫“卫迎煦!”
卫迎煦向他们挤过去。
车窗口,站在外面的弟弟妹妹,与车厢内的卫迎煦握手“姐,我们以后一定要去兵团!”
开车的铃声响了。
让人揪心的呼喊声、哭叫声,混和着激越的鼓乐声,轰然响作一片。
黑压压的人群向火车尾部滑去,有人跟着火车奔跑。
火车的速度渐渐加快,把黑压压的人群甩在后边,越甩越远……
(推出片名:五个知青)
车厢。
广播喇叭响起来,传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声。
1
扇坡村全景,下午。
字幕:1968年底。
荒芜的土山坡,一条“之”形、层级渐升的土路,错落散布着许多土窑洞。
山脚平地,有更多的青色砖房,建筑在三、四条村路边。
村中央,有个不规则的广场。
村边低地,有条枯干的小溪。
寂寥之中,突然传来锣鼓声,而且越来越响亮。
村口。
七、八个社员,毛巾裹头,正在敲锣打鼓吹唢呐。
一条横幅,挂在墙壁上,写着:热烈欢迎北京知青!
一群小孩追逐嬉闹着。
一棵老柳树,粗大的树干半面枯朽。有小孩骑在树枝上。
村外土路上。
一辆马车正颠簸着前进。
“奏(就)到哩!奏到哩!”
驾车的中年汉子程队长,手指着前面说。
村口。
马车停下。
二男二女四个知青跳下马车,向大家摆手:“乡亲们好!”
程队长指着迎上来的中年人介绍说“这似(是)杨书记,村革委会主任。”
杨书记满脸堆笑,伸出手来。
梳着短发、右边头发用橡皮筋扎起来的漂亮女知青主动与杨书记握手“杨书记您好,我叫许蓉。”
穿着“仿军装”的男知青与杨书记握手“我,解晓光。”
背着个用红丝线绣着“忠于毛主席”黄书包、胸前带着毛主席像章的清秀女知青与杨书记握手“我叫卫迎煦。”
瘦小的男知青与杨书记握手“我,我叫费秀华。”
杨书记边逐个握手,边重复着“欢迎啊!热烈欢迎啊!”
村路。
程队长牵引着马缰绳,边走边指点介绍:
“这搭(这儿)哩,坡下,是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四小队,那搭坡上,是五小队、六小队。你们奏(就)分在俄(我)们六小队。”
几个知青好奇地前后左右张望着。
村中央广场。
知青们从大队部、破旧的戏台前经过。
山坡上,程队长家院落边。
程队长说“这似俄(是我)家。”
有个中年妇女,正在院落内搭起的灶台前做饭。
程队长说“这似俄婆姨(妻)。”
那“婆姨”在围裙上擦手,满面笑容打招呼“待会来吃面。”
大车继续前行,上个小坡,进入一个没有围墙的院落。
知青院落。
土坎下,有三孔窑洞。
院落倒还宽敞,虽然没有院墙,却有个破旧的柴门。院落前面边缘,是个土坎。柴门开在左侧,门外小土坡连着村路。院内角落长着一棵畸形小树,碗口粗细,树身疤疤节节,弯折扭曲,几近扑倒在地。
程队长说“这奏似(就是)你们的家哩。”
知青们有点兴奋地到处看着。
程队长说“后生(男的)住左间,女子住右间,当旮旯(中间)奏做厨房。”
知青们看那窑洞,青砖的正面墙壁上,左右分别竖排写着:“广阔天地”和“大有作为”。看样子是用毛刷蘸着白灰刚刷上去的。
程队长说“卸车吧。先把东西放进窑里,然后到俄(我)家吃饭。”
程队长家院落。
“婆姨”手脚麻利,在灶台上做荞面碗坨。
几个知青觉得新鲜,围拢在她身边观看。
卫迎煦说“阿姨辛苦了。”
“婆姨”说“不敢叫阿姨,你们叫俄(我)秋云嫂吧。”说着,秋云嫂拿起一片已经看不出本色的肮脏抹布,麻利地先擦锅台,擦饭桌,再用它擦饭碗、擦筷子,擦得很细,把每个碗的里里外外都擦到。擦完后,每人盛上一碗荞面碗坨,摆在桌上。
看着擦得干干净净的碗和筷子,许蓉直皱眉头。
秋云嫂说“吃吧,这似(是)荞面碗坨,好吃着哩!”
卫迎煦、解晓光、费秀华等围桌坐下,津津有味吃起来。
许蓉勉强地尝了一点。
“吃碗坨哩!看,知青吃碗坨哩!”
一直趴在矮墙边的、衣着破烂的七、八个小孩,惊叫。
程队长挥手驱逐他们“可(去)!匪(调皮)猴娃!”
小孩们跳着跑散,叫喊着,像要将一个重大新闻通告全村。
村背后山坡,黄昏。
沟壑边,有条曲折山路通往山顶。
路边有稀疏的荆棘。
几个知青爬向山顶。
站在山顶几棵树下,他们前后左右张望。
解晓光指着东北边远处一条发亮的带状区域,叫喊“看,黄河!”
许蓉兴奋地叫“那边,是北京方向!”
卫迎煦不做声,可眼睛发亮。
大家又转过身来,看相反方向。
山坡下的扇坡村尽入眼帘。
村庄笼罩在黝黑寂寞之中,点点光亮犹如萤火虫,那是庄户人家窗纸透出的点点煤油灯光。
偶尔穿来三两声狗叫。
大家小声议论“真安静啊!”
北京卫迎煦家外/内,白天。
杂乱狭窄的四合院。
靠边的一个简朴厅堂。
妈妈拿着铝制的饭盒,从中一样一样地拿出粮本、煤本、布票、肉票、豆腐票……以及一些零钱,摆在饭桌上。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