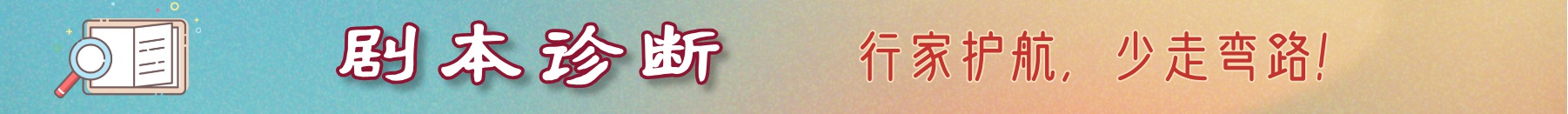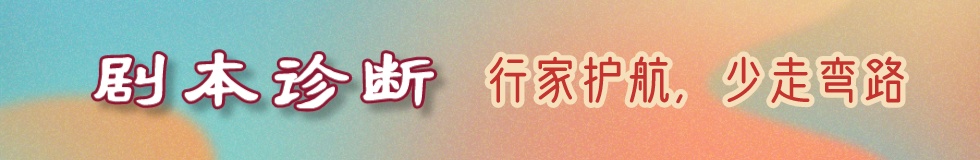权属:原创 · 独家授权
字数:48955
成片时长:约151分钟
阅读:13656
发表:2015/1/1
20集 农村 电视剧剧本
《走出乡镇》第3集
1
2
3
6
- 故事梗概
- 分集提纲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马 军:“那您还记不记得咱们景阳镇到底有没有过日本人?
马洪伟:“日本人肯定有过,以前镇西边有个开拓团,都是日本人。还有日本人在镇上租老百姓的房子住呢。”
马 军:“您见过?”
马洪伟:“那还能没见过?那么多日本人。”
马 军:“噢,说不定他要找的那个人,您还认识呢。”
马洪伟:“是呀,很可能认识,所以我得帮忙找一找。认识的就好找,就怕不认识。”
4、林业局印刷厂
[林业局印刷厂的工人和哈尔滨来的李技师一起在安装调试新买来的印刷机]
小 郭:“师傅,您是哈尔滨印刷厂的吗?”
李技师:“哈尔滨印刷厂多了。”
小 郭:“那您是哪个印刷厂的?”
李技师:“我是哈尔滨前进印刷厂的。”
小 郭:“前进印刷厂?你们厂印报纸吗?”
李技师:“我们不印报纸。”
小 郭:“你们都印什么?”
李技师:“我们印的东西多了,书、杂志、广告,也有报纸,小报。”
小 郭:“那些东西好印。”
李技师:“好印?这些东西最难印,尽是套色的,还不好装订,比印报纸复杂多了,报纸是最好印的。”
大班长:“比较起来,印报纸技术最简单。”
李技师:“对。其实你们光印报纸的话,用不着这么高级的印刷机。”
小 周:“那为啥?”
李技师:“印刷的技术复杂在套色,报纸是单色的,就用一种墨色,用不着调色彩,那还不简单?”
大班长:“现在的小报都是花里胡哨的,大报肯定也得套色,以后恐怕不再是单色的了。”
小 郭:“别的颜色没有,红色总得有,报头,大标题。”
小 周:“对,这回国庆节就得用上。”
大班长:“厂长说了,国庆节要出专刊。”
5、景阳宾馆
[马洪伟来到景阳宾馆。他在总台前向服务员问道]
马洪伟:“我是马洪伟,听说有位外国朋友要见我,请问他在哪儿?”
服务员:“噢,您是马书记!请跟我来。”
[服务员把马洪伟领到二楼客房。客房是大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客厅有沙发、茶几、彩电、冰箱]
服务员:“外宾马上就回来,请您先休息一下。”
[服务员说着从冰箱里取出一罐饮料,噗地打开盖子倒进玻璃杯里双手递给他,然后转身离去了]
[片刻之后,外宾回来了。马洪伟连忙站起来]
[外宾身材瘦削,穿着西服,胡子刮得光光的。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外宾老人的眼睛就盯住了马洪伟,定定地,且不说话,像在辩认,在回忆,直到两人的手握在一起了还没说出话来]
马洪伟:“对不起,我不会说日本话。你是……”
[这时却听外宾突然用中国话说]
外 宾:“对!马先生,是马先生,马厂长,马洪伟厂长!”
[马洪伟惊异不已]
[外宾拉着马洪伟坐下来,从容地解释]
外 宾:“你肯定把我当成外国人了,是吧?外宾嘛。我又有点像日本
人。其实,我是当地人,就是景阳镇的,咱们是老乡呀!”
马洪伟:“你是……”
外 宾:“我叫韩长林,排行老二,那时候都叫我韩老两。”
马洪伟:“韩老两!?你怎么认识我?”
韩长林:“我在你手下当过工人呀!那时候你是景阳镇木材加工厂的厂长。我在加工厂当过工人嘛。”
马洪伟:“是吗?什么时候?我怎么不记得了?”
韩长林:“是呀!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十年以前了!”
马洪伟:“四十年以前?”
韩长林:“对!是四十年以前了。”
6、回放 字幕1950年
景阳镇木材加工厂的储木场
[清晨,景阳镇木材加工厂房顶的汽笛鸣叫,笛声在小镇上空回荡]
[工人们脚步匆匆地走进加工厂大门]
[储木场上的木材堆积如山,有成材,更多的是原木。小火车响着尖厉的汽笛在楞垛之间穿行]
[储木场里的工人有的在归楞,有的在卸小火车,有的在装大火车和汽车]
[全场只有一台小吊车在装车,其它地方都是人工干活]
[加工厂车间。数台电锯同时开动,电机轰鸣,锯沫飞溅,一根接一根原木被推上锯台锯成小方或板材,然后装上平板车运进储木场。
[在一个楞垛跟前,八个戴着肩墊的工人分别站在一根粗大的原木两边,铁钩挂上原木,扁担搭上肩膀,一声吆喝,原木被抬离地面。在一个领头人的带领下,八双脚迈出沉重而又坚实的步子,同时,低沉的、压抑的但又是浑厚有力的号子声迸发出来:
“哎——扛起来喽!嗨——向前走吧!嗨——站稳脚呀!嗨——迈小步呀!嗨——别松劲儿呀!嗨——走上坡呀!嗨——加小心哪!嗨——齐使劲儿呀!嗨——上了车呀!嗨——轻放下呀!嗨——”……
[这一组人抬着原木一步步走上踏板,走上火车的车厢,放下原木,号子声也就停止,摘下挂钩,抽出扁担,下车去抬另一根原木]
[这其中的一个人就是韩长林]
回放完
7、景阳宾馆 韩长林客房
马洪伟:“对,对,是木材加工厂。那时候刚解放,还没成立林业局,就是个木材加工厂,人也不多,条件不好,工人干活很苦,也没有机械。”
韩长林:“那时候厂里工人有好几百,我干的时间又不长,你不会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因为你是厂长。”
马洪伟:“那你现在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又成了外宾了?”
韩长林:“马先生可能不知道,我虽是咱们景阳镇的老乡,但我不是中国人。怎么说呢?我先是朝鲜人,后来是中国人,现在呢,我又是朝鲜——噢不,是韩国人。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祖先是朝鲜人。在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家里人从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半岛跑到了中国东北,在东北一路逃荒来到景阳镇,在这里落了户。后来中国东北也给日本人占了,咱们都成了亡国奴,一直到苏联红军解放了全东北。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一去就没回来。”
[韩长林说到这里停下来,脸上现出苦涩的神情,似有难言之隐]
[韩长林掏出香烟,先给马洪伟抽出一支,马洪伟谢绝了,他便自己叼在嘴里。当他打火点烟的时候,马洪伟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抖]
[他吸了一口烟之后说:
韩长林:“我到朝鲜不久,赶上仁川战役。在那次战役中我被俘了。”
[韩长林神色黯然,吸了几口烟之后,语气低沉地说]
韩长林:“马厂长,在景阳镇,除了家人之外我就认识你一个人,家人我还没找到。你比我大,是我的兄长,又是我的上司。有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四十年了,今天见到你,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也只有向你说了。”
[马洪伟点头表示理解]
[韩长林又吸了一口烟,显然感到那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他那张在烟雾缭绕中有点变了形的瘦削的脸上凝结着痛苦、悔恨、企盼和希望。思索良久,他才重新开口]
韩长林:“马厂长,我对不起家乡父老,愧对东北乡亲呀。我当战俘的事你们大概早就知道了。我在战俘营里几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可是吃苦受罪的不光我一个。千不该万不该我后来没和同志们一块回祖国来。我请求留在了南朝鲜。我感到无颜面见乡亲。这也是我这么多年迟迟不敢回来,甚至不敢同家里联系的原因。”
马洪伟:“不不,应该回来,应该回来!回来就好。这么说韩先生是从景阳镇参军的了?”
韩长林:“是的。”
马洪伟:“你走的时候家里都有什么人?”
韩长林:“我的家里就我老婆一个人,我们结婚不久。我还有一个弟弟跟我们一起过。我们老家兄弟三人,我行二,人称我老两。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到中国来的时候,我大哥和姐姐留在了朝鲜,就我和老三跟随父母亲过来了。父母亲早就过世了。”
马洪伟:“你的三弟在哪儿?”
韩长林:“我走的时候他在景阳镇,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四十年了,他应该早就成家了。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打听我的妻子和三弟的消息,来看看他们。”
马洪伟:“只要他们还在,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他们的,这你放心。我想,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他们也不会不在。”
韩长林:“一晃四十年了。人这一辈子,也不过就这么三、四十年的事,是悲是喜,是福是祸,往往就是一步之差。当年我参加志愿军不光是响应号召,也是想到朝鲜去看看我大哥和大姐。不想朝鲜分成了南北两半,南北朝鲜两个世界。他们是在南朝鲜,不但见不着面,连打听都没法打听。后来我成了战俘,心想这回这条命算是白扔了,两头都够不着了。没曾想我命大,居然没死。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希望。停战后遣返战俘的时候,我说我在南朝鲜有亲人,要求不回中国,也就把我留下了。”
马洪伟:“你找到他们了吗?”
韩长林:“他们我是找到了,可是这边我又回不来了。唉!”
马洪伟:“世道兴衰,悲欢离合,古今中外都在所难免。不用说在两个国家,就是在一个国家里这种事也不少。现在好了,朝鲜不打仗了,中国也安定团结了,最近这几年实行改革开放,出国旅游,回国探亲的越来越多。许多分别几十年的亲友都重新团聚了。韩先生既然回来了,就多住些日子。我回去就帮你找人。”
韩长林:“那就拜托马厂长了。我一回来就和镇上的官员说我是回来探亲的,可是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他们说可以帮助我找人。等我一提起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也难怪,那时候他们还是孩子,有的还没出生呢。别说他们,连我自己都认不出地方了。这景阳镇变化真是太大了。”
马洪伟:“要说变化大主要还是改革开放这几年,不光是经济形势变了,人的思想也变了。现在这些人活得多带劲,跟咱们那时候可不一样了。”
韩长林:“是呀!咱们活了这么大年纪,吃苦受累一辈子,现在才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咱们也该好好活几年了。”
[他乐呵呵地抓住马洪伟的手]
韩长林:“今天见到你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我心里实在高兴。今天你就
在这里吃饭,咱们一块喝两盅,好好唠唠!”
马洪伟:“好,好啊!找人的事你放心,我会帮你找,镇上也会帮你的。他们虽然年轻,可是认识的人多,办法也多,一定能帮你找到。”
韩长林:“放心,放心!”
8、“林业工人报”编辑部
[姜文启来到编辑部大办公室]
姜文启:“老郑,你的印刷机买来了吗?”
郑魁松:“买来了,正在安装呢。”
姜文启:“那就好,咱们林业报的国庆专刊也编好了,这回可以出个新版面了。能印套色的吧?”
郑魁松:“能,买的是进口海德堡印刷机,自动调尺寸,自动调压力,自动调拉规。跟那老印刷机比,这回是更新换代了。”
姜文启:“多少钱?”
郑魁松:“买了两台,总共七十六万。”
姜文启:“两台七十六万?不贵。”
郑魁松:“是不贵,因为不是新的。”
姜文启:“为什么不买新的?”
郑魁松:“新的一台就得超过一百万。咱们这两台都有八九成新呢,合算。我还考虑,咱们套色印刷的技术还没掌握,先用这个旧的练练兵,等技术过关了,再买好机器也不晚。”
姜文启:“也行,目前只要把国庆专刊印好了就行。”
郑魁松:“那没问题。国庆专刊的稿件都齐了?”
姜文启:“齐了,版也基本排好了。”
郑魁松:“我上印刷厂去看看,催他们快一点。”
9、林业局印刷厂
[印刷厂工人和哈尔滨来的李技师一起在调试新机器。郑魁松来到车间]
郑魁松:“怎么样了?”
大班长:“这机器有点问题。”
郑魁松:“什么问题?”
大班长:“两台机器,我们先装的是这台对开的,机器装好了,可是套印彩色出不来。”
郑魁松:“为什么?”
李技师:“设备太陈旧,机件不灵活了。”
郑魁松:“你们厂怎么能用呢?”
李技师:“我们根本不用这种机器。这种机器早就淘汰了。”
郑魁松:“瞎说八道!这是进口机器还能淘汰?那台呢,怎么样?”
李技师:“那台四开的应该没啥问题。”
郑魁松:“你们厂有没有套印的配件?”
李技师:“应该有,但不知道能不能用。”
马洪伟:“日本人肯定有过,以前镇西边有个开拓团,都是日本人。还有日本人在镇上租老百姓的房子住呢。”
马 军:“您见过?”
马洪伟:“那还能没见过?那么多日本人。”
马 军:“噢,说不定他要找的那个人,您还认识呢。”
马洪伟:“是呀,很可能认识,所以我得帮忙找一找。认识的就好找,就怕不认识。”
4、林业局印刷厂
[林业局印刷厂的工人和哈尔滨来的李技师一起在安装调试新买来的印刷机]
小 郭:“师傅,您是哈尔滨印刷厂的吗?”
李技师:“哈尔滨印刷厂多了。”
小 郭:“那您是哪个印刷厂的?”
李技师:“我是哈尔滨前进印刷厂的。”
小 郭:“前进印刷厂?你们厂印报纸吗?”
李技师:“我们不印报纸。”
小 郭:“你们都印什么?”
李技师:“我们印的东西多了,书、杂志、广告,也有报纸,小报。”
小 郭:“那些东西好印。”
李技师:“好印?这些东西最难印,尽是套色的,还不好装订,比印报纸复杂多了,报纸是最好印的。”
大班长:“比较起来,印报纸技术最简单。”
李技师:“对。其实你们光印报纸的话,用不着这么高级的印刷机。”
小 周:“那为啥?”
李技师:“印刷的技术复杂在套色,报纸是单色的,就用一种墨色,用不着调色彩,那还不简单?”
大班长:“现在的小报都是花里胡哨的,大报肯定也得套色,以后恐怕不再是单色的了。”
小 郭:“别的颜色没有,红色总得有,报头,大标题。”
小 周:“对,这回国庆节就得用上。”
大班长:“厂长说了,国庆节要出专刊。”
5、景阳宾馆
[马洪伟来到景阳宾馆。他在总台前向服务员问道]
马洪伟:“我是马洪伟,听说有位外国朋友要见我,请问他在哪儿?”
服务员:“噢,您是马书记!请跟我来。”
[服务员把马洪伟领到二楼客房。客房是大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客厅有沙发、茶几、彩电、冰箱]
服务员:“外宾马上就回来,请您先休息一下。”
[服务员说着从冰箱里取出一罐饮料,噗地打开盖子倒进玻璃杯里双手递给他,然后转身离去了]
[片刻之后,外宾回来了。马洪伟连忙站起来]
[外宾身材瘦削,穿着西服,胡子刮得光光的。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外宾老人的眼睛就盯住了马洪伟,定定地,且不说话,像在辩认,在回忆,直到两人的手握在一起了还没说出话来]
马洪伟:“对不起,我不会说日本话。你是……”
[这时却听外宾突然用中国话说]
外 宾:“对!马先生,是马先生,马厂长,马洪伟厂长!”
[马洪伟惊异不已]
[外宾拉着马洪伟坐下来,从容地解释]
外 宾:“你肯定把我当成外国人了,是吧?外宾嘛。我又有点像日本
人。其实,我是当地人,就是景阳镇的,咱们是老乡呀!”
马洪伟:“你是……”
外 宾:“我叫韩长林,排行老二,那时候都叫我韩老两。”
马洪伟:“韩老两!?你怎么认识我?”
韩长林:“我在你手下当过工人呀!那时候你是景阳镇木材加工厂的厂长。我在加工厂当过工人嘛。”
马洪伟:“是吗?什么时候?我怎么不记得了?”
韩长林:“是呀!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十年以前了!”
马洪伟:“四十年以前?”
韩长林:“对!是四十年以前了。”
6、回放 字幕1950年
景阳镇木材加工厂的储木场
[清晨,景阳镇木材加工厂房顶的汽笛鸣叫,笛声在小镇上空回荡]
[工人们脚步匆匆地走进加工厂大门]
[储木场上的木材堆积如山,有成材,更多的是原木。小火车响着尖厉的汽笛在楞垛之间穿行]
[储木场里的工人有的在归楞,有的在卸小火车,有的在装大火车和汽车]
[全场只有一台小吊车在装车,其它地方都是人工干活]
[加工厂车间。数台电锯同时开动,电机轰鸣,锯沫飞溅,一根接一根原木被推上锯台锯成小方或板材,然后装上平板车运进储木场。
[在一个楞垛跟前,八个戴着肩墊的工人分别站在一根粗大的原木两边,铁钩挂上原木,扁担搭上肩膀,一声吆喝,原木被抬离地面。在一个领头人的带领下,八双脚迈出沉重而又坚实的步子,同时,低沉的、压抑的但又是浑厚有力的号子声迸发出来:
“哎——扛起来喽!嗨——向前走吧!嗨——站稳脚呀!嗨——迈小步呀!嗨——别松劲儿呀!嗨——走上坡呀!嗨——加小心哪!嗨——齐使劲儿呀!嗨——上了车呀!嗨——轻放下呀!嗨——”……
[这一组人抬着原木一步步走上踏板,走上火车的车厢,放下原木,号子声也就停止,摘下挂钩,抽出扁担,下车去抬另一根原木]
[这其中的一个人就是韩长林]
回放完
7、景阳宾馆 韩长林客房
马洪伟:“对,对,是木材加工厂。那时候刚解放,还没成立林业局,就是个木材加工厂,人也不多,条件不好,工人干活很苦,也没有机械。”
韩长林:“那时候厂里工人有好几百,我干的时间又不长,你不会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因为你是厂长。”
马洪伟:“那你现在是从哪儿来的?怎么又成了外宾了?”
韩长林:“马先生可能不知道,我虽是咱们景阳镇的老乡,但我不是中国人。怎么说呢?我先是朝鲜人,后来是中国人,现在呢,我又是朝鲜——噢不,是韩国人。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祖先是朝鲜人。在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家里人从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半岛跑到了中国东北,在东北一路逃荒来到景阳镇,在这里落了户。后来中国东北也给日本人占了,咱们都成了亡国奴,一直到苏联红军解放了全东北。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一去就没回来。”
[韩长林说到这里停下来,脸上现出苦涩的神情,似有难言之隐]
[韩长林掏出香烟,先给马洪伟抽出一支,马洪伟谢绝了,他便自己叼在嘴里。当他打火点烟的时候,马洪伟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抖]
[他吸了一口烟之后说:
韩长林:“我到朝鲜不久,赶上仁川战役。在那次战役中我被俘了。”
[韩长林神色黯然,吸了几口烟之后,语气低沉地说]
韩长林:“马厂长,在景阳镇,除了家人之外我就认识你一个人,家人我还没找到。你比我大,是我的兄长,又是我的上司。有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四十年了,今天见到你,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也只有向你说了。”
[马洪伟点头表示理解]
[韩长林又吸了一口烟,显然感到那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他那张在烟雾缭绕中有点变了形的瘦削的脸上凝结着痛苦、悔恨、企盼和希望。思索良久,他才重新开口]
韩长林:“马厂长,我对不起家乡父老,愧对东北乡亲呀。我当战俘的事你们大概早就知道了。我在战俘营里几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可是吃苦受罪的不光我一个。千不该万不该我后来没和同志们一块回祖国来。我请求留在了南朝鲜。我感到无颜面见乡亲。这也是我这么多年迟迟不敢回来,甚至不敢同家里联系的原因。”
马洪伟:“不不,应该回来,应该回来!回来就好。这么说韩先生是从景阳镇参军的了?”
韩长林:“是的。”
马洪伟:“你走的时候家里都有什么人?”
韩长林:“我的家里就我老婆一个人,我们结婚不久。我还有一个弟弟跟我们一起过。我们老家兄弟三人,我行二,人称我老两。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到中国来的时候,我大哥和姐姐留在了朝鲜,就我和老三跟随父母亲过来了。父母亲早就过世了。”
马洪伟:“你的三弟在哪儿?”
韩长林:“我走的时候他在景阳镇,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四十年了,他应该早就成家了。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打听我的妻子和三弟的消息,来看看他们。”
马洪伟:“只要他们还在,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他们的,这你放心。我想,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他们也不会不在。”
韩长林:“一晃四十年了。人这一辈子,也不过就这么三、四十年的事,是悲是喜,是福是祸,往往就是一步之差。当年我参加志愿军不光是响应号召,也是想到朝鲜去看看我大哥和大姐。不想朝鲜分成了南北两半,南北朝鲜两个世界。他们是在南朝鲜,不但见不着面,连打听都没法打听。后来我成了战俘,心想这回这条命算是白扔了,两头都够不着了。没曾想我命大,居然没死。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希望。停战后遣返战俘的时候,我说我在南朝鲜有亲人,要求不回中国,也就把我留下了。”
马洪伟:“你找到他们了吗?”
韩长林:“他们我是找到了,可是这边我又回不来了。唉!”
马洪伟:“世道兴衰,悲欢离合,古今中外都在所难免。不用说在两个国家,就是在一个国家里这种事也不少。现在好了,朝鲜不打仗了,中国也安定团结了,最近这几年实行改革开放,出国旅游,回国探亲的越来越多。许多分别几十年的亲友都重新团聚了。韩先生既然回来了,就多住些日子。我回去就帮你找人。”
韩长林:“那就拜托马厂长了。我一回来就和镇上的官员说我是回来探亲的,可是不知道亲人在哪里。他们说可以帮助我找人。等我一提起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也难怪,那时候他们还是孩子,有的还没出生呢。别说他们,连我自己都认不出地方了。这景阳镇变化真是太大了。”
马洪伟:“要说变化大主要还是改革开放这几年,不光是经济形势变了,人的思想也变了。现在这些人活得多带劲,跟咱们那时候可不一样了。”
韩长林:“是呀!咱们活了这么大年纪,吃苦受累一辈子,现在才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咱们也该好好活几年了。”
[他乐呵呵地抓住马洪伟的手]
韩长林:“今天见到你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我心里实在高兴。今天你就
在这里吃饭,咱们一块喝两盅,好好唠唠!”
马洪伟:“好,好啊!找人的事你放心,我会帮你找,镇上也会帮你的。他们虽然年轻,可是认识的人多,办法也多,一定能帮你找到。”
韩长林:“放心,放心!”
8、“林业工人报”编辑部
[姜文启来到编辑部大办公室]
姜文启:“老郑,你的印刷机买来了吗?”
郑魁松:“买来了,正在安装呢。”
姜文启:“那就好,咱们林业报的国庆专刊也编好了,这回可以出个新版面了。能印套色的吧?”
郑魁松:“能,买的是进口海德堡印刷机,自动调尺寸,自动调压力,自动调拉规。跟那老印刷机比,这回是更新换代了。”
姜文启:“多少钱?”
郑魁松:“买了两台,总共七十六万。”
姜文启:“两台七十六万?不贵。”
郑魁松:“是不贵,因为不是新的。”
姜文启:“为什么不买新的?”
郑魁松:“新的一台就得超过一百万。咱们这两台都有八九成新呢,合算。我还考虑,咱们套色印刷的技术还没掌握,先用这个旧的练练兵,等技术过关了,再买好机器也不晚。”
姜文启:“也行,目前只要把国庆专刊印好了就行。”
郑魁松:“那没问题。国庆专刊的稿件都齐了?”
姜文启:“齐了,版也基本排好了。”
郑魁松:“我上印刷厂去看看,催他们快一点。”
9、林业局印刷厂
[印刷厂工人和哈尔滨来的李技师一起在调试新机器。郑魁松来到车间]
郑魁松:“怎么样了?”
大班长:“这机器有点问题。”
郑魁松:“什么问题?”
大班长:“两台机器,我们先装的是这台对开的,机器装好了,可是套印彩色出不来。”
郑魁松:“为什么?”
李技师:“设备太陈旧,机件不灵活了。”
郑魁松:“你们厂怎么能用呢?”
李技师:“我们根本不用这种机器。这种机器早就淘汰了。”
郑魁松:“瞎说八道!这是进口机器还能淘汰?那台呢,怎么样?”
李技师:“那台四开的应该没啥问题。”
郑魁松:“你们厂有没有套印的配件?”
李技师:“应该有,但不知道能不能用。”
上一集
下一集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