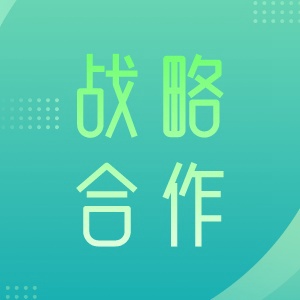权属:原创 · 独家授权
字数:31722
阅读:6404
发表:2020/5/19
农村
小说
占地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刘大外出打工,直到结识了小六子。那段故事,村里人至今没人想提起,也没有人有勇气和小六子说起,闹归闹,小六子听说丈夫的故事,也挺同情,可同情理解没有用啊,法律上还是不承认啊,搞不好刘大还要被清算历史帐,还得坐牢,要是不解决这事儿,就眼睁睁看着人家分钱分房,自己没有份儿。
摆在刘家人面前的难题,犹如一座大山,挡住了通往幸福的路。
正在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个自称是刘大媳妇的人,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回来认祖归宗,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就是刘大原来失踪的那个媳妇。法律上人家才才算正牌媳妇。
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何况是有这么深的积怨,那天晚上刘三婶子的小饭堂没有开,估计是怕看热闹的人太多。二娃和狗蛋,又拿出小时候的强项之一――扒墙根儿,刘家整夜灯火通明,叫骂声时而激烈,时而平缓,好不热闹。
第二天一大早,就听左邻右舍议论,这女人是来分家产的,人家还带着正宗的刘家男丁,肯定少不了人家的份儿。可这时候回来也不地道呀,估计也是趁火打劫来的,当然这只是人们的猜测,众说纷纭。
果然,没过几天刘三婶子给出了答案,这女人也是听说我们村拆迁的消息回来的,明确的说,冲钱来的,要求和刘大平分。小六子当然不同意了,自己是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家产是他和刘大大打拼来的,怎么能拱手送人。那女人说只要分了钱就立马和刘大办理离婚手续成全他们,自己这么多年给刘大带孩子,抚养费也值那么多钱了。况且当年跑回去以后,突然带回个儿子,那边的婆家接受不了,她就离婚了,在当地又找了一家。但又找这家的男人不争气,一直过得很清苦,也是无意中听当年拐卖她的表姐夫说起拆迁的事儿,才想起了这么一出。历史的悲剧,现实的难题,如阴云般笼罩在刘家人的心头。
一连几天,刘三婶子都四处奔走,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女人带着孩子也就暂时居住在刘家,小饭堂忙不过来时还会搭把手,而他的儿子和小六子生的女儿原本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两个孩子玩的还挺投缘,一场暴风雨,暂时停歇了,但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个开始。
这事儿如果这是放在古代就好办了,一夫多妻,问题迎刃而解,或男方一纸休书也没有什么闹腾的理由,那时的社会男人就是天,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男权主导的社会可惜一去不返。
两个女人,两个情敌同在一个屋檐下,法律上的正室与实际上的正室,激烈的交锋几乎天天上演。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脸嘲讽和轻蔑,就可能招来一场言语冲突,甚至是肢体冲突,刘三叔和三婶儿,就是消防队员,随时准备灭火。
几天下来,家里所有的人都瘦了一圈,只有那小兄妹俩玩得更加熟络,还别说他俩不仅长得有相似之处,小男孩儿洋洋还挺会关心妹妹小雨。他们俩融洽交往像极了两个敌对的国家,官方高层已经绝交,惟有民间人士不问政事,仍然保持良好的沟通,仍留一线复合的生机。
经过多方求证,最终还是采取了村里最流行、最通行,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议事方式,请村里最德高望重的长者及村长共同商定,据说非洲部落也是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
是夜,刚下过小雨的草原上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小池塘,青蛙们争先恐后的嚎叫,伴随着花草芬芳,和泥土的清香一并袭来,一片蛙鸣声衬托的夜更加宁静了。然而人们都没有欣赏这美妙夜色的心情,全村人都牵挂着这场旷世的谈判,这是村里最头条的新闻了。
北方大土炕,四方炕桌摆上,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三位长者,二爷、宝爷和何顺爷,村支书二红旗也在列,刘三叔,刘三婶,刘大以及两位当事人小六子和四川女人。
二爷清了清嗓子,首先发话了:“今天我们过来主要是商量刘大一家的户口及财产分配问题,这是我们村延续百年的议事传统。我们村是山西人走西口的后裔,我们村的祖上大部分是商人和手艺人,在和当地的蒙古人相互交流接触过程中,矛盾经常会发生,那咋办呢?我们是外来户,硬打硬拼不行。所以这种长辈议事就成了我们解决麻烦的主要办法,我们的原则是不粗暴,不出格,和平解决,现在开始吧。”
村支书在这种场合下一般都是主持人,二红旗刚上任没多久,处理这么棘手的问题还是头一次,先各自陈述。
四川女人:以前是历史原因,我是你们买来的,也是办过正经法律手续的,就是合法媳妇儿,况且儿子的血脉是老刘家的,我自己带了这么多年,抚养费也有很多了,我现在和以前的男人也分了,这都是给你们生儿子的后果,显然我是受害者,以前知道咱这儿穷,我也没和你们闹。现在马上要拆迁,有钱了,我肯定要把你们对我的伤害弥补一下,如果我要是去告刘大买卖人口,刘大早已经坐牢,念及孩子的血脉亲情才没有告发,用刘大一半的财产作为补偿天经地义。
女人边说边哭,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二爷和和顺爷的眼眶也红红的。
接下来轮到小六子了,连日来,哭得眼睛红肿的小六子声音嘶哑,她阐述的意思大致如下:
我和刘大在深圳打工时认识,当时我们没有结婚就同居了,一年以后有了孩子,当时家里困难,简单的仪式,就算办了喜事儿了,最关键的是把日子过好,我几次催刘大领证,他只说离我们工作地太远,一年回去一次就是春节,我们当地的机关单位这个时候也放假了,办不了证。这一拖就是几年,后来慢慢发现,我们周围这样没办证的很多,在大城市,也是一种流行时尚,我们也就没有了紧迫感,要不是这次拆迁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孩子已经6岁了跟刘大已经过了七八年了,好不容易打拼的有点样子了,又赶上拆迁,原本以为是老天眷顾我们,没想到出了这事儿。我不了解以前你们是啥样的,但这么多年,我才是刘大的正牌儿媳妇,我的劳动果实凭啥让别人不劳而获?穷的时候不来,看见有利可图了就来了,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小六子从小在城市里生活,家里把她娇惯的像个小公主,哪受过这气,说到动情处哽咽的不能出声,刘大呢,看着两个女人,又看看父母,看看其他人,无言以对,平时能说会道的刘三婶,这时候也哑火了,脸涨的通红。倒是平时老成持重不善言谈的刘三叔,这会儿开口了,颇有大将之风:
孩子们,你们两个其实都是受害者,其实错不在你们,在我们老两口,当时咱穷没本事,给孩子娶不起本地的媳妇,只有花小钱买远地儿的,当年在咱这儿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也有很多人留下来过得很好,但当年我们的情况特殊,没能把你留下,还把孩子也带走了,我们老两口当时死的心都有,都是为人父母的,谁不想着自己的孩子啊。
刘三叔慢条斯理的说着,也动了些许的情绪。他接着说:
至于小六子就更无辜了,当时你知道刘大这个情况,还会跟他吗?十几年了,村里的人都守口如瓶,怕破坏了你们的幸福,但事已至此,无需再遮遮掩掩的了,你们都是受害人,错在我们老两口,错在我没本事才酿成了今天的大祸。
他转脸又对四川女人说:我想你也别和刘大分了,我们还有两套房子呢,分一套给你弥补我们的过错,也弥补对你的伤害,但孙子我们得留下,这是我们老刘家的骨肉。
众人诧异的是,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说起话来也是这般有条有理,三位长者和村支书都频频点头称是,各方观点都放到了桌面上,就看大家接不接受了。
那四川女人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她又说,孩子是我自己带大的,这么多年是我的心头肉,不可能给你们,除非他成人了让他自己选,光一套房子解决不了问题,补助款也要有我一半,出口就是一股辣椒味,川妹子果然够泼辣。
几方唇枪舌剑,交锋激烈,几番下来,听说小六子几度失控,差点上演了全武行,最后经过一夜的争论,最终达成的协议是:
刘大拿出将来1/5的拆迁款,作为对孩子的抚养补偿费,刘三叔老两口拿出将来要拆迁的一套房和老两口的补偿款的一半,作为补偿,孩子过了18岁,自己选择归属,但每年必须带孩子回来住一个月培养感情,必须解除和刘大的婚姻关系,才能享受上述的补贴。
那女人一看,见好就收吧,也就答应了。小六子也因为能领结婚证了,才能有自己的那一份,毕竟还是自己拿的多,就也不纠缠了。毕竟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就让他见历史去吧,至于刘三叔老两口虽然损失最大,但错误是自己犯下的,权当赎罪,权当给了孙子,刘三婶儿现在又是佛教信徒,相信破财免灾。
一场本村历史上最大的财产纠纷案竟被最古老最土的法庭给解决了,遥想那些法律不健全的动荡年代,这种古老的模式,帮助过很多人,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据说这种方式在韩国和日本的古村落仍有延续。
一场户口纠纷,一段痛苦的回忆,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次古老与现代的碰撞,虽然解决了,相信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对历史教训的思考。人们知道在城镇化改革的大潮中,像我们这样的小村落,只有自生自灭,也许以后在任何的文献中都不会找到只言片语,但在我们心里,永远是不可忘记的故乡。
第四章:二娃相亲
百十多户人家的村庄,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在这样一个一度以农业立国的国度里,农村人的比例一度达到70%以上,传统的农耕文明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时至今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还有农耕的思想烙印。农耕文化和思想是我们的特色,但也常常遭受国人的诟病,自给自足,裹足不前是最典型的表现。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亦是如此,清朝的“闭关锁国”,招致百年的屈辱,就是典型的小农思想在作祟。
文化的融合与侵略,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往远了说,如蒙古人用铁骑统治了天下,可汉族人用文化同化了蒙古人;往小了说,如我们的乡野小村,几乎一夜之间就被城市的文化浸染,蜕变,直至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
二娃原本是村里的留守小伙,之前远近的人,嫌贫爱富,避之不及。二娃爹托了好多人说媒拉线,人家一听是“留守小伙”便摇头拒绝。如今,二娃家也有了两座房,一座是用父子俩给人打工挣来的钱修的小二楼;一座是祖宅,有比别人家大三倍的祖屋。而且他们现在还小有积蓄,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最多的一天接待了三拨提亲的,还有一个是邻村的远房亲戚家刚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
二娃如相亲的道具,赔笑的工具。二娃娘和邻居几个婶子是主厨,这是农村人的传统,大凡哪家有红白喜事,左邻右舍都会自愿帮忙。厨房帮忙端茶倒水,没有一个人会计较得失,干活为主,吃喝靠后,大家都无怨无悔,甚至比自家人办事更热心。这就是农村人,有别于城里人的地方。
现在的城里人电话本里存了几百人的号码,可没有一个是邻居的。铁护窗,防盗门,出门进门常相见却无言以对。
城市里人多了,人情味儿少了;车多了,步行的人却少了;高楼多了,平房少了;柏油路多了,绿地却少了;人被迫逼上了如鸟笼般的楼阁。思乡的老人总是占用小区的绿地,种瓜种菜,因为那是他们年轻时代生存的技能,是一种生活习惯,亦演变为一种本能。即使上了楼也念念不忘两亩田。
书归正传,留守小伙二娃,连自己也认为桃花运要来了,姻缘要来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二娃已经累计相亲上百次,是二娃变帅了吗?是二娃有了魅力了吗?是现在的女孩儿开始喜欢农民了吗?
二娃根本来不及想这些,只顾走马灯似的相亲相亲,再相亲了。印象中记得名字里带“花”的就有18个,带“叶”的有15个,另外还有听起来像外国名字的玛丽,爱丽丝等等,这些女孩儿的出现,虽然失败者十之八九,然而,突然间让二娃有些傲娇了。原来拆迁是让他有资格谈恋爱相亲的资本,留守了那么多年,并不是祸,反倒感觉幸福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而桂枝却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心坎里,他心里的桂枝只是以前那个温婉,略带娇羞的女子代名词。而不是眼前这个大方的让人窒息的女痞子。
人真的很善变。有道是,人之初性本善。可被外面的红尘世界浸染过的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轻浮,那么让人怜悯生厌。二娃替她流过泪,就像当初桂枝一家要搬到外地一样,二娃无力挽留,而此刻比挽留更难的是没办法抓住她的心。
如果人生可以随意的快进,快退的话。二娃希望尽快过了这一段,一下子到了垂垂迟暮,人们也就不会在意这浮华的一切了;要么可以倒退,二娃就是跪着也要祈求桂枝的爹娘不要离开村子。然而说什么都没用了,木已成舟。
是夜,二娃想到这些心如刀绞,又想着那些相亲对象没有一个让他动心的,场面挺热闹,可实际上离谈婚论嫁还遥遥无期。
他拎着半瓶二锅头,边走边喝,他想麻醉自己,想让自己的回忆和懊悔都随酒咽下肚子。新修的一幢幢新楼,睁着恶魔般的双眼,满身散发着水泥和贪婪的味道。整条新街上只有零星点缀的老房子里透出灯光,衬托出一个出奇安静的夜。
三婶的小饭堂,这几天也没有营业了,大概这几天又闹腾上了。
突然墙边窜出一条黑影拦住了二娃的去路,二娃吓的一激灵。心想,村里怕是来劫匪了吧?还是自己撞邪了,手里的酒瓶抓紧了,随时做好还击的准备。
“二娃是你吗?你喝多了吗?我呀,桂枝”一个女人的声音,娇滴滴的传入了耳朵里。
“哦哦,是桂枝啊,我以为抢劫的,你干嘛这么晚了不睡觉呀?”二娃睡眼朦胧的懒懒地说。
“我,呜呜呜……”桂枝呜呜咽咽的哭了出来,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桂枝桂枝,你别哭啊!”二娃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赶紧过来安慰,一把把桂枝揽入怀里。
桂枝本来就出脱的好,水蛇腰,瓜子脸,浓眉大眼。比小时候更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味道,一股女人体香直刺脑海,雄性的荷尔蒙在二娃的身体里升腾……
“桂枝,桂枝,你别着急,怎么了?慢慢说”理智告诉二娃要镇静。
桂枝只是哭,把头深深埋在二娃的臂弯里,从哽咽到放声大哭,泪水滂沱,如下了一场暴风雨。二娃从来没见过女人哭的这么伤心,还在自己的怀里,他一下子慌了手脚,可又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像木桩一样站着,左手拍着桂枝的后背,右手还拿着他的酒瓶子。
过了许久,二娃只觉得腿都麻木了,桂枝才从暴风雨逐渐成了小雨,哽咽着抽泣着,慢慢扬起脸看着二娃。却看到二娃像个被吓傻的小羊羔站的直直的,又像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任由她依靠着压的弯弯的,她忍不住破涕为笑。这一哭一笑弄得二娃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
那究竟桂枝到底为什么哭呢?原来她家里老是催婚,连日来,让她很烦心。傍晚吃饭的时候,父母又提起这事儿,还说了几句重话,让她很是伤心。
出来散步的时候无意间看见喝闷酒的二娃一时间心中的积怨才得以宣泄。
原来,桂枝八岁那年随父母移居外地,父母靠打工为生,自然也就居无定所,先上了打工子弟学校,到了初二,因父亲意外摔伤而辍学回家。那时母亲要给别家当月嫂养家,没有人照顾父亲。弟弟刚上小学四年级,懂事的她主动要求辍学照顾家里。一年多的时间,父亲逐渐康复,虽然多次催促她复课,可她却不想上学了,她想打工赚钱,和父母一起养家供弟弟上学。
就这样,桂枝开始了打工生涯,先在父亲认识的朋友那里学美容,后来美容院关门了,又做超市促销员,自学会计。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广东东莞。这个中国制造业中心,是无数人梦想的淘金地。
凭借自学的会计知识,桂枝在一家小型的工厂里当起了会计。可三年过去了,非但工资没涨多少,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自己花,而且流水账会计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她想换份工作。
这时,一家刚营业的娱乐会所招聘前台收银员的广告映入了眼帘,当时的工资竟然高达4500元/月。她认为,要去试试才知道行不行。
没想到,她的好身材和标志的五官,就是她通过面试的资本。就这样,她当上了那家新娱乐场所的前台收银。
“那后来呢?”二娃不想听桂枝慢条斯理的讲,急切的追问道。
不知不觉已过午夜,二娃和桂枝又像小时候一样坐在一起玩弄着小石子促膝长谈。对于桂枝嘴里的外面世界,二娃只是个听众,故事里各种身份,各种场所,他只能听个大概,桂枝讲的很生动,她的经历也够坎坷,一个女孩子在外地打工,着实不易。
“后来你不都知道了吗?”桂枝说道。
“什么啊,我哪知道”二娃还是傻傻的问。
“后来,东莞被扫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就你傻啊!”桂枝杏眼圆睁,轻轻的责怪道。
“哦哦,你说的是东莞扫黄吧,你被抓了吗?哈哈”二娃故意调侃道,他好像要得到什么答案似的。
“你个死二娃,叫你胡说,叫你胡说”桂枝的粉拳如雨点般在二娃的胸口落下,可一点儿都不疼,二娃咧着嘴嘿嘿地笑了起来。
二娃试探性的问道:“那我听村里人说,你是那个……”
“不是”桂枝厉声喝道。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是我在的那家会所被查封了,我只是个前台收银,接待,接待,你懂吗?会所涉黄,老板涉黄,但不等于所有人都涉黄啊!村里人道听途说能信吗?我什么都没干过,你信吗?你信吗?”桂枝说得很认真,语速很快,像连珠炮一样。
“我知道从那种地方回来的人名声都不好,我也是担心名声问题才回来的,父母亲人都说我了,他们以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难道东莞回来的就是小姐吗?所有人都在歧视我,所有人都在嘲笑我,戳我的脊梁骨,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做错什么了?”桂枝边说边又开始委屈的流泪。
“当初父亲看病要钱,弟弟上学要钱,不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我至于退学吗?干个高一点工资的工作有错吗?只是个场所涉黄,我又不知情,我没做鸡也没被人包养我干什么了?你们这么看我……”呜呜,情到深处,桂枝又泣不成声。
二娃定下神来,想想自己也没亲眼见过桂枝做小姐啊,只是听村里人道听途说,她是被从东莞扫回来的,如何如何……而村里人也没见过啊,无凭无据,凭什么毁一个姑娘的清白声誉呢?想着想着二娃竟然有些气愤。
他支支吾吾的说:“桂枝,我我,我这不也是听村里人说了闲话吗?其实家里给我相了那么多,我都没答应,其实其实……”二娃的脸涨的通红,和猪肝一样。
“其实什么?”桂枝突然扬起脸死死地盯住二娃的双眼,如两道激光束一般。
“其实什么?你说啊!”桂枝继续追问道。
“其实,其其其实,我我心里一直都有你。但我以为你变坏了,我还是喜欢以前的你。这么多年都想,我二娃没本事,去不了大城市,只能当一辈子农民。我知道,和你交往,是一种奢望,我还听信别人,不待见你,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真的……”二娃喃喃着,一直在后悔自责。
继续说道:“我,我,一直很喜欢你。小时候,你们家搬走的时候,我就想把你留下来,留下来……”二娃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和自己说话,生怕被桂枝笑话。
但二娃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一口气说出了心里的话,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二娃激动的热泪盈眶,这个年届三十的西北汉子,从来不会把儿女情长挂在嘴上。贫穷甚至让他连个谈恋爱的机会和资格都没有。人家女孩儿,不光是看不上这块贫瘠的土地,更看不上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坚守清贫的人。
留守小伙就该被人歧视吗?只要是身心健康的人都有一种渴望。渴望被认可,渴望被接纳,渴望有谈恋爱的机会。而不是有房有车有存款,才能有资格谈恋爱。
“我爱你,桂枝,我爱你……”二娃终于肆无忌惮的喊出他心里珍藏了三十多年的话语,突然间的释怀,让他卸下了所有的包袱。激动,兴奋,渴望,自卑,胆小……各种情绪的交织下,让他像一只刚打完架的猫,鼓起的战斗激情还未平息,依然心有余悸。
“二娃,我也爱你。”不知什么时候,桂枝的两片朱唇已经奋力地吻上了二娃,她想用温柔来化解他的激动。而他却又觉得受宠若惊,恍若隔世。
南归的燕子和小家雀恋爱了,那种激动的心情无需赘述。只听的叽叽喳喳的两只小嘴,在浓重的夜色中显得分外响亮。二娃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美妙的感觉,桂枝温暖而柔和的唇,和她身上透出的阵阵摄人心魄的味道,让二娃心旷神怡,整个人都陶醉在这奇妙的幻境中。
二娃像一只刚出笼的猛兽,开始猛烈地攻击“猎物”,雨点一般的吻落在她的脸上,脖子上。此刻,也许只差了一只小小的火柴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新建起来的“纸片楼”似乎都在晃动,新鲜的水泥味夹杂着浓重的荷尔蒙气息,久久回荡在夜色中……
月光如雪般散满大地,花香草香泥土的香,和着清洁如洗的空气一并吹拂过来,深深地吸一口沁人心脾。霎时间,人的身心焕发出青春活力。
就在这美好的夜色阑珊中,二娃和桂枝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第五章:逼婚闹剧
最近村里又发生了一件荒唐事儿,83岁的二爷居然要和38岁的小六子结婚,这真的是要疯的节奏啊,为了拆迁款真是不择手段!
原来,四川女人暂时不想离婚,怕离了人财两空。可小六子,毕竟已经在村里盖好一座房子,不是本村人,房子盖了也白搭,是分不到钱的。不知哪个法律人士的支招,除非嫁给本村有户口的人才行,实际上就是假结婚。和中国人去外国办绿卡是一回事儿。
可回头看,村里的单身男性,都名草有主了。只有二爷早年丧偶,还是单身。小六子只能找二爷,参照的模板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翁帆,以及默多克和邓文迪之流。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83岁的二爷,和38岁的小六子要结婚?一时间“老少配”成了村里的大新闻,像一股泥石流席卷了整个村庄。大家虽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忍不住茶余饭后的调侃。
再说二娃和桂枝,自从他俩相好之后。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二娃换上早年买西装革履,还系上一条粉红色的领带,逢人便笑眯眯的鞠躬。人们问:二娃,你不热啊?只见二娃彬彬有礼的说,人家电视里上海滩的绅士就这么穿的,上海在南方,人家都不嫌热,我们这儿是属于北方,肯定不会热。再说了,当绅士就得有点规矩。
人们又是一通唏嘘。可二娃,哪管这些,只顾哼着小调,摇头晃脑的在街上转来转去。而桂枝想找个人尽快结婚,二娃也许正是她心目中的那个老实人,需求决定了一切。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桂枝却不见二娃来提亲。她哪里想到此时的二娃,正和自己的父母冷战。原因大家都知道,二娃向父母提出娶桂枝的想法,可二娃爹,一听就火了。说我们家世代清清白白,就是打光棍也不能娶个婊子回家呀,这不是辱没祖宗吗?二娃娘倒是没发表太强烈的意见,但也没有说同意。连着几天,二娃和父母不说话,一直持续性冷战。
二娃,又和桂枝约会,二娃婉转的表达了父母的意思。其实桂枝自己也心知肚明,可桂枝毕竟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一点儿都不慌张,她也知道,农村人保守封建。但她想,自己从小就和二娃青梅竹马,既然有感情,是不会被人拆散的。那就想办法说服二娃的父母吧。两个人坐在村边的大石头上苦思冥想。想来想去,只有二爷了,二爷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而且也是二娃爹最敬重的人。
简短的说,他们去找二爷,一通说服之后。二爷当然肯出面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后来他又去找了狗蛋儿,毕竟外面回来的人,总是见多识广,比村里人要强,此二人出马,一通唇枪舌剑下来,可二娃爹就是不同意。二娃和桂枝急得团团转。
之后,又找了村支书和刘三婶……二娃爹的态度坚若磐石,就是不答应。一拨又一拨的说客败下阵来,二娃爹稳如泰山,任尔东南西北风,兀自岿然不动。你有千般妙计,我只一计定心。
古代的崔莺莺、杜十娘之流不知是否也曾遇到过如此的境地。寒风冽冽,纵使有情人也难成眷属。谣言和世俗相遇,终究也逃不过的世俗的做法。也许爱情自古多磨难。可二娃和桂枝,现在显然已是强弩之末,黔驴技穷。桂枝不甘心,城市里那么多的追求者,自己都没看上眼。区区一个留守小伙,一个老实人,怎么就搞不定呢?她气的暗咬银牙。
二爷和小六子的结婚证已经下来了,据说,这对老少配年龄差距,打破了县城的纪录。为了让戏演得更真一点。二爷逢人便解释道:娃娃们盖房,分点补偿款不容易,二爷这张老脸不算什么,解决贫困才是关键啊。可调皮的孩子们还是给二爷编了一首童谣:
二爷爷,了不起,
八十三,把亲娶。
新娘子,三十八,
稀里糊涂把人嫁,
大老头,小媳妇儿,
老少配,顶瓜瓜,
就是能看不能睡,
不能睡呀不能睡……
二爷听得直皱眉头,边摇头边说:“现在的小孩子,真能起哄,这乱七八糟的都是谁教的?这帮小崽子们,真是欠收拾。”可村里的其他人,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这几天赶上干热,据说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高温已经逼近了40度,北方干旱少雨,地皮烤得冒火,光脚丫出去肯定就起泡了。听说刘三婶子为了办酒席,专门弄来一台透明的大冰箱,和两个饮料专用的冰桶,准备招待客人。小饭堂里的酒水生意,又开始风生水起,刘大隔一天就得去城里进货。
村里住着百十号子外地人,这几天,高温都停工,小饭堂的地方大,又有大风扇,又有冰啤酒,自然是个好去处。从早到晚,棋牌麻将声不断,推杯换盏吆喝声不断。猜拳行令,选酒司令,玩棒子老虎鸡的,小蜜蜂的,玩色子的,转筷子的,干瞪眼的,叫号翻牌的……凡是酒桌上能玩的花样,随便玩儿,中心议题就是喝酒消遣避暑。
这些过路财神凑在一起,真能造。村里好几户都养着羊,土鸡等等,他们一来,几乎隔一天就宰羊杀鸡,小饭堂里的手抓肉,炖羊肉,焖羊肉,涮羊肉,血肉肠,包饺子,大烩菜,羊肉炒粉,葱爆羊肉,黄焖鸡,小野鸡炖蘑菇,土鸡蛋都是用盆煮的……再配上菜园子里的水萝卜,黄瓜,韭菜,大葱,生菜,白菜等这些丰富的绿色蔬菜。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大吃大喝,钱当然多半是主家出的,谁盖房子,谁家出。
刘三婶子的莜面,那是令人叫绝。在第二季《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以后,莜面,这种号称最健康的粗粮美食开始走俏大江南北,这种只属于晋蒙一带的美食,开始风靡全国。据说上海还开了一家某某莜面村的饭店,年销量过千万,越来越多的地方美食开始全国化。刘三婶子施展出最拿手的技艺,推莜面窝窝,那是在搪瓷盆的底上完成的,一寸多高,整整齐齐的立着,满满的一笼屉,没有一个倒下的。恰似整齐划一训练有素的部队。上锅蒸熟,蘸着鲜美的羊肉汤,羊杂汤,或是由生菜,黄瓜等新鲜蔬菜拌好的凉汤吃,那叫一个惬意。一筷子窝窝下口,窝窝的眼里灌注了汤汁肆意在口中翻腾,舌尖上舌根下,顿生津香之味,来不及细嚼慢咽,便已下肚。好像肚子早已等不及了,看着客人们大快朵颐,刘三婶子骄傲的笑了起来,面如桃花。
莜面是好吃,可是纯手工做起来繁琐,还慢。所以每天限量10斤,其他的莜面鱼鱼、条条、片片,饸饹(都是莜面做成的不同形状)等不限量,让食客们吃了念念不忘。
一天,村里的人们大早起来就往二娃家里跑,听说桂枝上二娃家里闹事儿了,二娃的爹娘,早上刚起来,就看见桂枝披头散发的哭着跑来,口口声声说自己有了二娃的孩子,没脸见人了,进门就一屁股坐到炕上不走了,鞋也不脱就上炕头,哭得泪眼婆娑。
这一下,可把二娃的爹娘给吓坏了,连忙叫了二娃对峙,二娃只是不说话,很懵很无辜的样子,可是心里却丝丝窃喜。他暗地里给桂枝挑了大拇指,那意思是,你这家伙终于出大招了,真有一套。
二娃爹,一脸的怒气,狠狠给了二娃两个大嘴巴子,打的他眼冒金星,嘴角都淌血了,口里骂道:“你这没出息的货,见了女人就管不住裤裆啊,你也不睁睁狗眼,看看是不是能种的地,你真要气死老子啊,不要脸的东西,给我们老王家丢脸啊,你叫我百年以后,咋去见祖宗?你个不孝的逆子”说着又一巴掌,朝二娃劈头盖脸的打了上去,二娃娘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拼命的拉着他爹,怕他再打二娃。
摆在刘家人面前的难题,犹如一座大山,挡住了通往幸福的路。
正在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个自称是刘大媳妇的人,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回来认祖归宗,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就是刘大原来失踪的那个媳妇。法律上人家才才算正牌媳妇。
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何况是有这么深的积怨,那天晚上刘三婶子的小饭堂没有开,估计是怕看热闹的人太多。二娃和狗蛋,又拿出小时候的强项之一――扒墙根儿,刘家整夜灯火通明,叫骂声时而激烈,时而平缓,好不热闹。
第二天一大早,就听左邻右舍议论,这女人是来分家产的,人家还带着正宗的刘家男丁,肯定少不了人家的份儿。可这时候回来也不地道呀,估计也是趁火打劫来的,当然这只是人们的猜测,众说纷纭。
果然,没过几天刘三婶子给出了答案,这女人也是听说我们村拆迁的消息回来的,明确的说,冲钱来的,要求和刘大平分。小六子当然不同意了,自己是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家产是他和刘大大打拼来的,怎么能拱手送人。那女人说只要分了钱就立马和刘大办理离婚手续成全他们,自己这么多年给刘大带孩子,抚养费也值那么多钱了。况且当年跑回去以后,突然带回个儿子,那边的婆家接受不了,她就离婚了,在当地又找了一家。但又找这家的男人不争气,一直过得很清苦,也是无意中听当年拐卖她的表姐夫说起拆迁的事儿,才想起了这么一出。历史的悲剧,现实的难题,如阴云般笼罩在刘家人的心头。
一连几天,刘三婶子都四处奔走,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女人带着孩子也就暂时居住在刘家,小饭堂忙不过来时还会搭把手,而他的儿子和小六子生的女儿原本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两个孩子玩的还挺投缘,一场暴风雨,暂时停歇了,但大家都明白,这只是个开始。
这事儿如果这是放在古代就好办了,一夫多妻,问题迎刃而解,或男方一纸休书也没有什么闹腾的理由,那时的社会男人就是天,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男权主导的社会可惜一去不返。
两个女人,两个情敌同在一个屋檐下,法律上的正室与实际上的正室,激烈的交锋几乎天天上演。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脸嘲讽和轻蔑,就可能招来一场言语冲突,甚至是肢体冲突,刘三叔和三婶儿,就是消防队员,随时准备灭火。
几天下来,家里所有的人都瘦了一圈,只有那小兄妹俩玩得更加熟络,还别说他俩不仅长得有相似之处,小男孩儿洋洋还挺会关心妹妹小雨。他们俩融洽交往像极了两个敌对的国家,官方高层已经绝交,惟有民间人士不问政事,仍然保持良好的沟通,仍留一线复合的生机。
经过多方求证,最终还是采取了村里最流行、最通行,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议事方式,请村里最德高望重的长者及村长共同商定,据说非洲部落也是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
是夜,刚下过小雨的草原上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小池塘,青蛙们争先恐后的嚎叫,伴随着花草芬芳,和泥土的清香一并袭来,一片蛙鸣声衬托的夜更加宁静了。然而人们都没有欣赏这美妙夜色的心情,全村人都牵挂着这场旷世的谈判,这是村里最头条的新闻了。
北方大土炕,四方炕桌摆上,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三位长者,二爷、宝爷和何顺爷,村支书二红旗也在列,刘三叔,刘三婶,刘大以及两位当事人小六子和四川女人。
二爷清了清嗓子,首先发话了:“今天我们过来主要是商量刘大一家的户口及财产分配问题,这是我们村延续百年的议事传统。我们村是山西人走西口的后裔,我们村的祖上大部分是商人和手艺人,在和当地的蒙古人相互交流接触过程中,矛盾经常会发生,那咋办呢?我们是外来户,硬打硬拼不行。所以这种长辈议事就成了我们解决麻烦的主要办法,我们的原则是不粗暴,不出格,和平解决,现在开始吧。”
村支书在这种场合下一般都是主持人,二红旗刚上任没多久,处理这么棘手的问题还是头一次,先各自陈述。
四川女人:以前是历史原因,我是你们买来的,也是办过正经法律手续的,就是合法媳妇儿,况且儿子的血脉是老刘家的,我自己带了这么多年,抚养费也有很多了,我现在和以前的男人也分了,这都是给你们生儿子的后果,显然我是受害者,以前知道咱这儿穷,我也没和你们闹。现在马上要拆迁,有钱了,我肯定要把你们对我的伤害弥补一下,如果我要是去告刘大买卖人口,刘大早已经坐牢,念及孩子的血脉亲情才没有告发,用刘大一半的财产作为补偿天经地义。
女人边说边哭,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二爷和和顺爷的眼眶也红红的。
接下来轮到小六子了,连日来,哭得眼睛红肿的小六子声音嘶哑,她阐述的意思大致如下:
我和刘大在深圳打工时认识,当时我们没有结婚就同居了,一年以后有了孩子,当时家里困难,简单的仪式,就算办了喜事儿了,最关键的是把日子过好,我几次催刘大领证,他只说离我们工作地太远,一年回去一次就是春节,我们当地的机关单位这个时候也放假了,办不了证。这一拖就是几年,后来慢慢发现,我们周围这样没办证的很多,在大城市,也是一种流行时尚,我们也就没有了紧迫感,要不是这次拆迁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孩子已经6岁了跟刘大已经过了七八年了,好不容易打拼的有点样子了,又赶上拆迁,原本以为是老天眷顾我们,没想到出了这事儿。我不了解以前你们是啥样的,但这么多年,我才是刘大的正牌儿媳妇,我的劳动果实凭啥让别人不劳而获?穷的时候不来,看见有利可图了就来了,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小六子从小在城市里生活,家里把她娇惯的像个小公主,哪受过这气,说到动情处哽咽的不能出声,刘大呢,看着两个女人,又看看父母,看看其他人,无言以对,平时能说会道的刘三婶,这时候也哑火了,脸涨的通红。倒是平时老成持重不善言谈的刘三叔,这会儿开口了,颇有大将之风:
孩子们,你们两个其实都是受害者,其实错不在你们,在我们老两口,当时咱穷没本事,给孩子娶不起本地的媳妇,只有花小钱买远地儿的,当年在咱这儿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也有很多人留下来过得很好,但当年我们的情况特殊,没能把你留下,还把孩子也带走了,我们老两口当时死的心都有,都是为人父母的,谁不想着自己的孩子啊。
刘三叔慢条斯理的说着,也动了些许的情绪。他接着说:
至于小六子就更无辜了,当时你知道刘大这个情况,还会跟他吗?十几年了,村里的人都守口如瓶,怕破坏了你们的幸福,但事已至此,无需再遮遮掩掩的了,你们都是受害人,错在我们老两口,错在我没本事才酿成了今天的大祸。
他转脸又对四川女人说:我想你也别和刘大分了,我们还有两套房子呢,分一套给你弥补我们的过错,也弥补对你的伤害,但孙子我们得留下,这是我们老刘家的骨肉。
众人诧异的是,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说起话来也是这般有条有理,三位长者和村支书都频频点头称是,各方观点都放到了桌面上,就看大家接不接受了。
那四川女人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她又说,孩子是我自己带大的,这么多年是我的心头肉,不可能给你们,除非他成人了让他自己选,光一套房子解决不了问题,补助款也要有我一半,出口就是一股辣椒味,川妹子果然够泼辣。
几方唇枪舌剑,交锋激烈,几番下来,听说小六子几度失控,差点上演了全武行,最后经过一夜的争论,最终达成的协议是:
刘大拿出将来1/5的拆迁款,作为对孩子的抚养补偿费,刘三叔老两口拿出将来要拆迁的一套房和老两口的补偿款的一半,作为补偿,孩子过了18岁,自己选择归属,但每年必须带孩子回来住一个月培养感情,必须解除和刘大的婚姻关系,才能享受上述的补贴。
那女人一看,见好就收吧,也就答应了。小六子也因为能领结婚证了,才能有自己的那一份,毕竟还是自己拿的多,就也不纠缠了。毕竟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就让他见历史去吧,至于刘三叔老两口虽然损失最大,但错误是自己犯下的,权当赎罪,权当给了孙子,刘三婶儿现在又是佛教信徒,相信破财免灾。
一场本村历史上最大的财产纠纷案竟被最古老最土的法庭给解决了,遥想那些法律不健全的动荡年代,这种古老的模式,帮助过很多人,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据说这种方式在韩国和日本的古村落仍有延续。
一场户口纠纷,一段痛苦的回忆,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次古老与现代的碰撞,虽然解决了,相信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对历史教训的思考。人们知道在城镇化改革的大潮中,像我们这样的小村落,只有自生自灭,也许以后在任何的文献中都不会找到只言片语,但在我们心里,永远是不可忘记的故乡。
第四章:二娃相亲
百十多户人家的村庄,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在这样一个一度以农业立国的国度里,农村人的比例一度达到70%以上,传统的农耕文明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时至今日,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还有农耕的思想烙印。农耕文化和思想是我们的特色,但也常常遭受国人的诟病,自给自足,裹足不前是最典型的表现。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亦是如此,清朝的“闭关锁国”,招致百年的屈辱,就是典型的小农思想在作祟。
文化的融合与侵略,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往远了说,如蒙古人用铁骑统治了天下,可汉族人用文化同化了蒙古人;往小了说,如我们的乡野小村,几乎一夜之间就被城市的文化浸染,蜕变,直至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
二娃原本是村里的留守小伙,之前远近的人,嫌贫爱富,避之不及。二娃爹托了好多人说媒拉线,人家一听是“留守小伙”便摇头拒绝。如今,二娃家也有了两座房,一座是用父子俩给人打工挣来的钱修的小二楼;一座是祖宅,有比别人家大三倍的祖屋。而且他们现在还小有积蓄,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最多的一天接待了三拨提亲的,还有一个是邻村的远房亲戚家刚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
二娃如相亲的道具,赔笑的工具。二娃娘和邻居几个婶子是主厨,这是农村人的传统,大凡哪家有红白喜事,左邻右舍都会自愿帮忙。厨房帮忙端茶倒水,没有一个人会计较得失,干活为主,吃喝靠后,大家都无怨无悔,甚至比自家人办事更热心。这就是农村人,有别于城里人的地方。
现在的城里人电话本里存了几百人的号码,可没有一个是邻居的。铁护窗,防盗门,出门进门常相见却无言以对。
城市里人多了,人情味儿少了;车多了,步行的人却少了;高楼多了,平房少了;柏油路多了,绿地却少了;人被迫逼上了如鸟笼般的楼阁。思乡的老人总是占用小区的绿地,种瓜种菜,因为那是他们年轻时代生存的技能,是一种生活习惯,亦演变为一种本能。即使上了楼也念念不忘两亩田。
书归正传,留守小伙二娃,连自己也认为桃花运要来了,姻缘要来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二娃已经累计相亲上百次,是二娃变帅了吗?是二娃有了魅力了吗?是现在的女孩儿开始喜欢农民了吗?
二娃根本来不及想这些,只顾走马灯似的相亲相亲,再相亲了。印象中记得名字里带“花”的就有18个,带“叶”的有15个,另外还有听起来像外国名字的玛丽,爱丽丝等等,这些女孩儿的出现,虽然失败者十之八九,然而,突然间让二娃有些傲娇了。原来拆迁是让他有资格谈恋爱相亲的资本,留守了那么多年,并不是祸,反倒感觉幸福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而桂枝却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心坎里,他心里的桂枝只是以前那个温婉,略带娇羞的女子代名词。而不是眼前这个大方的让人窒息的女痞子。
人真的很善变。有道是,人之初性本善。可被外面的红尘世界浸染过的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轻浮,那么让人怜悯生厌。二娃替她流过泪,就像当初桂枝一家要搬到外地一样,二娃无力挽留,而此刻比挽留更难的是没办法抓住她的心。
如果人生可以随意的快进,快退的话。二娃希望尽快过了这一段,一下子到了垂垂迟暮,人们也就不会在意这浮华的一切了;要么可以倒退,二娃就是跪着也要祈求桂枝的爹娘不要离开村子。然而说什么都没用了,木已成舟。
是夜,二娃想到这些心如刀绞,又想着那些相亲对象没有一个让他动心的,场面挺热闹,可实际上离谈婚论嫁还遥遥无期。
他拎着半瓶二锅头,边走边喝,他想麻醉自己,想让自己的回忆和懊悔都随酒咽下肚子。新修的一幢幢新楼,睁着恶魔般的双眼,满身散发着水泥和贪婪的味道。整条新街上只有零星点缀的老房子里透出灯光,衬托出一个出奇安静的夜。
三婶的小饭堂,这几天也没有营业了,大概这几天又闹腾上了。
突然墙边窜出一条黑影拦住了二娃的去路,二娃吓的一激灵。心想,村里怕是来劫匪了吧?还是自己撞邪了,手里的酒瓶抓紧了,随时做好还击的准备。
“二娃是你吗?你喝多了吗?我呀,桂枝”一个女人的声音,娇滴滴的传入了耳朵里。
“哦哦,是桂枝啊,我以为抢劫的,你干嘛这么晚了不睡觉呀?”二娃睡眼朦胧的懒懒地说。
“我,呜呜呜……”桂枝呜呜咽咽的哭了出来,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桂枝桂枝,你别哭啊!”二娃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赶紧过来安慰,一把把桂枝揽入怀里。
桂枝本来就出脱的好,水蛇腰,瓜子脸,浓眉大眼。比小时候更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味道,一股女人体香直刺脑海,雄性的荷尔蒙在二娃的身体里升腾……
“桂枝,桂枝,你别着急,怎么了?慢慢说”理智告诉二娃要镇静。
桂枝只是哭,把头深深埋在二娃的臂弯里,从哽咽到放声大哭,泪水滂沱,如下了一场暴风雨。二娃从来没见过女人哭的这么伤心,还在自己的怀里,他一下子慌了手脚,可又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像木桩一样站着,左手拍着桂枝的后背,右手还拿着他的酒瓶子。
过了许久,二娃只觉得腿都麻木了,桂枝才从暴风雨逐渐成了小雨,哽咽着抽泣着,慢慢扬起脸看着二娃。却看到二娃像个被吓傻的小羊羔站的直直的,又像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任由她依靠着压的弯弯的,她忍不住破涕为笑。这一哭一笑弄得二娃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
那究竟桂枝到底为什么哭呢?原来她家里老是催婚,连日来,让她很烦心。傍晚吃饭的时候,父母又提起这事儿,还说了几句重话,让她很是伤心。
出来散步的时候无意间看见喝闷酒的二娃一时间心中的积怨才得以宣泄。
原来,桂枝八岁那年随父母移居外地,父母靠打工为生,自然也就居无定所,先上了打工子弟学校,到了初二,因父亲意外摔伤而辍学回家。那时母亲要给别家当月嫂养家,没有人照顾父亲。弟弟刚上小学四年级,懂事的她主动要求辍学照顾家里。一年多的时间,父亲逐渐康复,虽然多次催促她复课,可她却不想上学了,她想打工赚钱,和父母一起养家供弟弟上学。
就这样,桂枝开始了打工生涯,先在父亲认识的朋友那里学美容,后来美容院关门了,又做超市促销员,自学会计。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广东东莞。这个中国制造业中心,是无数人梦想的淘金地。
凭借自学的会计知识,桂枝在一家小型的工厂里当起了会计。可三年过去了,非但工资没涨多少,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自己花,而且流水账会计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她想换份工作。
这时,一家刚营业的娱乐会所招聘前台收银员的广告映入了眼帘,当时的工资竟然高达4500元/月。她认为,要去试试才知道行不行。
没想到,她的好身材和标志的五官,就是她通过面试的资本。就这样,她当上了那家新娱乐场所的前台收银。
“那后来呢?”二娃不想听桂枝慢条斯理的讲,急切的追问道。
不知不觉已过午夜,二娃和桂枝又像小时候一样坐在一起玩弄着小石子促膝长谈。对于桂枝嘴里的外面世界,二娃只是个听众,故事里各种身份,各种场所,他只能听个大概,桂枝讲的很生动,她的经历也够坎坷,一个女孩子在外地打工,着实不易。
“后来你不都知道了吗?”桂枝说道。
“什么啊,我哪知道”二娃还是傻傻的问。
“后来,东莞被扫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就你傻啊!”桂枝杏眼圆睁,轻轻的责怪道。
“哦哦,你说的是东莞扫黄吧,你被抓了吗?哈哈”二娃故意调侃道,他好像要得到什么答案似的。
“你个死二娃,叫你胡说,叫你胡说”桂枝的粉拳如雨点般在二娃的胸口落下,可一点儿都不疼,二娃咧着嘴嘿嘿地笑了起来。
二娃试探性的问道:“那我听村里人说,你是那个……”
“不是”桂枝厉声喝道。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是我在的那家会所被查封了,我只是个前台收银,接待,接待,你懂吗?会所涉黄,老板涉黄,但不等于所有人都涉黄啊!村里人道听途说能信吗?我什么都没干过,你信吗?你信吗?”桂枝说得很认真,语速很快,像连珠炮一样。
“我知道从那种地方回来的人名声都不好,我也是担心名声问题才回来的,父母亲人都说我了,他们以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难道东莞回来的就是小姐吗?所有人都在歧视我,所有人都在嘲笑我,戳我的脊梁骨,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做错什么了?”桂枝边说边又开始委屈的流泪。
“当初父亲看病要钱,弟弟上学要钱,不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我至于退学吗?干个高一点工资的工作有错吗?只是个场所涉黄,我又不知情,我没做鸡也没被人包养我干什么了?你们这么看我……”呜呜,情到深处,桂枝又泣不成声。
二娃定下神来,想想自己也没亲眼见过桂枝做小姐啊,只是听村里人道听途说,她是被从东莞扫回来的,如何如何……而村里人也没见过啊,无凭无据,凭什么毁一个姑娘的清白声誉呢?想着想着二娃竟然有些气愤。
他支支吾吾的说:“桂枝,我我,我这不也是听村里人说了闲话吗?其实家里给我相了那么多,我都没答应,其实其实……”二娃的脸涨的通红,和猪肝一样。
“其实什么?”桂枝突然扬起脸死死地盯住二娃的双眼,如两道激光束一般。
“其实什么?你说啊!”桂枝继续追问道。
“其实,其其其实,我我心里一直都有你。但我以为你变坏了,我还是喜欢以前的你。这么多年都想,我二娃没本事,去不了大城市,只能当一辈子农民。我知道,和你交往,是一种奢望,我还听信别人,不待见你,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真的……”二娃喃喃着,一直在后悔自责。
继续说道:“我,我,一直很喜欢你。小时候,你们家搬走的时候,我就想把你留下来,留下来……”二娃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和自己说话,生怕被桂枝笑话。
但二娃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一口气说出了心里的话,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二娃激动的热泪盈眶,这个年届三十的西北汉子,从来不会把儿女情长挂在嘴上。贫穷甚至让他连个谈恋爱的机会和资格都没有。人家女孩儿,不光是看不上这块贫瘠的土地,更看不上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坚守清贫的人。
留守小伙就该被人歧视吗?只要是身心健康的人都有一种渴望。渴望被认可,渴望被接纳,渴望有谈恋爱的机会。而不是有房有车有存款,才能有资格谈恋爱。
“我爱你,桂枝,我爱你……”二娃终于肆无忌惮的喊出他心里珍藏了三十多年的话语,突然间的释怀,让他卸下了所有的包袱。激动,兴奋,渴望,自卑,胆小……各种情绪的交织下,让他像一只刚打完架的猫,鼓起的战斗激情还未平息,依然心有余悸。
“二娃,我也爱你。”不知什么时候,桂枝的两片朱唇已经奋力地吻上了二娃,她想用温柔来化解他的激动。而他却又觉得受宠若惊,恍若隔世。
南归的燕子和小家雀恋爱了,那种激动的心情无需赘述。只听的叽叽喳喳的两只小嘴,在浓重的夜色中显得分外响亮。二娃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美妙的感觉,桂枝温暖而柔和的唇,和她身上透出的阵阵摄人心魄的味道,让二娃心旷神怡,整个人都陶醉在这奇妙的幻境中。
二娃像一只刚出笼的猛兽,开始猛烈地攻击“猎物”,雨点一般的吻落在她的脸上,脖子上。此刻,也许只差了一只小小的火柴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新建起来的“纸片楼”似乎都在晃动,新鲜的水泥味夹杂着浓重的荷尔蒙气息,久久回荡在夜色中……
月光如雪般散满大地,花香草香泥土的香,和着清洁如洗的空气一并吹拂过来,深深地吸一口沁人心脾。霎时间,人的身心焕发出青春活力。
就在这美好的夜色阑珊中,二娃和桂枝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第五章:逼婚闹剧
最近村里又发生了一件荒唐事儿,83岁的二爷居然要和38岁的小六子结婚,这真的是要疯的节奏啊,为了拆迁款真是不择手段!
原来,四川女人暂时不想离婚,怕离了人财两空。可小六子,毕竟已经在村里盖好一座房子,不是本村人,房子盖了也白搭,是分不到钱的。不知哪个法律人士的支招,除非嫁给本村有户口的人才行,实际上就是假结婚。和中国人去外国办绿卡是一回事儿。
可回头看,村里的单身男性,都名草有主了。只有二爷早年丧偶,还是单身。小六子只能找二爷,参照的模板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翁帆,以及默多克和邓文迪之流。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83岁的二爷,和38岁的小六子要结婚?一时间“老少配”成了村里的大新闻,像一股泥石流席卷了整个村庄。大家虽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忍不住茶余饭后的调侃。
再说二娃和桂枝,自从他俩相好之后。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二娃换上早年买西装革履,还系上一条粉红色的领带,逢人便笑眯眯的鞠躬。人们问:二娃,你不热啊?只见二娃彬彬有礼的说,人家电视里上海滩的绅士就这么穿的,上海在南方,人家都不嫌热,我们这儿是属于北方,肯定不会热。再说了,当绅士就得有点规矩。
人们又是一通唏嘘。可二娃,哪管这些,只顾哼着小调,摇头晃脑的在街上转来转去。而桂枝想找个人尽快结婚,二娃也许正是她心目中的那个老实人,需求决定了一切。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桂枝却不见二娃来提亲。她哪里想到此时的二娃,正和自己的父母冷战。原因大家都知道,二娃向父母提出娶桂枝的想法,可二娃爹,一听就火了。说我们家世代清清白白,就是打光棍也不能娶个婊子回家呀,这不是辱没祖宗吗?二娃娘倒是没发表太强烈的意见,但也没有说同意。连着几天,二娃和父母不说话,一直持续性冷战。
二娃,又和桂枝约会,二娃婉转的表达了父母的意思。其实桂枝自己也心知肚明,可桂枝毕竟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一点儿都不慌张,她也知道,农村人保守封建。但她想,自己从小就和二娃青梅竹马,既然有感情,是不会被人拆散的。那就想办法说服二娃的父母吧。两个人坐在村边的大石头上苦思冥想。想来想去,只有二爷了,二爷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而且也是二娃爹最敬重的人。
简短的说,他们去找二爷,一通说服之后。二爷当然肯出面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后来他又去找了狗蛋儿,毕竟外面回来的人,总是见多识广,比村里人要强,此二人出马,一通唇枪舌剑下来,可二娃爹就是不同意。二娃和桂枝急得团团转。
之后,又找了村支书和刘三婶……二娃爹的态度坚若磐石,就是不答应。一拨又一拨的说客败下阵来,二娃爹稳如泰山,任尔东南西北风,兀自岿然不动。你有千般妙计,我只一计定心。
古代的崔莺莺、杜十娘之流不知是否也曾遇到过如此的境地。寒风冽冽,纵使有情人也难成眷属。谣言和世俗相遇,终究也逃不过的世俗的做法。也许爱情自古多磨难。可二娃和桂枝,现在显然已是强弩之末,黔驴技穷。桂枝不甘心,城市里那么多的追求者,自己都没看上眼。区区一个留守小伙,一个老实人,怎么就搞不定呢?她气的暗咬银牙。
二爷和小六子的结婚证已经下来了,据说,这对老少配年龄差距,打破了县城的纪录。为了让戏演得更真一点。二爷逢人便解释道:娃娃们盖房,分点补偿款不容易,二爷这张老脸不算什么,解决贫困才是关键啊。可调皮的孩子们还是给二爷编了一首童谣:
二爷爷,了不起,
八十三,把亲娶。
新娘子,三十八,
稀里糊涂把人嫁,
大老头,小媳妇儿,
老少配,顶瓜瓜,
就是能看不能睡,
不能睡呀不能睡……
二爷听得直皱眉头,边摇头边说:“现在的小孩子,真能起哄,这乱七八糟的都是谁教的?这帮小崽子们,真是欠收拾。”可村里的其他人,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这几天赶上干热,据说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高温已经逼近了40度,北方干旱少雨,地皮烤得冒火,光脚丫出去肯定就起泡了。听说刘三婶子为了办酒席,专门弄来一台透明的大冰箱,和两个饮料专用的冰桶,准备招待客人。小饭堂里的酒水生意,又开始风生水起,刘大隔一天就得去城里进货。
村里住着百十号子外地人,这几天,高温都停工,小饭堂的地方大,又有大风扇,又有冰啤酒,自然是个好去处。从早到晚,棋牌麻将声不断,推杯换盏吆喝声不断。猜拳行令,选酒司令,玩棒子老虎鸡的,小蜜蜂的,玩色子的,转筷子的,干瞪眼的,叫号翻牌的……凡是酒桌上能玩的花样,随便玩儿,中心议题就是喝酒消遣避暑。
这些过路财神凑在一起,真能造。村里好几户都养着羊,土鸡等等,他们一来,几乎隔一天就宰羊杀鸡,小饭堂里的手抓肉,炖羊肉,焖羊肉,涮羊肉,血肉肠,包饺子,大烩菜,羊肉炒粉,葱爆羊肉,黄焖鸡,小野鸡炖蘑菇,土鸡蛋都是用盆煮的……再配上菜园子里的水萝卜,黄瓜,韭菜,大葱,生菜,白菜等这些丰富的绿色蔬菜。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大吃大喝,钱当然多半是主家出的,谁盖房子,谁家出。
刘三婶子的莜面,那是令人叫绝。在第二季《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以后,莜面,这种号称最健康的粗粮美食开始走俏大江南北,这种只属于晋蒙一带的美食,开始风靡全国。据说上海还开了一家某某莜面村的饭店,年销量过千万,越来越多的地方美食开始全国化。刘三婶子施展出最拿手的技艺,推莜面窝窝,那是在搪瓷盆的底上完成的,一寸多高,整整齐齐的立着,满满的一笼屉,没有一个倒下的。恰似整齐划一训练有素的部队。上锅蒸熟,蘸着鲜美的羊肉汤,羊杂汤,或是由生菜,黄瓜等新鲜蔬菜拌好的凉汤吃,那叫一个惬意。一筷子窝窝下口,窝窝的眼里灌注了汤汁肆意在口中翻腾,舌尖上舌根下,顿生津香之味,来不及细嚼慢咽,便已下肚。好像肚子早已等不及了,看着客人们大快朵颐,刘三婶子骄傲的笑了起来,面如桃花。
莜面是好吃,可是纯手工做起来繁琐,还慢。所以每天限量10斤,其他的莜面鱼鱼、条条、片片,饸饹(都是莜面做成的不同形状)等不限量,让食客们吃了念念不忘。
一天,村里的人们大早起来就往二娃家里跑,听说桂枝上二娃家里闹事儿了,二娃的爹娘,早上刚起来,就看见桂枝披头散发的哭着跑来,口口声声说自己有了二娃的孩子,没脸见人了,进门就一屁股坐到炕上不走了,鞋也不脱就上炕头,哭得泪眼婆娑。
这一下,可把二娃的爹娘给吓坏了,连忙叫了二娃对峙,二娃只是不说话,很懵很无辜的样子,可是心里却丝丝窃喜。他暗地里给桂枝挑了大拇指,那意思是,你这家伙终于出大招了,真有一套。
二娃爹,一脸的怒气,狠狠给了二娃两个大嘴巴子,打的他眼冒金星,嘴角都淌血了,口里骂道:“你这没出息的货,见了女人就管不住裤裆啊,你也不睁睁狗眼,看看是不是能种的地,你真要气死老子啊,不要脸的东西,给我们老王家丢脸啊,你叫我百年以后,咋去见祖宗?你个不孝的逆子”说着又一巴掌,朝二娃劈头盖脸的打了上去,二娃娘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拼命的拉着他爹,怕他再打二娃。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