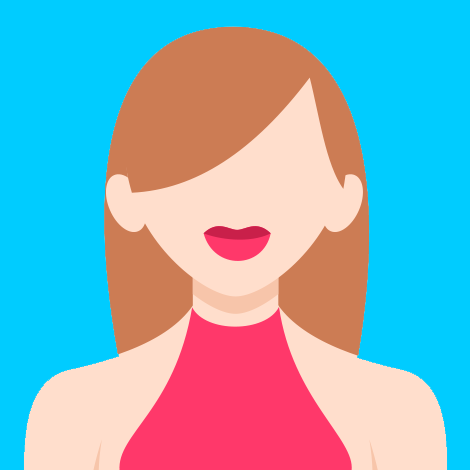第一节 剑门关之殇
大唐剑南道关隘口。
山风席卷着松涛从远处荷荷滚来,兀忽扬起一阵尖锐的悲鸣。天空密布着一层灰黑色的积云,随着唳风不断涌堆,仿佛随时都会像山崩一样砸下来。
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一个年约五十的乞丐背着风蜷缩在路边的界碑下。已经是隆冬的时节,他的衣服很单薄。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衣服,山苍子勒住马沉沉的凝望片刻,连面色也是暗暗的。她从褡裢里摸出一块银子掷在乞丐脚下,策马向关内赶来。
守在城门口的几个巡防兵正在相互抱怨着这鬼天气,远远的看着一个异族的貌美女子骑在一匹毛色雪白的马上向这边走来,未等山苍子靠近,早有一人站出来搭话。
“姑娘是哪里人?这么冷的天为何一个人出门?”
山苍子勒住马问道:“过了这道门,就是大唐了么?”
听她这样问几个巡防兵围拢上来,当中一个面膛紫红粗粗壮壮的兵士,扬了扬手中的红缨枪憨声憨气的嚷道:“看你也不像寻常家的女子,你来我大唐做什么?想过关就把来路报清楚。”
山苍子翻身下马撩开缰绳亦步亦趋的靠近到那憨子跟前,莺声鸾语道:“小女子实在不晓得大爷想要什么样清楚,不如大爷你悄悄告诉我。”
她青葱般的手指钩住那憨子的下巴,微微笑着凑近他耳际,正欲暗念咒语,忽地从城门内响起一个洪钟般的声音。“不好好值守你们在做什么?”
一众人忙不迭的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两只眼睛直愣愣的瞪着前方,噤如寒蝉。
山苍子上下打量着他,但见他身量魁梧,着一袭银色盔甲,握住腰间佩剑剑柄的手上青筋暴突,面貌极是俊逸,绝不输南诏国和回纥国任何一个男子。
“已经过了关城门的时间了,姑娘要进城就明天赶早吧。”他高山仰止的看了山苍子一眼,转脸训斥那些兵士道:“你们几个一人自去领五十军棍等候发落,以后不准出现在虎威营里。”转而吩咐跟在身后的兵勇:“把他们替下来。”
山苍子赶在他的背影隐没在城门前抢先一步挡在他面前:“将军请等一等——”
旁边一护卫正要抽出腰刀,他扬手制止,炯而发亮的眼睛略带诧异的问:“姑娘会武功?”
山苍子和他对视的那一瞬间看出他是一个忠厚之人,收敛起妩媚妖娆正色回答道:“小女子自幼习武。”
另一护卫喝道:“校尉大人已经说过了,姑娘要进城就等明天。”
山苍子面露难色,来路是一片无际的山林,去哪里找落身之地。她恳诚的央求道:“请校尉大人恩准小女子进城,我孤身一人如何能在山林里过夜?望大人明鉴!”
他抬头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刚想开口问她要通关文牒,忽觉周身一阵寒颤,整个人失去知觉,只朦胧的记得那个异族女子如嫣笑脸在眼前闪了一下便烟尘一般散去。
南宫澈醒来时人已在自己床上,最好的两个兄弟柱子和魏元守在一旁昏昏欲睡。他迷迷蒙蒙的坐起身问:“我怎么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两人长吁出一口气:“你总算醒了!刚才巫医来看过说你中了蛊毒。”
“蛊毒?”南宫澈心下一凛,使劲摇了摇发昏的脑袋细细的回想:“是那个女子。原来她不光会武功也会巫术。”忙不迭的追问他二人:“那个女子人在哪里?”
柱子说:“早就不见踪影了。”
魏元忧心忡忡的道:“据说是你批准她进的城,还帮她牵了马!现下整个将军府传的沸沸扬扬,大将军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你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吧。对了,他让你一醒就马上去向他汇报。”
柱子朝门外努努嘴,南宫澈看见守在门外的正是大将军李希烈的亲兵。他踉跄着翻下床从桌上提起茶壶往嘴里浇灌,沁凉的水使他片刻便恢复了神气。
南宫澈由芷柔引领者来到将军府西苑的星陨阁暗室之内,只见李希烈一身银色戎衣端坐在案机前,深邃的眼炯而发亮,黝黑的面目上几道深深的沟壑将他的愁容一览无余的呈现在南宫澈眼里,灰白的胡须有几缕被酒水浸湿粘在一起。除了应对府中人满为患的姬妾时,他从未表现过自己无措的一面。
不等李希烈发话,南宫澈便跪伏下身,揖首道:“属下办事不力,请大将军责罚。”
李希烈从经手掌摩挲过千万遍的大唐山河舆图上抬起栗色的眼睛,盔甲偶尔和铁案摩擦发出丝丝让人心头冰凉的兹兹声,略一抬手示意一旁的芷柔离开暗室。等暗室的门关闭,他方幽幽然道:“可老夫更想让你将功赎罪。”
南宫澈仰起头。
他的手指沿着舆图起伏的曲线贪婪的勾勒,不经意的问:“你可看清此女的身份?”
南宫澈顿了顿摇摇头。“属下不甚确定,一开始看她的装扮觉得她是回纥国的人,后来又觉得不像,她不仅会巫术。武功也深不可测。”
李希烈颌首示意他起身继续说下去。
“当时属下离她有一丈多远,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她是如何赶到我前面。”
李希烈起身从博古架上取下一轴略微泛黄的画卷摊开在案头,那画上的女子•••南宫澈一瞬间愣住了。
画上的女子凤冠霞帔坐在一株盛开的银薇树下,恬静的脸庞,小巧精致的鼻子,薄薄的唇微微上扬勾起一抹恬淡的笑意,一双灵动的狭长的眼却隐隐含着怨。那双眼睛和那个对他下蛊的女子,一模一样。
“她还是来了。”
从南宫的神情里李希烈看懂一切,嘴角漾起一丝苦涩的笑意,低声沉吟着:“她的速度的确够快。只是不知她硬闯我唐国所为何事?”他微闭上眼睛黝黑的面堂上闪过一瞬哀伤,铿锵有力的令道:“找到她,把她安然无恙的带回来!”一块红色丝线绳拴着的墨绿色勾玉,随着余音一并递到南宫澈面前:“她见到这玉佩,就会跟你回来。此事需小心谨慎,老夫不愿这件事公之于世。”
将军府一片肃静,芷柔仍旧领着他从后门出来到街上,早有守卫递过他的佩剑,一匹马和一个包袱。
芷柔道:“大将军说了,请校尉即刻动身。南宫大人为自家性命思虑,也要务必完成大将军交代的事情。”
南宫澈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芷柔疑窦暗生,为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李希烈居然如此反常,刚愎自负如他,做事从来都是轰轰烈烈,这一次却滴水不漏。到底这其中有什么连她也不得知晓的秘密?这样想着转过游廊,抬眼便看见陈仙奇反剪双手站在廊下的一棵参天银杏树下。
昨夜的一场唳风刮落了许多树叶,让往日缤纷繁华的枝头显得空廖。
楼英定住脚,四下看顾无人,不由得掌心凝聚起法力。
陈仙奇冷笑着转过身,“你总是喜欢做自不量力的事情。”
他阴稠绵软的嗓音更是激起芷柔的怒气,可惜还未出得手便先中了陈仙奇一记暗击。芷柔抹去嘴角蓝色的血,心底涌起无限的悲伤,三千年的修行面对人间的人,人间的事,依然无能为力。
“那个老匹夫昨天不准任何人对那个妖女动手,今天又为何单让南宫澈一人去追访她的下落?”
“我不知道。大将军把我支开了。”
“我要知道原因,并且是你亲口告诉我。”
“哈哈•••哈哈哈哈。”芷柔忍不住悲笑。
陈仙奇怒喝道:“你笑什么?我让你做什么你只需做好便是,等我哪天满意了,自然会放了你的苏郎。”他蹙了蹙眉头又道:“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苏一清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你一个修行了三千年的三昧灵狐,羽化成仙的那一刻为他放弃,真是可惜又可怜。你和他注定是生离死别,不若随了我醉生梦死,也强过他日的肝肠寸断。”
“苏郎是我的劫,我没办法。他一个人在这世上孤独的活着,功不成名不就,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如果我走了,他就什么都没了。你心如铁石又怎会明白我与他之间的海誓山盟。我受你控制是我自己遇人不淑。这世上有好人也有坏人,苏郎为人善良,我自然心甘情愿为他博取功名。现在看来功与名都是过眼烟云,我只求与他恩爱厮守,不管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哪怕只有一天,我芷柔死亦无憾。”
“好一个痴情的妖女。我说过,只要我达到目的,自然会放你们自由。”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要这天下!我要借李希烈的手,取得这天下的生杀予夺之权。”
芷柔不解:“你也曾是修仙之人,必定也曾以天下苍生安宁为念,何以如此恶毒、残暴不仁?”
那一瞬间,陈仙奇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哀伤,他默默回转过身,依旧瞻望着那株古银杏树。云雾在其间缭绕,几只雀鸟鱼贯飞梭,犹如仙境,但仙界真的有那么好吗?
南宫澈原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女子,岂知她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寻访了十余天整个剑南道到处都没有那个异族女子出现的踪影。看来要往关内走一遭了。他翻身下马,走进路边的茶亭,再往前二十里就是剑门关。他还清晰的记得父亲死在剑门关外的那个场面。
建中二年四月,作为一直拥护宰相杨炎向德宗提出的,施行削弱藩镇割据实力办法,颁布“两税法”等治国举措的父亲,遭朝中反对者弹劾。
两个月前,他刚升任太中大夫正四品文官,一扫从前郁郁不得志的晦暗心情。得杨炎青睐意气风发,屡次谏言获德宗赞誉更是前途不可限量,一时间竟也门庭若市,并借升官之际敛了来路不明的钱财。而南宫澈因为自小崇尚武道不喜舞文弄墨,十二岁师从羽林军中一个小头领,并渐次成为守护大明宫的羽林卫。
祖上也曾有高官出入朝堂,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随致家道中落。母亲离世的早,父亲又常悲叹命运不济,家中没有女主越发显得家不似个家。他们租住在皇城东一个狭窄的住着三户人家的院落里,父亲每天忙着结交朝中大臣,因囊中羞涩屡屡受人排挤。八岁时家中一个服侍了二十余年的,唯一的一个仆人终于耐不住南宫家的穷苦,卷了微薄的细软私逃了,那件事之后父子二人鲜有交集。
他幼年唯一的玩伴和依靠也只有邻居家那个刁蛮的小女孩苏飖。
苏飖的父亲是个走街串巷的郎中,手上套一个麻绳串着的铜铃,走几步将铜铃举过头顶吆喝一声,苏飖最厌弃,常诅咒发誓一定帮父亲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医馆。她的倔犟和捉弄人的本事简直叫人受不了,每次惹出事南宫澈这个闷葫芦总愿意替她担着。可能因为太孤独了吧,他害怕苏飖像风一样瞬间不知所踪,害怕想把握却无能为力的一切事物,所以两人相得益彰,南宫澈的心思只有苏飖一个人可以探知,并乐此不疲的付诸行动,出了事南宫澈出面挨罚。十二岁那年,他们在家门口的街上打闹撞到了一个商贩,商贩堵着门不依不饶非要大人出来赔罪,恰巧一个身着便服的羽林军头领经过街巷口,替他们解了围。
十六岁,由于父亲终于依附上在朝中崭露头角的杨炎,得他资助南宫家欢天喜地的搬离了那个小小的装满依恋的小院,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颇有大家闺范气质的苏飖,拒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邻近的布匹店的余少爷定亲。她扬一扬玉脂般的脸,一字一句的向南宫澈道:“这辈子我只嫁你。”
南宫澈沉一沉气,说:“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南宫澈的妻子。”
羽林军中不乏武艺精湛家世显赫的人,更有不少是出身武将世家,一生似乎注定要被唐宫器重,成为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得到更高的品阶他强迫自己适应官场上的那一套阴暗伎俩,和父亲一道在官海中起起伏伏消磨了几年时光。南宫澈始终没有攒到一份像样的聘礼,可以把苏飖风风光光的娶回家,而父亲对这门私定终身的亲事极力反对。苏飖的家世他是无论如何都看不上眼的,儿子就算娶不到三品以上官员家的女儿,亲家的官阶也绝不能低于四品。
一而再拖两人都到了二十几岁的年纪。
终于德宗即皇帝位,杨炎被任命为宰相,父亲屡获升迁从儒林郎直至太中大夫。
父亲自己也说不清收受了哪些人的钱财,多年来的穷困使他拒绝不了白花花的银子,他以为有了银子似乎就有了一切保障。
因着父亲杨炎在朝中沦为笑柄,甚至德宗也有些不大相信杨炎的举措,真的能让积重难返的唐朝从新走上贞观盛世的局面。
父亲所犯的过错毋容置疑是致命的,好在除了宰相杨炎其他人对朝堂上无足轻重的父亲并无多大兴趣,并且多数人不愿意随着杨炎一起人云亦云。留父亲一条命时时羞辱杨炎他们是极乐意的。
大理寺粗粗会审后,父子二人被削职为民一起流放蜀地。
苏飖曾得一个机会在长安城外的驿道上送一送南宫澈,她神情恹恹的,往日明亮的星眸布满血丝,只颤抖着斟满一杯酒简单说了一句:一路保重。不待南宫澈说什么便飞也似的跑开了。
彼时南宫澈有千言万语,他想说对不起,想说我会回来找你——却都没有机会说出口。
出了长安南宫澈便感觉到处境极为凶险。他总能感觉到有武功高强的人环伺在周围,终于到了一片林子里,忽然冒出一队黑衣人一人手持一把弯刀兜头便砍。四名差役命丧当场,南宫澈挣断锁链拿着差役的褡裢背着父亲拼命的往蜀地方向跑,他不敢走官道,不敢投宿客栈,也不确定走的路线对不对。父亲每天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左右也只是一条苟延残喘的贱命,逃或不逃他毫不关心。
南宫澈劝父亲宦海浮沉那是幻梦,自古以来多少得皇帝器重的肱骨大臣有几个下场是好的,即便是杨炎恐怕也有登高跌重的那一日。他表现不出儿子对父亲的那种亲昵,甚至觉得这样时时相对特别别扭。大多数逃亡的时间他们二人沉默相对,南宫澈竭尽全力或背或拖着他跋山涉水,他不抗拒也不积极。于是路就显得太别漫长。
后来他们闯入邛崃山脚下的落凰村。
村子里的人都很和善,听他们说是去蜀地寻亲路上遇到劫匪,村正在自己家里为他们筵席践行,并亲选了两匹骡马送给他们代步。
南宫澈不知道他离开的第二日,杨炎派出的杀手追访到落凰村,全村仅有几个进山玩耍的孩童躲过杀戮。
穿过林立的剑山群,再过了壁高千刃天开一线的剑门关便是蜀地剑南道,南宫澈回头张望一眼父亲,他眼窝深陷脸颊上颧骨突起,松耷耷的依旧没有精神。
“我们就快到了,前面就是剑门关。”
“唔。”
“等到了地方父亲好好休息两天,我去衙内送呈文书。”
“唔。”
南宫澈折回来牵起父亲所骑骡马的缰绳继续往前赶路,不多时听见身后人马呼啸声,他一面叮嘱父亲抱紧马颈一面催赶着马往密林中跑,那队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不一会儿便将他们包围起来。
父亲突然暴怒起来,“要杀要剐冲我来,贪赃枉法的是我一败涂地的也是我,跟我儿子没关系!”
领头的一个冷哼一声道:“既然没关系那他为什么要跟着你一起跑?”
他手一挥几把利剑一起向他们刺来,南宫澈踢开了眼前的几个人猝及不妨父亲朝一个黑衣人扑去,那黑衣人手中的剑直直的插进父亲的左胸。
他口中喷出一口鲜血面目狰狞的狂笑:“澈儿说的对,都是幻梦,都是幻梦。”
南宫澈惊惧的托住父亲渐渐萎靡的身形,不住的追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从前你就丢下我一个人不管不问,为什么今时今日还要这样做?你知道我有办法带你躲过这一劫,我是你的儿子为什么你从来都不给我机会爱你?”
父亲紧紧攥住南宫澈的一只手,拼尽最后一口气力断断续续的说:“对不起,从前是我错了,不住的追着那些镜花水月自欺欺人,如今我怎么还能再拖累你?这一路上我常常想,你若是生在别的人家一定会是一个很幸福的孩子。我对你不管不问你从不抱怨,你爱苏飖也是因为我的阻拦才一直未能将她娶进门,我常常想,常常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醒悟。孩子,我爱你,我爱你——”
怀抱中父亲安详的闭上眼睛,南宫澈抵着父亲的额头悄声道:“我也爱你!”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刺痛,巨大的活下去的渴望驱使着南宫澈起身反抗。
长安城里的苏飖,长在心里的人,如风一般飘飘忽忽扶摇直上,最后只有一张模糊的脸似笑非笑的俯瞰着这场血战。我快死了吧?南宫澈心底沉沉的想,他机械性的一剑剑砍下去收回来再砍下去——
醒来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身在天堂。他衣衫整洁的仰面躺在一张高床上,身边还环绕着四个婢女流水似的在房中洒扫。鹅黄色的帷幕在床沿打了一个褶皱曲线光滑的倾泻到脚榻上,帷幕上同色流苏随着窗口吹进来的风轻轻摇曳。房中的一应摆设无不精美,琉璃花瓶中还插着含苞待放的一束鲜红似血的腊梅。
他小心翼翼的轻声问:“这是哪里?”
一个婢女极力掩饰住惊喜回道:“大将军府。我们将军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
南宫澈凝神静默了一会儿:“如此说我还活着。我已经身在蜀地了?我怎么了?”
几个婢女围拢在一旁面面相觑。
“你受了很重的伤,大将军吩咐府兵把你抬回来的。”
“是啊,”南宫澈微闭了眼忍住夺眶欲出的眼泪:“我还活着!”
当他能下地走一段路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见到了李希烈。和父亲一样也是五十余岁,他的身材更高肩膀更宽硕一些,浓密的胡子硬扎扎的将一张黑红色的脸膛映衬得孔武有力。
李希烈将南宫澈上上下下打量良久,方朗声笑道:“资质不错,可堪重用。”
南宫澈用力绷紧每一寸神经,不卑不亢的问:“为什么救我?”
李希烈初初很诧异,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南宫澈再次追问:为什么救我。“你过来。”他招一招手看似随意的揽住南宫澈的肩,将他引到一口水缸前。
水缸中几尾猩红的锦鲤欢快的游荡不时泛起一圈圈涟漪。水中他的倒影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光鲜。李希烈突然掐住他的脖子用力的往水缸中按,在触到水的一霎那,南宫澈拼力抵挡住李希烈并不强大的内力,他既没有出手反抗,也没让李希烈得逞。
“老夫亲眼见过你的身手,想让你为我所用,这个回答够清楚吗?”
“属下愿为大将军肝脑涂地。”
“你把我当成什么?”
“父亲。”
“——我缺一个昭武校尉,就你吧。”
彼时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和成德军节度使李惟岳联手反唐,德宗发诏令 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东川节度使王叔邕、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刑南节度使李昌巙、陈少游发兵征讨梁崇义等人,任命李希烈为诸军都统。大唐的山河间战事如火如荼展开,长安如同掉进油锅里的丸子。
南宫澈辗转得到杨炎遭罢免和苏飖已经嫁给余少爷的消息。杨炎纵然害死了父亲,这其中也有父亲自己咎由自取的因由。李希烈已经妥善的安葬了他的父亲,这一篇他想翻过去从新开始不一样的人生。至于苏飖,知道她已经嫁人的那一刻南宫澈欣慰大于心痛。那个倔犟的小女孩终于肯对这个世界妥协。李希烈也非常器重他,给他兵权准他上阵杀敌,赐他官爵赏他府邸,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亲密。
可是就算时过境迁,剑门关依旧是他这一生抹不掉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