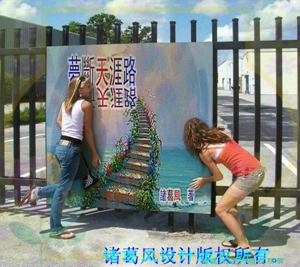家庭
小说
生与死的诱惑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我给他来点儿假象,”卡斯伯格念叨着。他离开自己一直走的小道,在原地绕起圈子,他绕啊绕啊,边绕圈儿边回想猎人对付狐狸的办法,狐狸对付猎人的诡计。他两腿发颤,手上脸上被树枝抽出道道血痕,他知道就算他有的是力气,在黑夜里乱跑也是自寻死路。他累极了,想歇会儿,他想:“我刚才玩了狐狸的把戏。现在该玩点儿猫的把戏了。”旁边有一棵大树,树干粗大,枝丫茂密。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尽可能不留一丝痕迹。他躺在一股粗大的树枝上,喘口气儿。休息给他带来了新的信心,甚至,是一种安全感。他告诉自己,就算是萨斯基将军那样疯狂的猎人,也不会找到这里来;只有魔鬼自己,才能在黑夜中找到灌木丛里那些难觅的脚印。但,也许,那个将军就是个魔鬼——
不祥的夜色宛如一条受了伤的毒蛇,慢慢地爬上来。丛林里一片死寂,瞌睡却没有降临到卡斯伯格。天快亮了,天空一片暗灰。就在这时,远处一只惊鸟的叫声引起了卡斯伯格的注意:什么东西正沿着卡斯伯格的来路,穿过灌木丛,慢慢地,轻轻地摸了过来。卡斯伯格透过浓密如织的树叶看去。来的是个人。
这个人就是萨斯基将军。他一路追踪而来,眼睛紧盯着地面。快到大树的时候,他停住脚步,双膝跪地,察看地上的痕迹。要不是看到他右手握着的那个刺眼的东西——一只小巧的自动手枪,卡斯伯格几乎要像猛虎下山一样扑下来了。
萨斯基摇了几下头,似乎感到很困惑。接着,他站起来,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黑色香烟。香烟刺鼻的香味飘过来,钻进卡斯伯格的鼻孔。
卡斯伯格屏住呼吸。将军的眼睛已经离开地面,一寸一寸地沿着树干往上移。卡斯伯格僵住了,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扑下去。但萨斯基锐利的眼睛快到卡斯伯格藏身的树枝时却停下来,微笑在他棕色的脸上荡漾开来。他深思熟虑般地吐了个烟圈儿,然后转过身子,沿着他走来的方向,若无其事地往回走。皮靴踩在小灌木上发出的沙沙声渐渐远去。
卡斯伯格长舒一口憋在肚里的气。第一个念头让他几乎绝望:萨斯基竟然能够在这么个黑夜里,穿过丛林跟踪找到树下,只是因为一念之差,这个哥萨克人才没发现我。
卡斯伯格的第二个念头更可怕,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他为什么暗笑?又为什么转身回去?
卡斯伯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得出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就如同此时太阳已经推开晨雾光临万物一样确凿无疑。他在耍我!他是要留着我,再玩一天!这个哥萨克就是一只猫,我呢,就是一只鼠。卡斯伯格一下子体会到了恐怖的全部含义。
“你不能屈服,不能!”
卡斯伯格从树上滑下来,又钻进了灌木丛。他一脸凝重,大脑几乎凝固。他跑了三百来码。停下脚。他发现一棵高大的枯树正好压在一棵小树上,卡斯伯格扔掉干粮袋,从刀鞘里抽出猎刀,用尽浑身力气砍起小树来。
终于砍完了,卡斯伯格在一百多英尺外的一截落木后边趴下。用不了多长时间,猫又会赶来。耍他这只鼠了。
萨斯基将军带着自信,牵着猎狗,沿着卡斯伯格的踪迹一路追过来。卡斯伯格留下的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不管是一片草叶,一块树皮,还是半个脚印,总之一切都逃不过他那一双恶黑的眼睛。这个哥萨克专心致志,轻手轻脚,卡斯伯格留下的这些踪迹,都被他发现了。他的脚碰到一根耸着的大树枝上,这根树枝恰恰就是卡斯伯格设下的机关。就在他碰到这根树枝的时候,萨斯基就嗅出了它的危险,他猿猴般敏捷地往后跳去。但他快得还不够,刚好靠在被卡斯伯格砍削过的那棵小树上的死树,哗地一声就砸下来,擦伤了萨斯基的肩膀。要不是萨斯基机敏,肯定会被砸在树下。他晃了一下,却没有被砸倒,也没砸掉左轮手枪。他站在那里,揉着受伤的那只胳膊。卡斯伯格的心一下子被恐惧攫住,他听见萨斯基的嘲笑透过灌木丛传过来:
“卡斯伯格,”萨斯基喊道,“我估计你就在附近,能够听到我的声音,那么我祝贺你。知道怎么设这种马来亚人套子的并不多。巧得很,我也在马六甲打过猎,我懂这玩艺儿。事实证明你很有意思,卡斯伯格先生。我回去包扎一下伤口,只是一点儿轻伤。我还会回来,还会回来的。”
萨斯基捂着他受了伤的胳膊一走,卡斯伯格又开始逃命。这可真是逃命,绝望的,绝命的奔逃。他逃到了一片竹林,又有了个办法,于是他抽出猎刀砍起竹子来,不大一会儿就做起了弓箭,这是一些特种兵通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也是他见过的最原始的办法。如果萨斯基放出许多的猎狗来,也许会用得上,想到这才有了一些宽慰。天暗下来,又黑下去,他逃啊逃。他觉得鹿皮鞋下的地越来越软,草木越来越密,越来越厚,蚊虫也疯狂地咬。就在他慢下脚步往前走的时候,脚被陷进了软沙里。他使劲把脚往上拽,沙子立即象吸血的水蛭一样钻进脚踝。折腾了好一阵,他才把脚拽出来。他知道,这儿就是流沙遍地的死亡沙漠。
踩在松软的沙地上,他突然有了主意。他从流沙里慢慢往回走。大约走了十几英尺远,他开始像巨大的史前水獭,在沙地上挖起洞来。
卡斯伯格二战期间在法国作战时,曾经挖沙隐蔽自己,那时候耽误一秒钟就意味着死亡,但与现在相比,简直就是消遣。洞越挖越深了,等到只露出脑袋的时候,他爬出来,从硬木树上砍下枝杈,削成尖尖的木签,而后把这些木签尖朝上埋进坑底。接着,他又用野草、树枝编了个盖子盖在坑顶上,掩上沙子。最后,他汗流浃背地拖着酸软的双腿,挪到一棵遭过雷击而烧焦的树后面,蹲下。
他知道追踪者到了:他听见踏在松软沙地上的脚步声,夜风送过来萨斯基吸的烟的香味儿,卡斯伯格感到萨斯基来得如此迅速,简直不是一边摸索一边一步步走来的。他蹲在地上,看不见那个陷阱。短短的一分钟在他就像是过了一年。他听见盖陷阱口的树枝断裂所发出的吱嗄声,这一刻他几乎兴奋得叫出声。他从藏身的地方跳起来,紧接着,却又像遭了电击一样地缩了下去。离陷阱三英尺外正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
“你干得很好,卡斯伯格,”萨斯基叫道,“你的缅甸陷虎坑干掉了我最好的一只猎犬。我想你又得了一分。卡斯伯格,我看你怎么对付一群猎犬。现在我回去休息一下,谢谢你让我度过了这么个有意思的夜晚。”
萨斯基一走,卡斯伯格立即动起了脑筋,他不顾疲惫地再次走到竹林,想设个更大的机关对付萨斯基和一群猎犬了。但愿自己走运,他用猎刀再次砍起了竹子,并且将竹子分成几捆做成弓状而用众多竹箭对向来路,他知道追踪者很快又要到了。并且又往身上加了些竹箭。
天亮的时候,躺在沙地上的卡斯伯格被一个声音惊醒。这个声音让他领教了另一种恐惧,这个声音时断时续,隐隐约约。他能分辨出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一群猎犬的狂吠声。
卡斯伯格想,他可以呆在这儿等着,但,那就是等死;自己设的陷阱行不行还未可知。他也可以逃,那也逃不脱死亡,只能使死亡推迟一点儿。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究竟该怎么办。突然,他脑海里又闪出一个主意,他紧了紧腰带,开始往外跑。
猎犬的狂吠声近了,近了,更近了,越来越近了。在一个土坎上,卡斯伯格爬上一棵树。小河边,他看见灌木丛在动,离这里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卡斯伯格瞪起两眼,看见了瘦高的萨斯基,在他前面,是一个宽肩阔背的家伙,在高高的灌木丛里晃动。是壮汉奥特。他还看见奥特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牵着往前走,卡斯伯格知道,奥特牵的一定是那群猎犬。
他们每时每刻都会扑上来。卡斯伯格从树上滑下来,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那片竹林,仍就顾自地逃命。猎犬似乎已经嗅到了他的味儿,愈加疯狂地嚎叫起来。卡斯伯格体会到了被追猎的滋味。
他不得不停住脚喘口气儿,这时,那群猎狗的狂吠声也突然停住,卡斯伯格的心一下子停跳了;他们可能?……
不祥的夜色宛如一条受了伤的毒蛇,慢慢地爬上来。丛林里一片死寂,瞌睡却没有降临到卡斯伯格。天快亮了,天空一片暗灰。就在这时,远处一只惊鸟的叫声引起了卡斯伯格的注意:什么东西正沿着卡斯伯格的来路,穿过灌木丛,慢慢地,轻轻地摸了过来。卡斯伯格透过浓密如织的树叶看去。来的是个人。
这个人就是萨斯基将军。他一路追踪而来,眼睛紧盯着地面。快到大树的时候,他停住脚步,双膝跪地,察看地上的痕迹。要不是看到他右手握着的那个刺眼的东西——一只小巧的自动手枪,卡斯伯格几乎要像猛虎下山一样扑下来了。
萨斯基摇了几下头,似乎感到很困惑。接着,他站起来,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黑色香烟。香烟刺鼻的香味飘过来,钻进卡斯伯格的鼻孔。
卡斯伯格屏住呼吸。将军的眼睛已经离开地面,一寸一寸地沿着树干往上移。卡斯伯格僵住了,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扑下去。但萨斯基锐利的眼睛快到卡斯伯格藏身的树枝时却停下来,微笑在他棕色的脸上荡漾开来。他深思熟虑般地吐了个烟圈儿,然后转过身子,沿着他走来的方向,若无其事地往回走。皮靴踩在小灌木上发出的沙沙声渐渐远去。
卡斯伯格长舒一口憋在肚里的气。第一个念头让他几乎绝望:萨斯基竟然能够在这么个黑夜里,穿过丛林跟踪找到树下,只是因为一念之差,这个哥萨克人才没发现我。
卡斯伯格的第二个念头更可怕,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他为什么暗笑?又为什么转身回去?
卡斯伯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得出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就如同此时太阳已经推开晨雾光临万物一样确凿无疑。他在耍我!他是要留着我,再玩一天!这个哥萨克就是一只猫,我呢,就是一只鼠。卡斯伯格一下子体会到了恐怖的全部含义。
“你不能屈服,不能!”
卡斯伯格从树上滑下来,又钻进了灌木丛。他一脸凝重,大脑几乎凝固。他跑了三百来码。停下脚。他发现一棵高大的枯树正好压在一棵小树上,卡斯伯格扔掉干粮袋,从刀鞘里抽出猎刀,用尽浑身力气砍起小树来。
终于砍完了,卡斯伯格在一百多英尺外的一截落木后边趴下。用不了多长时间,猫又会赶来。耍他这只鼠了。
萨斯基将军带着自信,牵着猎狗,沿着卡斯伯格的踪迹一路追过来。卡斯伯格留下的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不管是一片草叶,一块树皮,还是半个脚印,总之一切都逃不过他那一双恶黑的眼睛。这个哥萨克专心致志,轻手轻脚,卡斯伯格留下的这些踪迹,都被他发现了。他的脚碰到一根耸着的大树枝上,这根树枝恰恰就是卡斯伯格设下的机关。就在他碰到这根树枝的时候,萨斯基就嗅出了它的危险,他猿猴般敏捷地往后跳去。但他快得还不够,刚好靠在被卡斯伯格砍削过的那棵小树上的死树,哗地一声就砸下来,擦伤了萨斯基的肩膀。要不是萨斯基机敏,肯定会被砸在树下。他晃了一下,却没有被砸倒,也没砸掉左轮手枪。他站在那里,揉着受伤的那只胳膊。卡斯伯格的心一下子被恐惧攫住,他听见萨斯基的嘲笑透过灌木丛传过来:
“卡斯伯格,”萨斯基喊道,“我估计你就在附近,能够听到我的声音,那么我祝贺你。知道怎么设这种马来亚人套子的并不多。巧得很,我也在马六甲打过猎,我懂这玩艺儿。事实证明你很有意思,卡斯伯格先生。我回去包扎一下伤口,只是一点儿轻伤。我还会回来,还会回来的。”
萨斯基捂着他受了伤的胳膊一走,卡斯伯格又开始逃命。这可真是逃命,绝望的,绝命的奔逃。他逃到了一片竹林,又有了个办法,于是他抽出猎刀砍起竹子来,不大一会儿就做起了弓箭,这是一些特种兵通常使用的一种方法,也是他见过的最原始的办法。如果萨斯基放出许多的猎狗来,也许会用得上,想到这才有了一些宽慰。天暗下来,又黑下去,他逃啊逃。他觉得鹿皮鞋下的地越来越软,草木越来越密,越来越厚,蚊虫也疯狂地咬。就在他慢下脚步往前走的时候,脚被陷进了软沙里。他使劲把脚往上拽,沙子立即象吸血的水蛭一样钻进脚踝。折腾了好一阵,他才把脚拽出来。他知道,这儿就是流沙遍地的死亡沙漠。
踩在松软的沙地上,他突然有了主意。他从流沙里慢慢往回走。大约走了十几英尺远,他开始像巨大的史前水獭,在沙地上挖起洞来。
卡斯伯格二战期间在法国作战时,曾经挖沙隐蔽自己,那时候耽误一秒钟就意味着死亡,但与现在相比,简直就是消遣。洞越挖越深了,等到只露出脑袋的时候,他爬出来,从硬木树上砍下枝杈,削成尖尖的木签,而后把这些木签尖朝上埋进坑底。接着,他又用野草、树枝编了个盖子盖在坑顶上,掩上沙子。最后,他汗流浃背地拖着酸软的双腿,挪到一棵遭过雷击而烧焦的树后面,蹲下。
他知道追踪者到了:他听见踏在松软沙地上的脚步声,夜风送过来萨斯基吸的烟的香味儿,卡斯伯格感到萨斯基来得如此迅速,简直不是一边摸索一边一步步走来的。他蹲在地上,看不见那个陷阱。短短的一分钟在他就像是过了一年。他听见盖陷阱口的树枝断裂所发出的吱嗄声,这一刻他几乎兴奋得叫出声。他从藏身的地方跳起来,紧接着,却又像遭了电击一样地缩了下去。离陷阱三英尺外正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
“你干得很好,卡斯伯格,”萨斯基叫道,“你的缅甸陷虎坑干掉了我最好的一只猎犬。我想你又得了一分。卡斯伯格,我看你怎么对付一群猎犬。现在我回去休息一下,谢谢你让我度过了这么个有意思的夜晚。”
萨斯基一走,卡斯伯格立即动起了脑筋,他不顾疲惫地再次走到竹林,想设个更大的机关对付萨斯基和一群猎犬了。但愿自己走运,他用猎刀再次砍起了竹子,并且将竹子分成几捆做成弓状而用众多竹箭对向来路,他知道追踪者很快又要到了。并且又往身上加了些竹箭。
天亮的时候,躺在沙地上的卡斯伯格被一个声音惊醒。这个声音让他领教了另一种恐惧,这个声音时断时续,隐隐约约。他能分辨出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一群猎犬的狂吠声。
卡斯伯格想,他可以呆在这儿等着,但,那就是等死;自己设的陷阱行不行还未可知。他也可以逃,那也逃不脱死亡,只能使死亡推迟一点儿。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究竟该怎么办。突然,他脑海里又闪出一个主意,他紧了紧腰带,开始往外跑。
猎犬的狂吠声近了,近了,更近了,越来越近了。在一个土坎上,卡斯伯格爬上一棵树。小河边,他看见灌木丛在动,离这里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卡斯伯格瞪起两眼,看见了瘦高的萨斯基,在他前面,是一个宽肩阔背的家伙,在高高的灌木丛里晃动。是壮汉奥特。他还看见奥特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牵着往前走,卡斯伯格知道,奥特牵的一定是那群猎犬。
他们每时每刻都会扑上来。卡斯伯格从树上滑下来,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那片竹林,仍就顾自地逃命。猎犬似乎已经嗅到了他的味儿,愈加疯狂地嚎叫起来。卡斯伯格体会到了被追猎的滋味。
他不得不停住脚喘口气儿,这时,那群猎狗的狂吠声也突然停住,卡斯伯格的心一下子停跳了;他们可能?……
上一章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