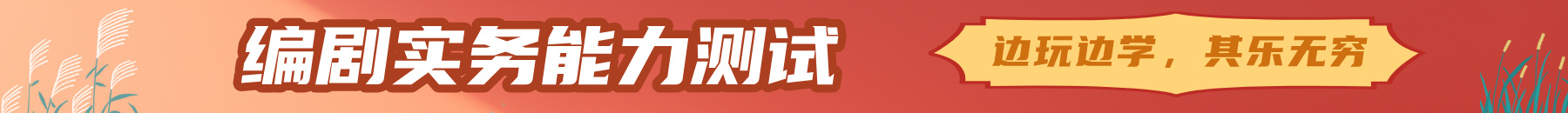权属:原创 · 独家授权
字数:5876
阅读:7085
发表:2014/6/11
34章 主旋律 小说
《红云白雾》第28章:三
0
…
28
28
29
…
34
全部
第二十八章(三)作品名:红云白雾 作者:任勤
用餐过后,大家都相约着去跳舞,唱歌,高洁却将邱成峰约到了会客室,她招呼服务生,要了两杯咖啡,服务生离开后,她主动问起了邱成峰。
“经常与林秋月和孩子通话吗?她们母子俩在国外怎么样?”
“每周都通话,那边都挺好的,邱霖的奖学金就够他们娘俩用了,我每次要给他们打些钱,都遭到拒绝。林秋月最近要在那边参加医务专业从业资格考试,通过后就可以在相关的医疗机构找一份工作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美国?一家三口人,长期分居大洋两岸也不妥呀!”
“我在国内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邱霖还要在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在我和邱霖之间,林秋月选定的是邱霖,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邱霖!’其实,自从有了邱霖之后,她不仅疏远了我,而且已经失去了‘自我’。”
“与秋月比起来,在家庭生活方面,我们都显得有些自私了。”高洁感慨的说。
“秋月虽然人到了美国,可仍然保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不顾‘自我’、心甘情愿的‘倾心教子’,我们虽然还呆在自己这片国土上,但思想却有些西化,开始更多的注重‘自我’了!”邱成峰也在感叹着。
“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比较赞同西方人的观念,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的权力。如果每个人都为了别人——哪怕这‘别人’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子女——而牺牲了自己的这些权力,那么这种牺牲也是不公平、无价值、无意义的。”
“富含哲理的思辨!其实林秋月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为了邱霖而牺牲了‘自我’。算了,不谈这些了,谈谈你吧,最近在做些什么?你那本《乌托邦——社会学中的莫尔猜想》出版了吗?”
“都十多年的事情了,你还记得。那本小册子没有获准公开出版,系里只是作为内部教材和院校间的交换资料印了一些,八九年,我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后,就把它搁置到一边了。前一段时间,我把从 文革 开始,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所写的日记整理了一下,按照 文革 、插队、上大学三个不同时期,编成了三部分,分别为《 文革 日记》、《插队日记》和《大学日记》。”
“好啊!早就听林秋月和其他女同学说过,你有每天都记日记的习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但你可从来没将你的日记向我公开过。对了!那篇‘攻击’林副统帅的日记也在其中吗?”
“当然在《 文革 日记》中了!”
“那太好了!要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渴望能看到你那本日记。赞同你的人是想一睹为快,反对你的人是想探寻到批判你的材料,进而达到打击你们‘八•;;;一八’派的目的,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好奇,想近距离的窥视一下你这位‘神枪女杰’神秘的内心世界,我便是属于后者,可是当时听说那本日记被你母亲给烧了呀?”
“那是她顺水推舟、放的一颗烟雾弹。当时,你们‘无联总’抄家队的人去我家的时候,她正在烧一些可能被人抓把柄的笔记和其它材料,但并没有我的那个日记本。抄家队的头头要她交出我的日记时,她就故意说,家里所有的日记、笔记本等文字材料都已经烧掉了,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阿姨真是有胆有识,演了这么一出偷梁换柱的好戏,可是你的日记本当时在哪里?又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这多亏了赵炎,他办了一件具有地下工作和传奇色彩的十分惊险的事!既救了我、又将这本日记保存了下来。”高洁的语调中带着伤感和怀念。
“地下工作?传奇色彩?十分惊险的事?我怎么没听说过?”邱成峰惊诧的一连用了几个问号。
“不仅你没听说过,多少年来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那本日记究竟落到了何处。尽管当时母亲一再告诉我,那本日记她确实没有烧掉,叮嘱我一定要找到它,亲手把它销毁,以免留下后患,可是我翻遍了家里所有可能藏匿它的角落,也翻遍了我们‘虎山行’战斗队女队员的几处临时宿舍,把我随身所带的东西都抖落个遍,却始终没有找到它。为此,多年来我一直深信,一定是母亲把它烧掉了,只是由于她自己没有记清,又担心万一落到对立派的手里,被人抓住把柄,对我造成危害,因此才不留余地的、宁可认定自己没有烧掉它。”
“那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赵炎就是抄家队的成员,那天,当抄家队的大多数人围着正在烧材料的母亲追问我的日记时,他一个人进了我的卧室,撬开我写字台的上着锁的抽屉,找到了我的那本日记。他匆匆的翻了几页之后,从里面所记的内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情急之中,他将自己的《 毛主席 语录》外面的塑料皮拆了下来,套在了我的日记本上,然后装进了那只每次活动都要背在身上、专门用来装《 毛主席 语录》红布口袋里,这才使我的那本日记有惊无险的逃过了一劫,也使我避过了一场劫难。”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本日记他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回到你手里的?”
“回到家里后,他又为如何安全的藏好这本日记,费了一番心思。第二天,他找到吴文甫,借口家里的一尊 毛主席 石膏像的底座碰掉了一块,然后和吴文甫一起到他父亲医院的骨科要了一些石膏粉。晚上,他一个人躲在家里,将日记本用牛皮纸包好,放到 毛主席 石膏像底座的空腔里,然后用水调好石膏粉将本来敞开的底座封死,这才放心的将石膏像放回原处。
“直到我们下乡时,他才小心的抠开石膏像的底座,取出日记本,此后,这本日记就一直藏在他的箱底。赵炎失踪后,他的箱子原封不动的放着,赵艳也无心清理,直到七四年,赵艳上卫校前,在清理自己和哥哥的衣物时才发现了这本日记。她本想早些还给我,但却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我的日记是怎么落到他哥哥的手里的,怕因此引起我的误会。春节前接到赵炎的遗书后,她才决定把它交还给我,但对于日记本究竟是如何落到赵炎手里的,她和我仍然不得而知。
“我和她去哈尔滨找罗永莉时,罗永莉交给了我们一个赵炎留下的笔记本。赵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个笔记本中,写下了他的真实的‘自传’,记下了自己一些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以及多年来复杂的思想情感变化,其中就有他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保存我的这本日记的内容。罗永莉说,赵炎直到临终时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该将这份写着‘自传’的笔记本交给我们、公之于众,所以便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嘱咐罗永莉,如果家人不去寻认自己就算了,如果家人或老同学、老朋友去寻认自己,就将这个笔记本交给他们,也算是对家人和同学有了一个最终的、明确的交代。”
“真的是太传奇了!赵炎应当是你真正的知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政治生命的守护神!”邱成峰带着几分伤感、几分失落,他自觉在对高洁的情感方面,自己远不及赵炎那样深沉、厚重、无私与无畏。
“你说的毫不过分,我对他情感上的亏欠太多,而且没有了弥补的机会!”高洁毫不掩饰的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
“不要伤心了!心里装着他就是了。如果你后半生过的幸福而有意义,心里又装着他,就算没辜负他对你所做的一切,没有辜负他对你的一片真情,那么,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但愿如此、也只能如此了!”
“对了,这三本日记你准备怎么处理?我能有幸拜读吗?”为了缓解伤感的情绪,邱成峰不再谈赵炎的事。
“我把三本整理好的日记都送到了北方大学出版社,编审看过之后,认为除了插队时的日记略经删改便可以出版外,另外两本暂时还不适宜出版,但他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以后应该会有出版的机会。”
“暂时能出版一本也很好啊!现在出版这样一本日记,是非常合时宜的。我们这一代 文革 后的老知青,进入了中年以后,普遍的产生了怀旧的心理,现在很多老知青都对当年的照片、家书和日记等能唤起记忆的东西产生了兴趣,如果你的这本日记真的出版了,你能得到一些稿酬不说,它还能成为帮助我们回顾那一段岁月,重新品味青春之梦的索引。”
“近来,当我自己翻看 文革 和大学日记的时候,总是在怀旧,但在翻看完《插队日记》时,我却有了更多的感慨和思考。当年的插队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现在我们摆脱了那样的生活,可溪河湾的乡亲们,还仍然祖祖辈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勉强维持着温饱、远没能达到小康的水平。不过,溪河湾虽然贫穷落后,但有山有水、自然资源丰富,正像当年张主任到学校接我们去那里插队时所说的,‘溪河湾山清水秀’就需要我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去开发它,建设它,让它成为花果山、鱼米乡。
“可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山’不仅没成为‘花果山’,反而因为多年的滥砍盗伐而近乎于‘荒山秃岭’;‘乡’不仅没能成为‘鱼米乡’反而因为竭泽而渔、水土流失、河道堵塞,而成了污水浊流的穷乡僻壤。尽管现在上自政府、下到普通百姓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封山育林、疏通河道、治理污染的相关政策,但因为当地的财政紧张,老乡们的生活也不富裕,因而投入的资金有限,难以在短期内收到成效,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呐!”高洁感慨颇深的说。
“对此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想法?”
“你这样问我,说明我所想的问题你可能也想到了!如果我们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为溪河湾投入一些资金,促进村里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把那里建成一个山清水秀,适宜人们生活居住地方。因此,我想把我现在的全部积蓄,以及出版这本日记可能带来的版权收益都投在溪河湾,用来做这样几件事:第一、帮助溪河湾的乡亲们发展绿色环保经济,不仅使他们的收入增加,摆脱贫困,早日实现小康,而且使那里的山更青,水更秀、天更蓝;第二、在我们青年点原址,建一栋老年公寓,我们退休之后就到那里去养老,这样,我们既可以过上陶渊明理想中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又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我们当年提出的‘扎根农村干革命、五•;;;七道路走全程’的誓言;第三、全面改造南山头,在那里建一个小型的公墓区,在赵炎墓的两侧各建一个寄骨亭,凡是在溪河湾生活过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百年之后都可以将骨灰安放在那里,或者深埋在墓区限定的地方,同时在上面栽植一棵树——也就是所谓的‘树葬’。这样,我们的养老和人生的归宿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
“你的想法很有创意,特别是第一点,我非常赞同!一会儿我把常守志和黎晓华找来,咱们把事情考虑的再详细和具体些,过些日子,再由他们俩出面,召集同学们共同商量一下,此事如果能得到多数同学的赞同,实现的可能性就很大。对于第二点吗,我还存在一些疑问和顾虑。”
“有什么疑问和顾虑?”
“你所说的回溪河湾养老,是短期疗养、休闲式的,还是长期定居?”
“当然是长期定居!邱成峰,我已经猜到你的顾虑是什么了。”
“既然猜到了,那你就说说看!”
“你可能认为我们的晚年生活不适合在溪河湾养老,而最大的顾虑就是医疗条件问题。”
“看来你的确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而且往往是猝发性的,如果抢救不及时,便会危及生命,所以老年人应选择医疗条件好、便于就医的地方养老,而不适合在溪河湾这样的地方。”邱成峰解释着自己的想法。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老年人应当选择医疗条件好的地方养老,而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一个公平、公正、理想而又人性化的社会,应当为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提供一个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
“可是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邱成峰还是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但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行动来推进这个现实的改变。我们是城里人,而且通常被认为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城里人,我们到农村——偏远山区的农村去养老,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会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当然,在一定时间内,这种改善是相当有限的,我们也会为此而承担一定的风险,甚至会做出一些牺牲。但是,从人权平等的角度来讲,普通农民老了,理所当然的在农村养老,城里人老了为什么就不能在农村养老呢?我认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应当只考虑自己要选择一个医疗条件好的地方去养老,更应当为改善全社会的医疗条件——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医疗条件——做出一些积极的努力。
“我们当年到溪河湾插队时的指导思想,和今天要到溪河湾养老的想法,都是源于消灭城乡差别的愿望和道义,为此,我们自己多承担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况且对于心脑血管这种猝发性的疾病,并非人人都会得,而对于多数的慢性疾病来说,耽误个三、五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定期到省城资质好的大医院体检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高洁对这个问题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高洁,我现在完全理解了你的这种高度自觉的民主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对于这第二点,我也完全赞同!”
“那么对于第三点,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对于第三点,我个人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我只是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暂时先不考虑为好,因为对于多数同学来说,过早的考虑这个问题,会影响人的情绪,会给人带来压抑感······”。
——
高洁的想法不仅得到了常守志和黎晓华的赞同,也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赞同,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决定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并称其为“五七道路拓展计划”。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大家积极捐款,几天的工夫就筹集到了十多万元的资金,其中捐款最多的是常守志、高洁和黄龙彪,他们每人都捐了三万元。其实,黄龙彪在所有同学中是最有经济实力的,他完全可以捐的再多一些,但他却在同学中公开的说,自己是个商人,而商人在往出掏钱时,考虑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是能否有相应的回报,能否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从这一原则出发,他自己是不赞同这个所谓的“拓展计划”的,因为溪河湾地处偏僻山区,交通极不方便,在那里投资效益低,还可能无效益,甚至“血本无归”,而且那里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也不适合老年人养老,所以他无意在那里投入太多的资金,只是因为自己曾在那里插过队,才捐助了这三万元。
对于黄龙彪这种消极的态度,常守志、黎晓华和高洁都很不满意。常守志针对黄龙彪的这种态度还特别做了一个声明:在两、三年内,自己还将再捐款三到五万元。
九月二十日,插队三十周年之际,同学们带着筹集到的资金回到了溪河湾。黎晓华代表全体同学与溪河湾村委会主任王金玉签订了“‘五·七道路拓展计划’的实施协议”。在协议中,双方约定,同学们捐助的资金必须全部投入到“拓展计划”中去,用来发展溪河湾的集体经济。具体的实施步骤是:首先,筹建溪河湾林蛙养殖基地和人参栽培基地;经过三到五年的发展,再利用回收的资金和其它追加投资,建虹鳟鱼、甲鱼养殖基地以及驯鹿场;还要在适当的时机,在青年点原址建一座老年公寓。
签署协议后,黎晓华和常守志将资金交给了王金玉和村会计,当然,这些资金和后续追加资金,都将在知青代表黎晓华的监督下使用。
用餐过后,大家都相约着去跳舞,唱歌,高洁却将邱成峰约到了会客室,她招呼服务生,要了两杯咖啡,服务生离开后,她主动问起了邱成峰。
“经常与林秋月和孩子通话吗?她们母子俩在国外怎么样?”
“每周都通话,那边都挺好的,邱霖的奖学金就够他们娘俩用了,我每次要给他们打些钱,都遭到拒绝。林秋月最近要在那边参加医务专业从业资格考试,通过后就可以在相关的医疗机构找一份工作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美国?一家三口人,长期分居大洋两岸也不妥呀!”
“我在国内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邱霖还要在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在我和邱霖之间,林秋月选定的是邱霖,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邱霖!’其实,自从有了邱霖之后,她不仅疏远了我,而且已经失去了‘自我’。”
“与秋月比起来,在家庭生活方面,我们都显得有些自私了。”高洁感慨的说。
“秋月虽然人到了美国,可仍然保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不顾‘自我’、心甘情愿的‘倾心教子’,我们虽然还呆在自己这片国土上,但思想却有些西化,开始更多的注重‘自我’了!”邱成峰也在感叹着。
“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比较赞同西方人的观念,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的权力。如果每个人都为了别人——哪怕这‘别人’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子女——而牺牲了自己的这些权力,那么这种牺牲也是不公平、无价值、无意义的。”
“富含哲理的思辨!其实林秋月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为了邱霖而牺牲了‘自我’。算了,不谈这些了,谈谈你吧,最近在做些什么?你那本《乌托邦——社会学中的莫尔猜想》出版了吗?”
“都十多年的事情了,你还记得。那本小册子没有获准公开出版,系里只是作为内部教材和院校间的交换资料印了一些,八九年,我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后,就把它搁置到一边了。前一段时间,我把从 文革 开始,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所写的日记整理了一下,按照 文革 、插队、上大学三个不同时期,编成了三部分,分别为《 文革 日记》、《插队日记》和《大学日记》。”
“好啊!早就听林秋月和其他女同学说过,你有每天都记日记的习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但你可从来没将你的日记向我公开过。对了!那篇‘攻击’林副统帅的日记也在其中吗?”
“当然在《 文革 日记》中了!”
“那太好了!要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渴望能看到你那本日记。赞同你的人是想一睹为快,反对你的人是想探寻到批判你的材料,进而达到打击你们‘八•;;;一八’派的目的,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好奇,想近距离的窥视一下你这位‘神枪女杰’神秘的内心世界,我便是属于后者,可是当时听说那本日记被你母亲给烧了呀?”
“那是她顺水推舟、放的一颗烟雾弹。当时,你们‘无联总’抄家队的人去我家的时候,她正在烧一些可能被人抓把柄的笔记和其它材料,但并没有我的那个日记本。抄家队的头头要她交出我的日记时,她就故意说,家里所有的日记、笔记本等文字材料都已经烧掉了,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阿姨真是有胆有识,演了这么一出偷梁换柱的好戏,可是你的日记本当时在哪里?又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这多亏了赵炎,他办了一件具有地下工作和传奇色彩的十分惊险的事!既救了我、又将这本日记保存了下来。”高洁的语调中带着伤感和怀念。
“地下工作?传奇色彩?十分惊险的事?我怎么没听说过?”邱成峰惊诧的一连用了几个问号。
“不仅你没听说过,多少年来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那本日记究竟落到了何处。尽管当时母亲一再告诉我,那本日记她确实没有烧掉,叮嘱我一定要找到它,亲手把它销毁,以免留下后患,可是我翻遍了家里所有可能藏匿它的角落,也翻遍了我们‘虎山行’战斗队女队员的几处临时宿舍,把我随身所带的东西都抖落个遍,却始终没有找到它。为此,多年来我一直深信,一定是母亲把它烧掉了,只是由于她自己没有记清,又担心万一落到对立派的手里,被人抓住把柄,对我造成危害,因此才不留余地的、宁可认定自己没有烧掉它。”
“那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赵炎就是抄家队的成员,那天,当抄家队的大多数人围着正在烧材料的母亲追问我的日记时,他一个人进了我的卧室,撬开我写字台的上着锁的抽屉,找到了我的那本日记。他匆匆的翻了几页之后,从里面所记的内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情急之中,他将自己的《 毛主席 语录》外面的塑料皮拆了下来,套在了我的日记本上,然后装进了那只每次活动都要背在身上、专门用来装《 毛主席 语录》红布口袋里,这才使我的那本日记有惊无险的逃过了一劫,也使我避过了一场劫难。”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本日记他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回到你手里的?”
“回到家里后,他又为如何安全的藏好这本日记,费了一番心思。第二天,他找到吴文甫,借口家里的一尊 毛主席 石膏像的底座碰掉了一块,然后和吴文甫一起到他父亲医院的骨科要了一些石膏粉。晚上,他一个人躲在家里,将日记本用牛皮纸包好,放到 毛主席 石膏像底座的空腔里,然后用水调好石膏粉将本来敞开的底座封死,这才放心的将石膏像放回原处。
“直到我们下乡时,他才小心的抠开石膏像的底座,取出日记本,此后,这本日记就一直藏在他的箱底。赵炎失踪后,他的箱子原封不动的放着,赵艳也无心清理,直到七四年,赵艳上卫校前,在清理自己和哥哥的衣物时才发现了这本日记。她本想早些还给我,但却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我的日记是怎么落到他哥哥的手里的,怕因此引起我的误会。春节前接到赵炎的遗书后,她才决定把它交还给我,但对于日记本究竟是如何落到赵炎手里的,她和我仍然不得而知。
“我和她去哈尔滨找罗永莉时,罗永莉交给了我们一个赵炎留下的笔记本。赵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个笔记本中,写下了他的真实的‘自传’,记下了自己一些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以及多年来复杂的思想情感变化,其中就有他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保存我的这本日记的内容。罗永莉说,赵炎直到临终时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该将这份写着‘自传’的笔记本交给我们、公之于众,所以便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嘱咐罗永莉,如果家人不去寻认自己就算了,如果家人或老同学、老朋友去寻认自己,就将这个笔记本交给他们,也算是对家人和同学有了一个最终的、明确的交代。”
“真的是太传奇了!赵炎应当是你真正的知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你政治生命的守护神!”邱成峰带着几分伤感、几分失落,他自觉在对高洁的情感方面,自己远不及赵炎那样深沉、厚重、无私与无畏。
“你说的毫不过分,我对他情感上的亏欠太多,而且没有了弥补的机会!”高洁毫不掩饰的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
“不要伤心了!心里装着他就是了。如果你后半生过的幸福而有意义,心里又装着他,就算没辜负他对你所做的一切,没有辜负他对你的一片真情,那么,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但愿如此、也只能如此了!”
“对了,这三本日记你准备怎么处理?我能有幸拜读吗?”为了缓解伤感的情绪,邱成峰不再谈赵炎的事。
“我把三本整理好的日记都送到了北方大学出版社,编审看过之后,认为除了插队时的日记略经删改便可以出版外,另外两本暂时还不适宜出版,但他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以后应该会有出版的机会。”
“暂时能出版一本也很好啊!现在出版这样一本日记,是非常合时宜的。我们这一代 文革 后的老知青,进入了中年以后,普遍的产生了怀旧的心理,现在很多老知青都对当年的照片、家书和日记等能唤起记忆的东西产生了兴趣,如果你的这本日记真的出版了,你能得到一些稿酬不说,它还能成为帮助我们回顾那一段岁月,重新品味青春之梦的索引。”
“近来,当我自己翻看 文革 和大学日记的时候,总是在怀旧,但在翻看完《插队日记》时,我却有了更多的感慨和思考。当年的插队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现在我们摆脱了那样的生活,可溪河湾的乡亲们,还仍然祖祖辈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勉强维持着温饱、远没能达到小康的水平。不过,溪河湾虽然贫穷落后,但有山有水、自然资源丰富,正像当年张主任到学校接我们去那里插队时所说的,‘溪河湾山清水秀’就需要我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去开发它,建设它,让它成为花果山、鱼米乡。
“可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山’不仅没成为‘花果山’,反而因为多年的滥砍盗伐而近乎于‘荒山秃岭’;‘乡’不仅没能成为‘鱼米乡’反而因为竭泽而渔、水土流失、河道堵塞,而成了污水浊流的穷乡僻壤。尽管现在上自政府、下到普通百姓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封山育林、疏通河道、治理污染的相关政策,但因为当地的财政紧张,老乡们的生活也不富裕,因而投入的资金有限,难以在短期内收到成效,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呐!”高洁感慨颇深的说。
“对此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想法?”
“你这样问我,说明我所想的问题你可能也想到了!如果我们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为溪河湾投入一些资金,促进村里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把那里建成一个山清水秀,适宜人们生活居住地方。因此,我想把我现在的全部积蓄,以及出版这本日记可能带来的版权收益都投在溪河湾,用来做这样几件事:第一、帮助溪河湾的乡亲们发展绿色环保经济,不仅使他们的收入增加,摆脱贫困,早日实现小康,而且使那里的山更青,水更秀、天更蓝;第二、在我们青年点原址,建一栋老年公寓,我们退休之后就到那里去养老,这样,我们既可以过上陶渊明理想中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又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我们当年提出的‘扎根农村干革命、五•;;;七道路走全程’的誓言;第三、全面改造南山头,在那里建一个小型的公墓区,在赵炎墓的两侧各建一个寄骨亭,凡是在溪河湾生活过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百年之后都可以将骨灰安放在那里,或者深埋在墓区限定的地方,同时在上面栽植一棵树——也就是所谓的‘树葬’。这样,我们的养老和人生的归宿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
“你的想法很有创意,特别是第一点,我非常赞同!一会儿我把常守志和黎晓华找来,咱们把事情考虑的再详细和具体些,过些日子,再由他们俩出面,召集同学们共同商量一下,此事如果能得到多数同学的赞同,实现的可能性就很大。对于第二点吗,我还存在一些疑问和顾虑。”
“有什么疑问和顾虑?”
“你所说的回溪河湾养老,是短期疗养、休闲式的,还是长期定居?”
“当然是长期定居!邱成峰,我已经猜到你的顾虑是什么了。”
“既然猜到了,那你就说说看!”
“你可能认为我们的晚年生活不适合在溪河湾养老,而最大的顾虑就是医疗条件问题。”
“看来你的确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而且往往是猝发性的,如果抢救不及时,便会危及生命,所以老年人应选择医疗条件好、便于就医的地方养老,而不适合在溪河湾这样的地方。”邱成峰解释着自己的想法。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老年人应当选择医疗条件好的地方养老,而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一个公平、公正、理想而又人性化的社会,应当为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提供一个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
“可是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邱成峰还是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但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行动来推进这个现实的改变。我们是城里人,而且通常被认为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城里人,我们到农村——偏远山区的农村去养老,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会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当然,在一定时间内,这种改善是相当有限的,我们也会为此而承担一定的风险,甚至会做出一些牺牲。但是,从人权平等的角度来讲,普通农民老了,理所当然的在农村养老,城里人老了为什么就不能在农村养老呢?我认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应当只考虑自己要选择一个医疗条件好的地方去养老,更应当为改善全社会的医疗条件——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医疗条件——做出一些积极的努力。
“我们当年到溪河湾插队时的指导思想,和今天要到溪河湾养老的想法,都是源于消灭城乡差别的愿望和道义,为此,我们自己多承担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况且对于心脑血管这种猝发性的疾病,并非人人都会得,而对于多数的慢性疾病来说,耽误个三、五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定期到省城资质好的大医院体检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高洁对这个问题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高洁,我现在完全理解了你的这种高度自觉的民主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对于这第二点,我也完全赞同!”
“那么对于第三点,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对于第三点,我个人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我只是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暂时先不考虑为好,因为对于多数同学来说,过早的考虑这个问题,会影响人的情绪,会给人带来压抑感······”。
——
高洁的想法不仅得到了常守志和黎晓华的赞同,也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赞同,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决定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并称其为“五七道路拓展计划”。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大家积极捐款,几天的工夫就筹集到了十多万元的资金,其中捐款最多的是常守志、高洁和黄龙彪,他们每人都捐了三万元。其实,黄龙彪在所有同学中是最有经济实力的,他完全可以捐的再多一些,但他却在同学中公开的说,自己是个商人,而商人在往出掏钱时,考虑问题的原则和出发点是能否有相应的回报,能否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从这一原则出发,他自己是不赞同这个所谓的“拓展计划”的,因为溪河湾地处偏僻山区,交通极不方便,在那里投资效益低,还可能无效益,甚至“血本无归”,而且那里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也不适合老年人养老,所以他无意在那里投入太多的资金,只是因为自己曾在那里插过队,才捐助了这三万元。
对于黄龙彪这种消极的态度,常守志、黎晓华和高洁都很不满意。常守志针对黄龙彪的这种态度还特别做了一个声明:在两、三年内,自己还将再捐款三到五万元。
九月二十日,插队三十周年之际,同学们带着筹集到的资金回到了溪河湾。黎晓华代表全体同学与溪河湾村委会主任王金玉签订了“‘五·七道路拓展计划’的实施协议”。在协议中,双方约定,同学们捐助的资金必须全部投入到“拓展计划”中去,用来发展溪河湾的集体经济。具体的实施步骤是:首先,筹建溪河湾林蛙养殖基地和人参栽培基地;经过三到五年的发展,再利用回收的资金和其它追加投资,建虹鳟鱼、甲鱼养殖基地以及驯鹿场;还要在适当的时机,在青年点原址建一座老年公寓。
签署协议后,黎晓华和常守志将资金交给了王金玉和村会计,当然,这些资金和后续追加资金,都将在知青代表黎晓华的监督下使用。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