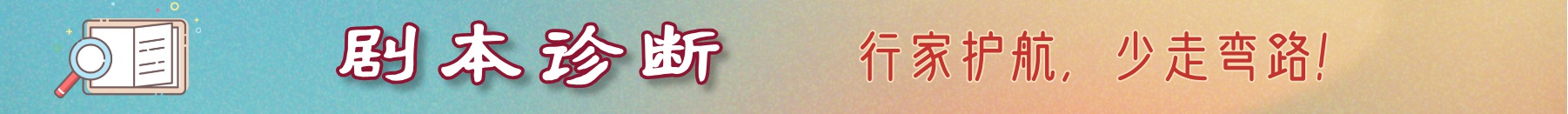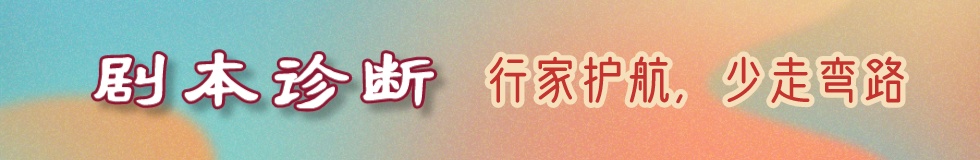1
任何一个大活人,置身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只要没做过一桩亏心事,即使半夜有人咚咚敲门,将门敲得山响,敲得整幢楼地动山摇,也不会紧张,更不会恐慌。
老景和英子作为相依为命的准古稀老人,不曾种下“亏心事”这个因,自然远离了“心不惊”这个果。
那天深夜11点半前后,老俩口所住的小区里,充斥着死一般的静寂,连忠于职守的路灯都打起了瞌睡,散发出来的光线半明不昧,软弱无力。老景和英子在踏踏实实的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这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状况,老景和英子不约而同地坐起来,竖起耳朵,让自己因年老而迟钝的听觉更加灵敏一些,以此判断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幻听,对于老景和英子来说,是常有的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家常便饭。退休后,老俩口的听力都有所下降,宅在家里,时常会听到异常的响动,好在如兔子尾巴一般短短秃秃,很快家里又恢复古井般的平静。有一次,英子问老景,不会是阎王爷前来探路吧?老景立马制止老伴胡思乱想,说,有生必有死,死亡没那么可怕,谁也躲不了,那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就像窗外绿油油的银杏叶子到了深秋,肯定要枯萎、落在地上一样。如此一番解释,英子的心里也就通透敞亮了,她认为自己同那些英年早逝者相比,多活了好多年,早就够本了,剩下的年头,全是净赚。
门铃,仍在响着,其声不绝如缕。应该不是幻听,肯定不是。
老景和英子的右手,同时伸向台灯的开关。行动一致的背后,是高度的默契。结婚四十多年来,老景和英子早已融为一体,她在家里咳嗽一声,他即使在别的地方也会跟着打喷嚏。用沉浸在爱河里的年轻人的说法,这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
打开台灯,浓重的夜色立马退潮,眼前亮如白昼。可以看出,老俩口的卧室里,装修和陈设颇为简单,老式家俱、电视和窗帘等,旧成了山寨版古董,时光的残酷无情由此可见一斑。挂在白墙上的全家福照片,三代同堂,明显区分出老中青少这几个层次。
英子问,是不是有人按错了门铃?
老俩口住在一楼,又是一单元,按错门铃的事,时有发生。不过,一般只限于大白天。
门铃仍在响着,持续不停,仿佛操作它的是一个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人。
对于英子的问题,老景没有回答,也不用回答。因为,响个不停的门铃声就是答案。
当时正值夏天,老景穿好单薄的衣裳,没费多少时间。他走到卧室门口,打开客厅的灯,回过头来,叮嘱道,你继续睡觉吧,我去看看是谁在按门铃?
英子柔声问道,是不是大奎回来啦?
大奎是老景和英子的大儿子,作为一个忙忙碌碌的生意人,他常年住在北京,离老俩口所住的江北雄州镇有一千多公里。除了逢年过节,他平时很少回来。“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对大奎来说,只是唱唱而已,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一个字:难。
老景站着没动,回答道,应该不是大奎,他要是回来的话,肯定先打电话,深更半夜搞突然袭击,给咱们这样一个反常的意外惊喜,似乎不是他做事的风格。
英子说,我这几天总是惦记着大奎,眼前总是晃动着他的影子,我还想到了他小时候白天爬高上低、磨破裤子,晚上尿床的事情。
老景真想对英子说,你这样的话,我早就听腻了。话到嘴边,被他咽了回去。穿过客厅,他走到防盗门那儿。门铃仍在不屈不挠地响着,那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刺耳。这是夜间,四周安静得如同死亡,任何一点细微的声音都会显得突兀。
拿起对讲门铃的话筒,在万籁寂静的夜间显得尖锐的声音彻底没了,老景问,谁啊?
对方的回答是,是我。
听到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老景不由得警觉地问,你是谁?
男子说,我是大奎的朋友。
老景又问,你是大奎的朋友?
男子肯定地说,对,是大奎让我来的。
老景听岔了,以为大奎是与按门铃的朋友一起回来的,心里滚过一阵激动,如同一个误入荒漠戈壁的人突然找到了干净的水源和食物。此外,他想到的是,英子念叨着的那句话,终于应验了,现在见到大奎,她不知有多高兴,有多激动。
按下对讲门铃上的那个键,老景听到了楼道单元门被打开的声音,他知道,大奎与朋友进来了。
大约过了两分钟,老景听到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消失在自家的防盗门外。他知道,大奎与朋友站在自家的门外了。
正准备开门的刹那间,老景出于警觉,透过猫眼,睁大一只昏花老眼朝外看。他要确认门外有一个人是大奎,大奎就站在门外。
唉,年纪大了,眼睛不太好使了。老景在心里长叹一声。猫眼让他捕捉到的除了一团漆黑,就是漆黑一团。楼道里的灯光很暗,属于暗无天日的暗,再加上猫眼不属于老年人,那么小的一个孔,哪能看得清楚呢?豹眼才好,不过,哪有人家在防盗门上安装那么大的豹眼呢?
老景迟疑着没开门。门外的人,显然等得不耐烦了,开始敲门,动作野蛮而粗暴。
活了大半辈子,老景虽然没做过任何亏心事,但是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猛烈敲门声,还是怕了。邻里好,赛金宝。他不怕别的,就怕对门的邻居、楼上楼下的邻居一宿好觉遭惊扰,被破坏。
老景刚硬着头皮打开防盗门,四个不速之客像泛滥的潮水一样涌进家里,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一个30出头,另外三个20出头,大奎并不在其中。
难道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老景愣住了,心里不由得格噔了一下,他努力控制着自己,尽量不朝坏处想。
老景问,你们是来找大奎的?
为首的小伙子过了而立之年,长得像梁朝伟,两只眼睛大而神,衬衫、西裤和轻便休闲鞋都是名牌,腕上的手表更是非同一般,让老景暗自吃惊,直觉告诉他,这个小伙子比大奎更有钱。
小伙子高声回答道,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是景大奎的父亲景从明吧?
老景说,我是景从明,大奎不住在我这儿。
那个身穿黑色T恤、手臂上纹着一条青龙的小伙子指着为首的小伙子,介绍说,这位是杨总,北京乐万家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戴着眼镜,一个剃着光头,他俩异口同声地附和道,对,这位就是咱们的杨总。
老景顿时明白了,杨总带着三个同伴,确实是来这里找大奎的。不过,他感到纳闷的是,大奎人在北京,杨总的公司也在北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江北雄州镇找大奎呢?
老景正要开口问个究竟,杨总等四人已经坐在那组沙发上了。沙发靠近柜式空调,眼镜男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摇控器,打开空调,显示的温度是22,凉气呼呼地冒了出来。
老景这才注意到,他们带着毛巾被和空调被,还拎着一只纸箱。显然是有备而来。
杨总,你们找大奎有什么事情?虽然老景的心里格噔了一下,但他却努力保持着平静,问上了这么一句。
杨总说,我们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子,累了倦了困了,天亮以后再说吧。
长发男说,老景,你去睡觉吧,有事等到天亮再说。
老景站着没动,他要从杨总等四人的面部表情上找到答案。结果,一无所获。
这时,英子穿好衣服,从卧室走到客厅里,走到老景的身旁,问杨总等四人,你们找大奎?大奎怎么啦?
杨总反问道,你是景大奎的母亲吧?
我是,请你们告诉我,大奎怎么啦?你们找大奎有什么事?
眼镜男要老景和英子回卧室睡觉,等到天亮以后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告诉我。
老景和英子站着没动,如同两棵经历无尽风雨的沧桑老树,期待着杨总等四人揭开谜面,露出谜底。
可是,杨总和衣倒在长沙发上,闭上了眼睛,很快发出了不轻不重的鼾声,不像是装的。光头男给他盖上了空调被,倚靠在单人沙发上,也是昏昏欲睡。T恤男和眼镜男更是睡意袭来如山倒。
见杨总等四人这个样子,老景和英子只得回到卧室。
躺在床上,老景和英子即使服用安眠药,也难以睡一个回笼觉。老俩口开始猜测,会不会是大奎抢了杨总的女人?
大奎和妻子祁春花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俩从小学读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一起通过招工进了江北雄州镇供销社上班,干了几年后一起辞职经商,从南京一起闯范到北京。这些年来,大奎当老板,祁春华做全职太太,两人恩爱如初,是公认的模范夫妻。大奎洁身自好,从未传出任何绯闻,“男人有钱就变坏”这个说法,在他身上是站不住脚的。
当英子说出“大奎是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祁春花的事情”时,老景叹了一口气,表示自己最怕大奎变心。他说,这个社会,诱惑实在太多了,那些老板,有情人和小蜜,叫做正常;没情人和小蜜,叫做不正常。
英子说,大奎是我从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敢断定,过去、现在和今后,他都不会上错床,他赚的钱再多,也不会花在别的女人身上。
老景说,但愿如此。
英子补充道,大奎一直与岳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有贱心也没贼啊。
老景没吭声,他在琢磨,杨总带人从北京风尘仆仆赶过来,究竟要干什么?他是怎样找到自己和英子的这个住处的?他为什么不改作白天上门?
不琢磨则罢,越琢磨,老景的头脑里越是乱成了一锅粥。问题好找,答案难寻,正当他同自己较劲的时候,英子突然坐了起来,低声问道,大奎会不会出事了?她的话里透出特别的紧张。
老景反问道,怎么可能呢?你别乌鸦嘴,好不好?
英子用双手紧紧捂住胸口,告诉老景,自己的心脏一直在咚咚乱跳。
我看你的心脏该送去检测维修了,老景的话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英子没再吭声,她知道老景生气了。为了让他尽快消气,英子拿起自己的枕头,先下床,然后躺到床尾那儿,一动不动,把自己变成木头人。
床头吵架床尾和。这些年来,英子的这一招,屡试不爽。果然,老景从床头爬到了床尾,伸出双手将她搂入怀里,告诉她,从杨总等四人进门后,自己的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请求她理解自己。
英子问,要不要现在打电话给大奎,问个究竟?
打也是白打,老景说。
他知道,大奎有个雷打不动习惯,手机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关机,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才关机。大奎举家去北京发展后,老景和英子轻易不会主动打电话给大奎。因为,大奎是个忙人,一旦分心,很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每隔两三个月,大奎都会打一次电话回来,不过,三言两语就打住,急着忙别的事情去了。
应老景的要求,英子跟着他从床尾挪到了床头。老俩口搂在一起,谁也没有出声,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声。
不知过了多久,老景和英子听到小区里有人送牛奶,专用车子的声音,奶瓶碰到一块的声音,前者没啥特点,后者清脆响亮,有着玻璃的质地。
牛奶送到,意味着黎明越来越近了。老景和英子开始搂着睡觉,虽然毫无睡意,但是,老俩口只能保持这样的睡姿。大半辈子就这么搂过来了,同在一张床上,背对背睡,换来的是很不习惯。
老景盯着天花板望了一会儿,要英子同自己一样,千万别朝坏的地方想,尽可能朝好的地方想。
英子以“嗯”作答。
老景强调指出,杨总是大奎的朋友,不是大奎的仇人,大老远地找到这儿来,应该是好事,不应该是坏事。
英子问,会不会是杨总打算在江北雄州镇搞什么新项目,先到我们这儿打探消息?
老景如释重负,说,但愿是这样。
英子附和道,但愿是这样。
老景说,咱俩快睡吧,不然,白天没精神。
2
早晨七点多钟,老景自然而然地醒了。“嘟哒……嘟哒……”“咕咕……咕咕……”友好地闯入他耳朵的,是两只鹧鸪的鸣叫声。那对可爱的鸟儿,藏身小区附近的小树林,却像是养在自家的阳台上,声音里透出无限的亲切,总是让他听不够。这些年来,老景每天早晨都是被一公一母的鹧鸪唤醒的,那对鹧鸪早已成为他体内的小闹钟。
老景睁开眼睛时,英子仍在熟睡之中。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老景在心里惊叫道,糟了。
这些年,老景早已习惯成自然,他每天早晨四点半前后就起床了,具体安排是,外出晨练一个小时;顺便买点儿早点;回家洗脸刷牙,冲把热水澡;煮稀饭,或者做豆浆;将家里保洁一遍。上述的事情全部做好,已是上午八点多,正好英子一觉睡到自然醒,老景与她一起共进早餐,然后开始上午平静安逸的生活。
杨总等四人深更半夜的突然闯入,扰乱了老景的早晨,看来,好端端的晨练只得取消了,这让他心不甘情不愿,却只能接受现实。
老景轻轻地松开英子,轻手轻脚地下床,趿上拖鞋,穿好衣服,走出卧室,顺手关上门。他的动作闷声不响,如同一个轻飘飘的纸人,朝着梦魇的方向走去。
站在客厅中央,老景苍老却不乏神采的目光朝杨总等四人扫去,只见他们东倒西歪睡在沙发上,睡姿难看得很。老景听到有个人发出的鼾声特别有意思,一声长,一声短,如咏叹调,更像是患上了某种分裂症。
鼾声是谁发出来的?老景出于好奇,走到沙发那儿,确认是杨总发出了鼾声,而且粗重的呼吸声与鼾声混在一起,也就是说,长的是羼合着呼吸声的鼾声,短的是羼合着鼾声的呼吸声。三个同伴只有呼吸声,没有鼾声,无意中巩固了杨总龙头老大的地位。
看来,杨总在睡梦中也要领导着三个同伴,作为老板,他就是这么霸气,这么强势。
长沙发被杨总占据了,虽然与单人床不可同日而语,但他睡得十分舒展,从鼾声和呼吸声的酣畅淋漓上可以看得出,他在睡梦中也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与其说T恤男、眼镜男和光头男在睡觉,不如说他们仨卷缩在一起,两个单人沙发靠在一起,也比不上杨总单独享用的长沙发。
柜式空调打得很低,客厅里凉爽得如同深秋。老景没有心疼电费,而是心疼酣睡未醒的杨总等四人,他担心他们大热天被吹出感冒来了。
稍稍调高空调的温度,老景注意到杨总等四人睡得太沉了,像死猪一样沉,即使拿鞭子赶他们,估计一时半会也不会醒。
老景还注意杨总的脸上有眼屎和口水的痕迹,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有钱的老板也是俗人一个,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本质区别啊。
透过客厅窗户,老景看到多个小区居民走动的身影,一天之计在于晨,睡了一宿好觉,该出门活动啦。于是,老景带上钱包和老人专用的手机,匆匆出门,步出小区,去体育场那儿的美食一条街。一路上,有面熟的居民笑着同他打招呼,他均给予热情的回应。
老景来到早点铺前,店老板笑着说,老景,早啊。
老景请店老板帮自己拿六份烧饼和油条。
店老板说,六份?老景,你过去都买两份啊。
老景强调说,对,是六份,家里来客人了。
店老板没再说什么,而是取出两只大号的塑料袋,替老景装好足够六个人吃的烧饼和油条。老景把钱付清,拎着烧饼和油条朝家里走。半道上,他突然记起自己忘了买咸鸭蛋,只得返回早点铺,对店老板说,给我拿六只咸鸭蛋。
好咧,店老板边说边忙碌。
掏出相应的零钱,店老板笑容可掬地收下,老景这才拎着烧饼、油条和咸鸭蛋回家。到家后,出乎意料的是,防盗门已被英子打开,她站在客厅中间,满脸怒容,目光像锥子一样盯着杨总等四人。
不仅如此,柜式空调被英子关上了,客厅的窗户被打开了,家里有了新鲜的空气,不过,温度却大幅度升高了。杨总、T恤男、光头男和眼镜男状若死猪,酣睡未醒。闷热的家居小环境,似乎影响不到他们的睡眠。
进屋后,老景顺手关上防盗门,朝英子笑了笑,然后走到餐厅,将烧饼、油条和咸鸭蛋放在餐桌上,招手示意她过来。
英子缓步来到餐厅。老景却去了客厅,关上窗户,重新打开空调,使之制冷。
见此情景,英子那张阴郁的脸像烤面包一样又干又硬,她把老景拉进厨房里,关上推拉门,问,你开什么空调,这不是白白地浪费电吗?
老景努力用最平和的语调与英子沟通。他说,电费能值多少钱?说一千道一万是大奎欠杨总600万,不是杨总欠大奎600万,咱们千万别让杨总他们在这里感觉到不舒服,你就别管了,家里有我张罗,你带好欢欢就行了。
英子又问,你买这么多烧饼和油条干什么?
老景说,来的都是客,杨总不是外人,他是大奎的朋友,我不招待他和三个同伴,难道要让他们四个人自掏腰包去外面吃早饭?
英子指责老景这是浪费,理由是,杨总他们一觉睡醒,估计到中午了,吃的是午饭,而不是早饭。
一语点醒梦中人,老景在心里埋怨自己老糊涂了。转而一想,他对英子说,烧饼留作咱们俩慢慢吃,吃不完的油条下油锅走一遭,炸得老一些,用来炒丝瓜,咸鸭蛋切开装盘,今天的午饭不就多了两道菜吗?
英子说,杨总和三个同伴或许不在我们家吃午饭呢。
我们老俩口吃,老景没好气地说了这么一句,他故意加重了“吃”这个字的音量,以此向英子提出抗议。
婚后几十年,老景和英子在消费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慷慨大方,一个抠门小气。家里来了客人,英子恨不得拿粗茶淡饭招待,老景却舍得端出好酒好菜,让客人吃饱喝足。在老景看来,天天待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英子却认为,攒钱比挣钱更重要,会攒钱的人才会过日子。老俩口为此一次次闹矛盾,老景索性将家里的财政大权收归己有。这样一来,英子看不惯老景的作派,只是提提意见,闹闹别扭。老景只要朝她吹胡子瞪眼睛,她当即噤若寒蝉,识趣地离开,免得针尖对麦芒,免得闹出不愉快。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之类的道理,英子当然明白,比谁都明白。
果然,英子不再为杨总等四人在家吃午饭的问题而纠结了。
当老景忙着煮绿豆稀饭时,英子带着欢欢出去散步了。
欢欢是贵宾犬,跟随英子有七八年了,是小区里一位居民送给她的。欢欢虽然八九岁了,却长不大,一直小巧玲珑。刚开始,老景反对英子养狗,认为狗很脏,会把家里弄得不成样子。可是,英子对欢欢爱不释手,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欢欢很干净,从不在家里排泄,而且越来越有灵气。每次见到英子和老景从外面回来,就会兴奋得直摇尾巴,在老俩口的面前撒着欢儿,跑来跑去。欢欢还认得别的家人,小奎一家三口、大奎一家三口回来一次,它就认得了,后面只要在家里听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就会兴奋地朝着防盗门跑去,迎接家人的到来。
过了半个小时,老景把绿豆稀饭煮好,端上了餐桌,英子牵着欢欢回来了,杨总等四人仍然熟睡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