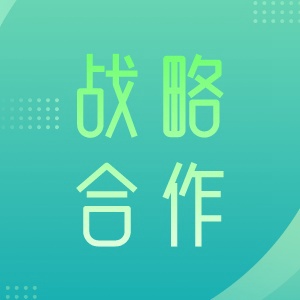权属:原创
字数:12777
阅读:8786
发表:2014/7/13
历史
小说
石破天惊之明建文皇帝在大理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梦回金陵――明建文皇帝在大理
作者简介:
马光宇,男,1965年出生,工程师。在《纺织学报》和《毛纺科技》学术期刊发表三篇论文。
马泽雷,男, 1974年12月生,云南省政法高等专科学校(现云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系毕业,现任洱源县民宗局副局长、洱源县七届政协委员。
引 子
佛经云:汝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2006年夏秋之交,笔者于洱源牛街串亲访友,闲聊之余,听说海西海风景区离之不远,便相约前往观赏。
海西海犹如一位羞涩的少女,藏身于龙门舍坝子北面的群山之中。一行人谈笑间己来到坝子尽处,但见一带山翼横亘眼前,岭上林木葱郁,长草丛生。众人穿技拂叶,觅路而行,一个时辰过后,攀上山坳,迤逦如带的海西海终于呈现于眼前。山不高而秀雅,湖不大而妩媚,轻烟薄雾之中,笼罩着万顷碧波,朵朵白云从水面轻盈荡起,在峰峦间飘浮游移,湖面尤如一片白玉,在浓雾中显得分外晶莹。身临其境,恍惚间置身于画中。波光鳞鳞的湖水清澈见底,微风徐来,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玉湖之北,一山巍然耸立。顶若佛钟,形态威严,脚下银瀑尽泻,绿荫森森,这便是的观音山,仿佛是一方神灵,守护着这片净土。
随行的亲友介绍,顺湖北眺,观音山腰有一石窟,谓之眠龙洞,是明朝建文皇帝遁逃大理的藏身之所。我听后颇为惊讶!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是西南地区乃至中南半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今随处可见的斑斑古迹,诉说着曾经的荣耀与辉煌。自元灭大理国,尤其明朝的改土归流之后,大理沦为远离中央朝廷的偏荒之地。靖难之役,明惠宗皇帝朱允炆的去向,众说纷纭,史学界至今亦无定论。难道是上天有意,山水有情,这里淳朴善良的白乡民众有缘,留住了当年匆匆的从亡脚步?这灵秀的山川,云霞幽深之处,果真承载着隐晦六百年的历史烟云,建文帝流连此间,僧衣麻鞋,度过凄楚的流亡岁月?
不知是好奇,还是来自心中隐约的召唤。笔者一扫适才湖光景色的眷恋之情,信步越过湖堤,走近观音山,探寻这云雾缭绕的神秘之所。
穿过村落,一条盘旋的山间小径呈现眼前,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时值雨后初晴,树枝草尖挂满水珠,花香馥郁,让人心悦气爽。山路不远,一石坊立于道中,清末高僧印心的楹联迎面而来:
洞天偶引困龙眠,消魂万里;
石乳难充真主渴,饮恨千秋。
过石坊,攀上高岫,已来到筇竹翠绕的古庵前,朱墙碧瓦中透着浑厚之气,古刹倚山面湖,极占形胜。走进山门,是一个雅致的院落,松柏苍郁,亭台潇洒,西面的大雄宝殿气势恢宏,妙相庄严,雅致的厢房分列南北,楣柱间漆落斑驳,写尽岁月沧桑,东面是几间黑黝黝的祭祀房。穿过南阁甬道,一条悬崖石径不远,便是眠龙洞,石窟嵌砌在观音山石崖上,洞内乳石嶙峋,神态各异。“洞深五丈阔十丈,岩嶂岑蔚,飞泉瀑布,清气袭人。”
洞中有“兰若寺常住碑”,记载兰若寺创建和几经劫难,以及建文皇帝逃难到眠龙洞隐居之史实。身临石窟,四周的建文石榻、石几……,触景生情,不由得让人心生伤感和无限遐思。出洞口几步,望湖楼伫立于石壁尽处,凭栏远望,碧海蓝天,海西海帆影点点,龙门舍坝子村落隐隐,一片生机,尽收眼底。松柏丛中,群鸟欢啼,此起彼伏,是欢迎远道的客人?石崖上的山花,扬起脖颈,在风中摇拽起舞,仿佛在欢叙着昔日的荣光。
在恋恋不舍中,告别了白乡洱源。身在归途,而心却留在了观音山上的幽幽古洞,留在了建文皇帝避难大理这段隐晦几个世纪的历史之中……。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下落成了千古之迷,民间以讹传讹,使之更显扑朔迷离。归来后,白乡盛传的建文帝佚事,当地历代凭吊诗词,时常萦绕心头,难以释怀。值此期间,见央视报导建文帝隐居湖南之传说云云。从而催生了写作的冲动,希望能拾掇这段荡人心弦的历史,敬献给读者。
然而自己弃笔从商,挤身于商贾之旅久矣,尔虞我诈中,淡去了书生的呆板,平添了几分势利与乖巧。今日抛却尘世的羁绊,回到久违的书房,这一隅的宁静,让浮躁的心绪趋于平淡,躬于笔耕,闭门沉思。仿佛自己是殉道者,为信仰的执着,踏上决绝之途。又俨然是一怪兽,置眼前利益于不顾,逃离熙熙攘攘的肆坊,遁入清冷的书斋,让如痴的梦呓,去拥抱贫穷。
这期间,书案上堆满苦心收集的地方史志和诗词,然而几经努力仍感到史料匮乏,心头无绪,一次次怅然止墨。笔下的主人公犹如夜空中悄然划过的流星,来去无声。这瞬间耀眼的光芒,却不知如何收藏,我知道岁月留痕,四十年的从亡之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来的,岂止是这斑斑点点,然而几经努力,面对的,仍是无语。
也许是冥冥中天意,牵动着这一丝因缘。2011年,笔者在一次访谈中,意外拾得明代大理三位作者的笔记小品佚书,如获至宝。几年来对这段史实的渴求,此刻间终于寻得一片水源。
佚书的三位作者李浩、张继白、李以恒。李浩生于元至正十四年,七岁时和沐英、太子朱标结为义姓兄弟。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后做太子侍读,后编入定远军,西平侯沐英的随身文官,平滇后授天威径镇抚使,德胜驿(今下关镇)千户长;张继白,大理太和人,好梅而善丹青,南中七子之一,与李浩结为姻亲;李以恒生于明正德二年,为李浩第五代孙。李浩、张继白是建文帝从亡云南的亲历者,佚书的诸多篇幅中有详实记载,与地方史志相印证。
至此,这段沉入历史烟尘,在扑朔迷离的时空里拉上了重重帐幔的疑案,跋涉于羊肠暗道,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主贴共十三章,未完待续)
大理龙儿2014.07.11
一
早晚来朝只有乌,空山谁忆御阶雏。
箧留遗命名先定,絏负从亡计不愚。
归去龙孙犹恋主,飞来燕子竟称孤。
弥茨云护残碑在,一剔莓苔字未糊。
——光绪《浪穹县志略》赵鲸
洪武25年四月,37岁的朱标太子突然去世,朱元璋震悼不已,伤心之极。百无聊赖中,把太子之死归咎于填燕尾湖建的新宫风水不好,年底亲撰祭光禄寺灶神文: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此时的太祖朱元璋已是65岁高龄,为防止皇室内讧,稳定大局,皇嗣的钦定己是迫在眉睫,依照接班的次序,朱标的嫡妻所生长子已在十年前去世。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的次子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能成功,但事实上洪武帝并没有考虑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朱允炆被立为皇嗣之日起,太祖对太孙的培养也即刻摆上日程,如同先前的太子施教,德才并重,请名儒授学,挑选才俊青年伴读。时常赐宴赋诗,谈古论今。选了一批有德行的端人正士,做太子宾客以谕德。并实习政事,批阅奏章,平决政事,学习做皇帝。这期间,建文帝“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自朱元璋登基,如同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任何人不可能与皇帝分享权力,兔死狗烹只是时间和方式而已。为确保已经拥有而时时被人觊觎的一切,解决皇权与相权、功臣宿将的矛盾,朱元璋对居功自傲、结党营私的勋臣武将分阶段解决,从洪武三年的廖永忠开始,之后胡惟庸、李善长、李文忠和徐达等相继被清除。朱标太子辞世,朱元璋执意再兴大狱,对资深望重的开国勋臣再一次清理,为皇孙将来登基扫清障碍。继而蓝玉、傅友德和冯胜等相继被诛。这样,到洪武二十八年,随朱元璋起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光了,真正侥幸保下性命来的大将只有西平侯沐英、信国公汤和、耿炳文和郭英四人。
朱元璋出生贫寒,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深刻体会与同情,在执政三十一年间,以民为本发展农业,减免赋税,提倡节俭,严于吏制,营建小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大明律》、《大诰》的颁布实施,废中书省及丞相,六部分理政务,以及御史台监察机构和锦衣卫特务机关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随着功臣武将的彻底清除,分封各地的藩王拥兵自重,其对将来皇权的影响也凸现出来。允炆问皇祖元璋:“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告诫允炆:“燕王不可不虑。”而又谕敕朱棣:“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为谁?……尓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安,以答天心,以副朕意。”
以上自相矛盾的临终交待,凸显了朱元璋内心的忧虑。“南倭北虏”是明朝开国以来国家安全的两大威胁,蒙元残部北遁沙漠,但仍称北元,保有政府机构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时有南下复国之图;东面沿海倭寇的频频袭扰,是明初国防的两大重点。北方需要重兵屯守,若直隶朝廷指挥,京都与前线遥距千里。把边境军权交付异姓诸将,恐生哗变,或尾大不掉,造成藩镇跋扈的历史覆辙。朱元璋索古冥思,权衡再三,决定建都于南方富庶之地,龙蹯虎踞的南京,而分封诸子藩王于北方据点。王位世袭的诸王有统兵军事之权,却没有土地,不许干预民政。从而在经济、军事和皇权三个方面,似乎完美地解决了。诸子分封至洪武十八年结束,太子朱标卒后洪武帝亦无意于变更,唯希望于诸王共扶皇孙,以期王朝江山永固,世代传承。尤其元勋武将的清洗,洪武二十六年之后,北方的军事防御,不得不交给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和四子燕王指挥。其中晋燕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这些藩属王国作为抗击蒙元南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支柱,诸王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法律上他们对境内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诸王手握兵权,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
为确保皇帝对藩封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罗列了诸多规章条款以约束藩王的行为,其如:新皇帝登基以后的三年内藩王不许赴京师,只能留守藩封。但如有“奸臣”当道,诸王须准备其兵力,听候新皇帝召遣,入京“清君侧”。 当驱逐了奸佞,完成护驾任务之后,他们仍应及时返回封地。
关于皇位的继承,洪武帝亦有严格规定,继承人必须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对《祖训录》有丝毫的改动。并且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都可以群起而攻之。
开国皇帝的这一想法是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建文皇帝即位后企图削夺藩封,这就使他与诸王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些藩王看来,新皇帝对自己王位特权的削夺,严重悖逆了《祖训录》。燕王由此为自己举兵对抗朝廷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也能短时期内召集到抗命的人马。
朱元璋如此费尽心机的缜密布局,死后却引起萧墙之祸,建文帝怕诸王过于强大而削藩,致使燕王起兵发动内战。燕王登基后的迁都和削藩,把朱元璋的建都和边防布局,打个稀烂。
朱元璋当过和尚,对天文、地理和卜筮之学独有情钟。在率师南征,路过婺州的兰溪时,胡大海推荐了一位精于天文星占的月庭和尚,颇受朱元璋器重,命他蓄发娶妻。在婺州为之建观星楼,学其星象观测和星占之术,乐此不疲。之后朱元璋养成夜观天象的习惯,在南京的宫庭中,时常露天夜坐,有时通宵达旦,观察星相变化。那时候普遍认知是天人感应,天上的星象世界与地上的众生一一对应。通过星象变化的观测和占卜术,不但能够预测战争成败,也可预知人事祸福。在刘基的文集中,朱元璋写的两封亲笔信,是星相占卜学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亦是两位伟人关于星相占卜应验的真实记录。
皇孙的担忧,朱元璋也有预料,纵横天下几十年,在腥风血雨中一路走来,他深知王权之路的险恶与叵测、 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学会了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在朱标太子去逝后,洪武帝未雨绸缪,在边陲大理为皇太孙允炆悄然布下了棋子。
大理素有佛都、妙香古国之称誉。佛教起缘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大理是佛教成长和早期传播之地。《白宫因由》一书中提到:释迦如来为法勇菩萨时,观音为常提菩萨时,在灵鹫山修行。法勇菩萨将无上菩提心宗在此尽传……。《滇黔纪游》载:“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初属罗刹。大理点苍古称灵鹫山,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曾于此讲《法华经》,又在洱海印证如来位。”晋代高僧法显的《佛国记》载:“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劈山入下,入处不容人,下处极远,有旁孔,迦叶金身在此中住。”元代郭松年《大理纪行》载:“此帮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
传说佛主释迦牟尼于灵鹫山香草坪(点苍中和峰山腰)开道场,一会讲经说法,一会拈花示众,听者皆默然,唯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于是,释迦牟尼以心印嘱咐迦叶为禅宗初祖。迦叶尊者欣然从命,抱金褴袈裟,携舍利子佛牙上鸡足山开华化道场,后来他入定华首门,肉身成佛,因此鸡足山成了享誉东南亚的佛教名山,朝佛圣地。
大理以“天开佛国,灵山古都”闻名于世,南诏建都史被颂为观音菩萨的指引和授予,蒙氏王族也附会成为印度阿育王的后裔。至大理国时期,段思平夺取政权,登基之日先拜天地,再拜观音:“吾国国号大理,本妙香福地,以佛立国。”因此大理国时期,佛教在当地更为推广,成为带普遍性的全民信仰,由于对佛教信仰的深笃,一些大理国王,禅去王位而皈依佛门为僧。白族封建主们的子弟,也多出家当和尚。
元至正年间,仙道张三丰慕名而来,在点苍玉皇阁道长陈玄子邀留下。仙居大理一年,这期间与大理名流多有交往,与段总管成忘年交。陈玄子将张三丰著的《上圣灵妙真经》、《大圣灵应真经》、《大圣灵通真经》配以丝竹仙乐,起名《三玄妙谈经》,由玉皇阁十八道士、段府十六乐工谈演于五华楼,听者如云。至此,灵妙大洞仙音开始流传于大理。
洪武十六年,经西平候沐英推荐,感通寺无极禅师率二十四弟子奉诏入京,觐献白驹一匹、茶花一盆, 太祖临軒纳之。忽然白马嘶鸣,茶花绽放○1,洪武帝大喜,当即赋诗一首,题名《僧居点苍》赐之:
巉岩突兀倚银汉,影浸榆河号点苍。
谷鸟迎僧春转巧,潭龙听法水生香。
峰头积雪炎天厚,岩上深松盛腊长。
问道也应如是住,好将钟鼓震蛮荒。
朱元璋赋毕,群臣唱和,当场集诗十二首,命人抄录赠予无极。钦赐无极禅师法名“法天”, 封为护国法师,授大理府僧都纲司都纲。三个月后,无极法师启程返滇, 太祖拟“无极趋水之易,步陆之艰,冲烟突雾,履雪凌霜”的路途艰辛之状,“敕翰林诸学士,僧箓司诸首僧以诗赠行。”并亲赋七律诗为之送行:
《赐僧无极归大理》
春游草木尽青青,觅法年来僧未宁。
石径云穿霞入树,江波烟气罩横汀。
作者简介:
马光宇,男,1965年出生,工程师。在《纺织学报》和《毛纺科技》学术期刊发表三篇论文。
马泽雷,男, 1974年12月生,云南省政法高等专科学校(现云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系毕业,现任洱源县民宗局副局长、洱源县七届政协委员。
引 子
佛经云:汝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2006年夏秋之交,笔者于洱源牛街串亲访友,闲聊之余,听说海西海风景区离之不远,便相约前往观赏。
海西海犹如一位羞涩的少女,藏身于龙门舍坝子北面的群山之中。一行人谈笑间己来到坝子尽处,但见一带山翼横亘眼前,岭上林木葱郁,长草丛生。众人穿技拂叶,觅路而行,一个时辰过后,攀上山坳,迤逦如带的海西海终于呈现于眼前。山不高而秀雅,湖不大而妩媚,轻烟薄雾之中,笼罩着万顷碧波,朵朵白云从水面轻盈荡起,在峰峦间飘浮游移,湖面尤如一片白玉,在浓雾中显得分外晶莹。身临其境,恍惚间置身于画中。波光鳞鳞的湖水清澈见底,微风徐来,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玉湖之北,一山巍然耸立。顶若佛钟,形态威严,脚下银瀑尽泻,绿荫森森,这便是的观音山,仿佛是一方神灵,守护着这片净土。
随行的亲友介绍,顺湖北眺,观音山腰有一石窟,谓之眠龙洞,是明朝建文皇帝遁逃大理的藏身之所。我听后颇为惊讶!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是西南地区乃至中南半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今随处可见的斑斑古迹,诉说着曾经的荣耀与辉煌。自元灭大理国,尤其明朝的改土归流之后,大理沦为远离中央朝廷的偏荒之地。靖难之役,明惠宗皇帝朱允炆的去向,众说纷纭,史学界至今亦无定论。难道是上天有意,山水有情,这里淳朴善良的白乡民众有缘,留住了当年匆匆的从亡脚步?这灵秀的山川,云霞幽深之处,果真承载着隐晦六百年的历史烟云,建文帝流连此间,僧衣麻鞋,度过凄楚的流亡岁月?
不知是好奇,还是来自心中隐约的召唤。笔者一扫适才湖光景色的眷恋之情,信步越过湖堤,走近观音山,探寻这云雾缭绕的神秘之所。
穿过村落,一条盘旋的山间小径呈现眼前,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时值雨后初晴,树枝草尖挂满水珠,花香馥郁,让人心悦气爽。山路不远,一石坊立于道中,清末高僧印心的楹联迎面而来:
洞天偶引困龙眠,消魂万里;
石乳难充真主渴,饮恨千秋。
过石坊,攀上高岫,已来到筇竹翠绕的古庵前,朱墙碧瓦中透着浑厚之气,古刹倚山面湖,极占形胜。走进山门,是一个雅致的院落,松柏苍郁,亭台潇洒,西面的大雄宝殿气势恢宏,妙相庄严,雅致的厢房分列南北,楣柱间漆落斑驳,写尽岁月沧桑,东面是几间黑黝黝的祭祀房。穿过南阁甬道,一条悬崖石径不远,便是眠龙洞,石窟嵌砌在观音山石崖上,洞内乳石嶙峋,神态各异。“洞深五丈阔十丈,岩嶂岑蔚,飞泉瀑布,清气袭人。”
洞中有“兰若寺常住碑”,记载兰若寺创建和几经劫难,以及建文皇帝逃难到眠龙洞隐居之史实。身临石窟,四周的建文石榻、石几……,触景生情,不由得让人心生伤感和无限遐思。出洞口几步,望湖楼伫立于石壁尽处,凭栏远望,碧海蓝天,海西海帆影点点,龙门舍坝子村落隐隐,一片生机,尽收眼底。松柏丛中,群鸟欢啼,此起彼伏,是欢迎远道的客人?石崖上的山花,扬起脖颈,在风中摇拽起舞,仿佛在欢叙着昔日的荣光。
在恋恋不舍中,告别了白乡洱源。身在归途,而心却留在了观音山上的幽幽古洞,留在了建文皇帝避难大理这段隐晦几个世纪的历史之中……。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下落成了千古之迷,民间以讹传讹,使之更显扑朔迷离。归来后,白乡盛传的建文帝佚事,当地历代凭吊诗词,时常萦绕心头,难以释怀。值此期间,见央视报导建文帝隐居湖南之传说云云。从而催生了写作的冲动,希望能拾掇这段荡人心弦的历史,敬献给读者。
然而自己弃笔从商,挤身于商贾之旅久矣,尔虞我诈中,淡去了书生的呆板,平添了几分势利与乖巧。今日抛却尘世的羁绊,回到久违的书房,这一隅的宁静,让浮躁的心绪趋于平淡,躬于笔耕,闭门沉思。仿佛自己是殉道者,为信仰的执着,踏上决绝之途。又俨然是一怪兽,置眼前利益于不顾,逃离熙熙攘攘的肆坊,遁入清冷的书斋,让如痴的梦呓,去拥抱贫穷。
这期间,书案上堆满苦心收集的地方史志和诗词,然而几经努力仍感到史料匮乏,心头无绪,一次次怅然止墨。笔下的主人公犹如夜空中悄然划过的流星,来去无声。这瞬间耀眼的光芒,却不知如何收藏,我知道岁月留痕,四十年的从亡之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来的,岂止是这斑斑点点,然而几经努力,面对的,仍是无语。
也许是冥冥中天意,牵动着这一丝因缘。2011年,笔者在一次访谈中,意外拾得明代大理三位作者的笔记小品佚书,如获至宝。几年来对这段史实的渴求,此刻间终于寻得一片水源。
佚书的三位作者李浩、张继白、李以恒。李浩生于元至正十四年,七岁时和沐英、太子朱标结为义姓兄弟。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后做太子侍读,后编入定远军,西平侯沐英的随身文官,平滇后授天威径镇抚使,德胜驿(今下关镇)千户长;张继白,大理太和人,好梅而善丹青,南中七子之一,与李浩结为姻亲;李以恒生于明正德二年,为李浩第五代孙。李浩、张继白是建文帝从亡云南的亲历者,佚书的诸多篇幅中有详实记载,与地方史志相印证。
至此,这段沉入历史烟尘,在扑朔迷离的时空里拉上了重重帐幔的疑案,跋涉于羊肠暗道,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主贴共十三章,未完待续)
大理龙儿2014.07.11
一
早晚来朝只有乌,空山谁忆御阶雏。
箧留遗命名先定,絏负从亡计不愚。
归去龙孙犹恋主,飞来燕子竟称孤。
弥茨云护残碑在,一剔莓苔字未糊。
——光绪《浪穹县志略》赵鲸
洪武25年四月,37岁的朱标太子突然去世,朱元璋震悼不已,伤心之极。百无聊赖中,把太子之死归咎于填燕尾湖建的新宫风水不好,年底亲撰祭光禄寺灶神文: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此时的太祖朱元璋已是65岁高龄,为防止皇室内讧,稳定大局,皇嗣的钦定己是迫在眉睫,依照接班的次序,朱标的嫡妻所生长子已在十年前去世。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的次子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能成功,但事实上洪武帝并没有考虑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朱允炆被立为皇嗣之日起,太祖对太孙的培养也即刻摆上日程,如同先前的太子施教,德才并重,请名儒授学,挑选才俊青年伴读。时常赐宴赋诗,谈古论今。选了一批有德行的端人正士,做太子宾客以谕德。并实习政事,批阅奏章,平决政事,学习做皇帝。这期间,建文帝“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自朱元璋登基,如同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任何人不可能与皇帝分享权力,兔死狗烹只是时间和方式而已。为确保已经拥有而时时被人觊觎的一切,解决皇权与相权、功臣宿将的矛盾,朱元璋对居功自傲、结党营私的勋臣武将分阶段解决,从洪武三年的廖永忠开始,之后胡惟庸、李善长、李文忠和徐达等相继被清除。朱标太子辞世,朱元璋执意再兴大狱,对资深望重的开国勋臣再一次清理,为皇孙将来登基扫清障碍。继而蓝玉、傅友德和冯胜等相继被诛。这样,到洪武二十八年,随朱元璋起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光了,真正侥幸保下性命来的大将只有西平侯沐英、信国公汤和、耿炳文和郭英四人。
朱元璋出生贫寒,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深刻体会与同情,在执政三十一年间,以民为本发展农业,减免赋税,提倡节俭,严于吏制,营建小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大明律》、《大诰》的颁布实施,废中书省及丞相,六部分理政务,以及御史台监察机构和锦衣卫特务机关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随着功臣武将的彻底清除,分封各地的藩王拥兵自重,其对将来皇权的影响也凸现出来。允炆问皇祖元璋:“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告诫允炆:“燕王不可不虑。”而又谕敕朱棣:“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为谁?……尓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安,以答天心,以副朕意。”
以上自相矛盾的临终交待,凸显了朱元璋内心的忧虑。“南倭北虏”是明朝开国以来国家安全的两大威胁,蒙元残部北遁沙漠,但仍称北元,保有政府机构和强大的军事实力,时有南下复国之图;东面沿海倭寇的频频袭扰,是明初国防的两大重点。北方需要重兵屯守,若直隶朝廷指挥,京都与前线遥距千里。把边境军权交付异姓诸将,恐生哗变,或尾大不掉,造成藩镇跋扈的历史覆辙。朱元璋索古冥思,权衡再三,决定建都于南方富庶之地,龙蹯虎踞的南京,而分封诸子藩王于北方据点。王位世袭的诸王有统兵军事之权,却没有土地,不许干预民政。从而在经济、军事和皇权三个方面,似乎完美地解决了。诸子分封至洪武十八年结束,太子朱标卒后洪武帝亦无意于变更,唯希望于诸王共扶皇孙,以期王朝江山永固,世代传承。尤其元勋武将的清洗,洪武二十六年之后,北方的军事防御,不得不交给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和四子燕王指挥。其中晋燕二王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这些藩属王国作为抗击蒙元南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支柱,诸王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法律上他们对境内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诸王手握兵权,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
为确保皇帝对藩封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罗列了诸多规章条款以约束藩王的行为,其如:新皇帝登基以后的三年内藩王不许赴京师,只能留守藩封。但如有“奸臣”当道,诸王须准备其兵力,听候新皇帝召遣,入京“清君侧”。 当驱逐了奸佞,完成护驾任务之后,他们仍应及时返回封地。
关于皇位的继承,洪武帝亦有严格规定,继承人必须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对《祖训录》有丝毫的改动。并且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都可以群起而攻之。
开国皇帝的这一想法是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建文皇帝即位后企图削夺藩封,这就使他与诸王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些藩王看来,新皇帝对自己王位特权的削夺,严重悖逆了《祖训录》。燕王由此为自己举兵对抗朝廷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也能短时期内召集到抗命的人马。
朱元璋如此费尽心机的缜密布局,死后却引起萧墙之祸,建文帝怕诸王过于强大而削藩,致使燕王起兵发动内战。燕王登基后的迁都和削藩,把朱元璋的建都和边防布局,打个稀烂。
朱元璋当过和尚,对天文、地理和卜筮之学独有情钟。在率师南征,路过婺州的兰溪时,胡大海推荐了一位精于天文星占的月庭和尚,颇受朱元璋器重,命他蓄发娶妻。在婺州为之建观星楼,学其星象观测和星占之术,乐此不疲。之后朱元璋养成夜观天象的习惯,在南京的宫庭中,时常露天夜坐,有时通宵达旦,观察星相变化。那时候普遍认知是天人感应,天上的星象世界与地上的众生一一对应。通过星象变化的观测和占卜术,不但能够预测战争成败,也可预知人事祸福。在刘基的文集中,朱元璋写的两封亲笔信,是星相占卜学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亦是两位伟人关于星相占卜应验的真实记录。
皇孙的担忧,朱元璋也有预料,纵横天下几十年,在腥风血雨中一路走来,他深知王权之路的险恶与叵测、 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学会了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在朱标太子去逝后,洪武帝未雨绸缪,在边陲大理为皇太孙允炆悄然布下了棋子。
大理素有佛都、妙香古国之称誉。佛教起缘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大理是佛教成长和早期传播之地。《白宫因由》一书中提到:释迦如来为法勇菩萨时,观音为常提菩萨时,在灵鹫山修行。法勇菩萨将无上菩提心宗在此尽传……。《滇黔纪游》载:“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初属罗刹。大理点苍古称灵鹫山,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曾于此讲《法华经》,又在洱海印证如来位。”晋代高僧法显的《佛国记》载:“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劈山入下,入处不容人,下处极远,有旁孔,迦叶金身在此中住。”元代郭松年《大理纪行》载:“此帮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
传说佛主释迦牟尼于灵鹫山香草坪(点苍中和峰山腰)开道场,一会讲经说法,一会拈花示众,听者皆默然,唯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于是,释迦牟尼以心印嘱咐迦叶为禅宗初祖。迦叶尊者欣然从命,抱金褴袈裟,携舍利子佛牙上鸡足山开华化道场,后来他入定华首门,肉身成佛,因此鸡足山成了享誉东南亚的佛教名山,朝佛圣地。
大理以“天开佛国,灵山古都”闻名于世,南诏建都史被颂为观音菩萨的指引和授予,蒙氏王族也附会成为印度阿育王的后裔。至大理国时期,段思平夺取政权,登基之日先拜天地,再拜观音:“吾国国号大理,本妙香福地,以佛立国。”因此大理国时期,佛教在当地更为推广,成为带普遍性的全民信仰,由于对佛教信仰的深笃,一些大理国王,禅去王位而皈依佛门为僧。白族封建主们的子弟,也多出家当和尚。
元至正年间,仙道张三丰慕名而来,在点苍玉皇阁道长陈玄子邀留下。仙居大理一年,这期间与大理名流多有交往,与段总管成忘年交。陈玄子将张三丰著的《上圣灵妙真经》、《大圣灵应真经》、《大圣灵通真经》配以丝竹仙乐,起名《三玄妙谈经》,由玉皇阁十八道士、段府十六乐工谈演于五华楼,听者如云。至此,灵妙大洞仙音开始流传于大理。
洪武十六年,经西平候沐英推荐,感通寺无极禅师率二十四弟子奉诏入京,觐献白驹一匹、茶花一盆, 太祖临軒纳之。忽然白马嘶鸣,茶花绽放○1,洪武帝大喜,当即赋诗一首,题名《僧居点苍》赐之:
巉岩突兀倚银汉,影浸榆河号点苍。
谷鸟迎僧春转巧,潭龙听法水生香。
峰头积雪炎天厚,岩上深松盛腊长。
问道也应如是住,好将钟鼓震蛮荒。
朱元璋赋毕,群臣唱和,当场集诗十二首,命人抄录赠予无极。钦赐无极禅师法名“法天”, 封为护国法师,授大理府僧都纲司都纲。三个月后,无极法师启程返滇, 太祖拟“无极趋水之易,步陆之艰,冲烟突雾,履雪凌霜”的路途艰辛之状,“敕翰林诸学士,僧箓司诸首僧以诗赠行。”并亲赋七律诗为之送行:
《赐僧无极归大理》
春游草木尽青青,觅法年来僧未宁。
石径云穿霞入树,江波烟气罩横汀。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