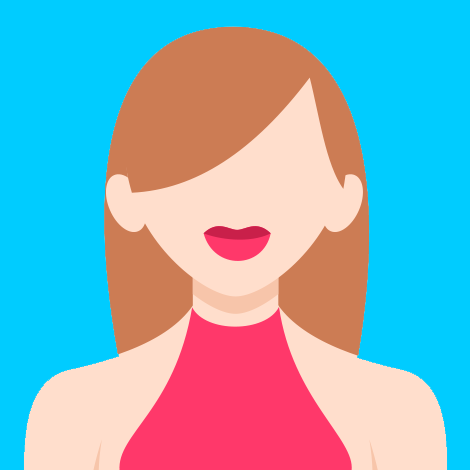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普通授权
字数:104301
阅读:12578
发表:2017/10/30
奇幻
小说
撰纸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门雏犹犹豫豫地走向他,缓慢地抓住背包的带子试图拿下来,动作的速度是给阿莫士反抗的机会,但是阿莫士不做任何抵抗。这时门雏注意到,他已经高出自己一个头了。门雏拿走包打开看了一眼,阿莫士极其神经地盯着他的脸,屋内强烈的灯光照得人脸走形,尽管身后的黑暗张牙舞爪,也不及这人脸狰狞。
“另一个人杀的他,我只是将他带回来了。”他的语气不坚决,说实话那时候看到的和塔图长得一样的凶手,他怀疑是不是幻觉。
“我明白,毕竟他从离开时就被人暗害过。所以你没必要这么害怕。”
门雏的这句话提醒了阿莫士。他在害怕吗?是怕经过他手的血淋淋的头颅吗?还是怕神秘的俯视者只见他的行为不见他的内心而对他妄加定罪再施以惩罚?
“你把灯换成小的,有些刺眼。”他说。
到了白天的时候,门雏在他们住的山上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和阿莫士一起把塔图的头颅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阿莫士的精神状态都很混乱,一直躺在家里做着噩梦,一天到晚什么工作也不干。
“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说什么安慰的话,因为我知道这是无用的行为。”门雏坐在阿莫士床边说,他刚把他从噩梦中摇醒。看着阿莫士疲惫的脸色,一段距离在他心中产生,痛在当事人身上,其他人希望代之承担是一种奢望,其他人的任何话语也解决不了任何皮毛之痒。
“我的脑子里总在想这件事,想起一些琐碎的回忆。”
“那你就回忆吧,不要回避,这是一种悼念。”他看着阿莫士即将入睡,说到一半的话流动成喃喃低语,“就如同他还陪伴着你一样,每天,很蹊跷,是他存在过是一场梦,还是他的离开是一场梦,又或者你的存在或者是连我的存在都是假的。”他说着这些,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阿莫士假装已经沉睡,他把这看成是敷衍,他不相信不幸的心情可以侃侃而谈,如果可以,那这种不幸的心情只是一种旁观态度。这种态度他不想在门雏身上有感。
阿莫士在黑夜的噩梦后醒来,尔后想起了一些几乎遗忘的童年记忆。小时候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定期给几座豪宅的园林做修剪,因为其中一家的砖瓦被风吹下来而砸到胳膊,还因此打了石膏,所以那一家给他们的补贴比较好。那家住的宅子在街道边缘的靠山处,外墙是深红与黄白相间的,有三层,房正面有一排落地玻璃窗,映出庭院内氤氲的景色。其他的庭院都是用铁栏杆围起来的,他们的庭院却被高高的石墙挡住,从外面可以隐约瞥见院内茂密的植被,活像一处秘密的监狱。他在父亲工作的时候常常跟随着,最在意的就是这所宅子。这里住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是那天不小心将砖瓦砸到他父亲的胆小鬼,名叫塔图,他面容娇好,像童话中的王子。从第一次见他,他就对他投注羡慕的眼光,直到他们混成朋友,他也相信塔图从未发现他的这种目光,这种目光和所有见过塔图的人的目光一样,泛滥到像是垃圾堆里的碎玻璃片折回来的光线。塔图对他像兄弟一样亲近,却从来不敢说砸到他父亲砖瓦的风就是他自己。宅子的主人是一个表情阴沉的老人,那里好像只有塔图和这个老人两个人住着。有一天老人领回来一个和塔图长得很像的小孩,说要带他们去旅行,那天他正好被父亲留在他们家,老人走得急急匆匆,塔图执意要带着他一起,后来他们两个人都被丢在了坞山上。他们在山下飘荡了几天,门雏就是在那个时候收留的他们。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日里见到的和塔图长得一样的人,大概就是当年老人领回来的那个小孩。可怕,那个人一直在他的记忆里,可是他一直都想不起他,这之间是何种鲜活的裂隙,以至于他大费周折地将怀疑引到自己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莫士渐渐不再被噩梦缠身。他开始走出户外,只是每天都跑过去徘徊在那小土丘旁,从秋天到下一个秋天,呼吸着树上的酸果子腐烂的味道,拥在落叶堆里取暖,将新鲜的野花采下来摆在周围,听着寒蝉鸣泣的起伏,把这四个场景不厌其烦地循环着。有一段时间他将小土丘周围用带刺的铁网围出一个区域,这一无意义的行为好像可以从他的手中变出一个时空,在这个时空中塔图仍然在同他对话。可是不久后他在铁网上发现了豁口,想象中的那个时空碎裂了,他没有考虑或许是什么生物弄破的,只觉得是塔图想要回避他了,就将铁网拆卸了。这片地方被他整得辛苦,连近处的树木也落下疲惫的光泽。门雏建议将塔图的头颅移出来埋到他们房子的地下。从那之后,阿莫士走出了阴影,下山去工作,极少再回山上住了。
对于这同一件事,远处还有一个人经历着折磨。那天鸣火和阿枚走散后先回到了家中,却没有看见塔图,不知为何意识中闪现出了塔图不会再回来的概念。他外出寻找了好几天,丝毫没有见到塔图的踪影,强烈的失落感牵涉出了一种直觉,塔图突然的消失或许是已经死了。他不想去揣测这件事与阿枚有关,但在阿枚一反常态的表现中他难以不去联系。
他不辞而别,去了以前和塔图一起待过的那个小洋楼里隐居起来。在这里的一段时间他经历了人生中不曾有过的荒凉,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活着的实感,并不是因为时间的久远,那时候思维能力的不健全让印象不真不假,好像是作为人偶一样活在混沌与没有希望的时间里。阿枚在他的生命中是代替母亲的存在,她对他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他想当然的任性也不会被她抱怨。他从很小就非常依赖阿枚,然而无论多深爱的亲人,在久久被麻烦折磨后也会精疲力竭,现在这种无条件的爱幻灭了,塔图也没有再出现过,他放眼望去找不到生存的动机。绝望不能灭绝他的生命,他还得为了维持躯体的动力去行动,却丝毫没有行动的欲望。多少个从午后醒来的瞬间,他都感觉呼吸像铅块压得他陷进自己的身后,窗户在强光照射下映出几根弯曲树枝的黑色叠影,除此之外是一片白光,什么也看不到,安静得仿佛万物将死。
这是个安静惬意且又敞亮的空间。他看着它,惊觉自己从黑暗中出来,却总是躲在避光的阴影处。尚未闭合的明暗格差不断移动着,这种移动带来一种摇摆不定的痛苦,仿佛这个空间开始向他言说他不在此处时的此处。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已经创作不出什么音乐了,在这之前注意力被分散,他沉溺于改造自己的身体,开发更多可能的感觉。贝壳长入他的皮肤是个偶然,不过这是大自然给他的一个有效提示,他尝试与自然界更多与人体不融合的物质接合,使自己的身体在感觉上从世界那里获取更接近实质的内在。他尝试主动将石头接在自己的骨骼中,本来是抱着或死的心态,可是身体只是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比贝壳长入他的皮肤那次反应更强烈,他没日没夜地痛苦,却死不了。然而与此同时在他的身体里也的确产生了新的感觉,在他的理解里,是非任何人类拥有的感觉,是极大的不可思议,比颠覆重力还令他狂喜。但在人类的感觉中,输入的感觉有相对输出的途径。当然他向外获得的感觉找不到输出的途径,这导致感觉的诞生有一种欲望被遏制的错觉,一种不完整的破碎感,使他这种爱蒙上了一层痛苦的割裂面。当他体会到的意象恰到好处时,也无法将这种内心的澎湃用适当的方法宣泄,它积压起来,变成了一种不安。可能他还不知如何成全这种激情,在邂逅了这种惊艳之后,尤其不知如何去化解这种一厢情愿,使得欲望倍感迷惘,无法完全对等,留下了一部分空茫。要做好准备,投入一切回想和曾有的体验,才能对得起他感之所及的每个细节。他叹气,吮吸着那不存在的香,这种激情像看到闪电从身边经过……
于是他痛苦着却也无法自拔地沉溺着,为了破解那种割裂感又反复寻找新的方式。他参透自己的局限,打算从每个角落攻破,灭绝自己的局限来提升自己。他停不下来这个过程,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因为局限会反杀,要求他与它同行——局限本身就是生命,他将会遭到生命的离弃。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损失,他不是外在的生命,而是超越生命的能力。当然这能力是以局限作为磨练和台阶而产生的。
或微妙或浩瀚,他都能从感觉中提炼愉悦,痛苦只是副作用。他燃烧着自己的中心,生命在他的吞噬本能中被消耗,变得病态。然而他将新的知觉带来的精神兴奋连同这躯体的痛苦一起无私地送给了创作,无耻地把它们用做素材。他创作出的东西不再只是音乐,还有音乐的非旋律形式,音乐的题材,甚至音乐的感受途径。然而这些都不够,还不够!他的边缘神经变得异常敏感,从光的潜伏期最初的一刻就能察觉,它们在皮肤中逗留一阵才能变成现实的感应,远比声音的潜伏期长。对它们的感觉交织起来分分合合击碎他的征服欲,他新的作品征服了他的痛苦,也淡化了他的思念。
他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自己,他还无法成为他所要成为的,过去的与未完成的、与正在进行着的相颉颃,他是一个实际上的怪物。他的怪物不是形态,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他可以存于两处,怪物的概念将他拯救。这是一个变量,它为确定的时刻不断到来又逝去,在空间内构不成“在场”,在逻辑上却可以构成多个“在场”,所以在这个概念中他具有多种属性。
一个冲动的人总是容易错误估算,有一次他甚至长途跋涉,去活火山将岩浆注入到血液中,就是这次的实验使他久病不愈,没有痛苦也没有开发出新的感觉,只是整日整夜地疲惫不堪。他只能勉强维持自理,很久都不出门一次,偶尔摘些院子里的野菜充饥。等他注意到的时候,周围人都已经搬走了。
第三章
第十七节. 旧所
在这几年里时咲主持投资,将拆迁活动主要转移到坞山周边,将山顶上的信号屏蔽,以及山下的污染工厂处理掉,导致那片区域变得特别落后。他一直很活跃,只是最近总是待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有时塔仑会推开房间的门看他一眼,看见他冷清的肩膀和衰老的背影,以及一如既往地对于入侵者无所反应。时咲自己预感着一种死亡的迫近,虽然只有隐隐约约的身体不适,虽然这不适也只是困乏的累加也说不定,但这困乏的毒效开花结果,他的精神和智力都在往临界靠拢,他快要帮不上塔仑什么了。他躺在床上,浑浊的眼睛半开半阖,虚弱刻意在兴奋,各种场景迫切地闪入他的视象。所有的闪现都是回忆,没有任何新的想法,他久久张望着记忆的逆行回归,渴望以此来磐涅重生,气力的疲惫让他的思维和意志都变得消极。但即使他的气息微弱到将要散尽,也无法释放他体内蕴藏的全部情绪,一些遗憾郁结在某处,他终日的叹息似乎是想要强行宣泄出那些无法散尽的气氛。时咲看起来愚笨又惹人烦,塔仑怀疑他是打算将氧气生生吐完,他过去的决策与冷静绝对被他自己宣泄得干干净净了。他的萎靡发展地自然而然也很突然,只是从开春以来而已。
现在寻找鸣火的人不只有阿莫士,塔仑也在找,他走过的足迹和打问过的人也有一定数量了。这年塔仑正好长到和塔图死去时差不多大的年龄,他戴着一副厚重的圆眼镜,头上顶着一顶崭新的圆顶帽,盖住他那修剪得乱七八糟的亚麻色头发,外套的色泽滑落得极为凄惨,整个人的打扮滑稽得活像一个小老头。他开了辆旧式的小轿车,每次出门前时咲都会提醒他若是见了那些同样在寻找鸣火的人就先躲起来,免得尴尬。这天他将车开到一个旧城区背后的小村落,村落前还有一条大河和荒地隔开,此处城市败落的原因也许是二十几年前这里修筑起一层厚厚的围墙,墙垣高度足有六十米,将这片城区和其他城市隔离开来。墙上刻着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低处一些墙砖已经脱落了,显示出呼吸过的痕迹。他开车绕了很远的路程才来到这里,还有一些穷苦人守着这片荒地不走。他将车在一排平房前停下来,那些平房的房顶上铺着很干净的苇草,院子周圈用鹅卵石堆砌的矮墙圈起来,门前有个蹲坐着的老妇人,正在阳光下摘菜。
“请问您在附近有见到过这个人吗?”塔仑走上前,很有教养地脱下圆帽夹在腋下并双手握着照片递给老妇人。
老妇人接过照片,看了一下不能辨认,又一手拿着照片将它从眼前推开一段距离。“有见过,不过,也很久了。之前我们住在这河对岸,他住在一栋构造奇特的小洋楼里,偶尔见他走出院墙一副病弱的样子,却总是一个人,所以还比较有印象。”
“那栋房子现在还在吗?”
“唉,我也不清楚呀,这几年都没过去看过,这条大河的右岸经常泛滥,所以对岸的人几乎都搬到了这边,你过了河之后沿着被冲刷的砾石滩向西走去,直到看见有一排排高大的栎树的地方你再寻找好了。”
“好,我去找找看,谢谢您了。”
连接河对岸的只有一座简陋的木架桥,原来石桥被冲毁的痕迹还在,看来这木桥是临时搭建的。塔仑只能把车子留在这边,自己走过去,过桥之后,他找到了长满高大栎树的地方,树叶和掉落的树皮有被扫成堆的痕迹,这里应该还有人来过才对。树是沿着围墙长的,墙上也落满了叶子,在墙的拐角处仔细看时才可以发现掩藏在叶堆中间的一扇门,门是砖红色的木板凌乱拼凑的,但他随即意识到这扇门是类似于装饰品的存在,它与墙体并没有接合的地方。他将那周围墙上爬满的叶子拨开,发现了嵌在石墙上的玻璃,是一扇窗子,窗子内侧被杂物堵着,应该是底层储物用的。于是他仰起头来向上看,才看见有一道伸在半空中的楼梯,梯级很厚,在楼梯底部尽头的侧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铁门,有一定高度,在他所在的高度无法直接够到,估计进出的大门是在围墙的另一侧,而楼梯的顶部尽头在叶子的掩映下拐向了墙对面。房子的设计没有墙外敞开的入口,于是他从墙上翻了过去,在落地时踩到了支离破碎的触感,同时比预想的落地距离短。他踩在了高高堆起的叶片上,这些叶子的干枯程度像是往年残留下来的。它们很久没有被清理过了,躲在墙的阴凉处,散发着不祥的腐朽。
“另一个人杀的他,我只是将他带回来了。”他的语气不坚决,说实话那时候看到的和塔图长得一样的凶手,他怀疑是不是幻觉。
“我明白,毕竟他从离开时就被人暗害过。所以你没必要这么害怕。”
门雏的这句话提醒了阿莫士。他在害怕吗?是怕经过他手的血淋淋的头颅吗?还是怕神秘的俯视者只见他的行为不见他的内心而对他妄加定罪再施以惩罚?
“你把灯换成小的,有些刺眼。”他说。
到了白天的时候,门雏在他们住的山上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和阿莫士一起把塔图的头颅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阿莫士的精神状态都很混乱,一直躺在家里做着噩梦,一天到晚什么工作也不干。
“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说什么安慰的话,因为我知道这是无用的行为。”门雏坐在阿莫士床边说,他刚把他从噩梦中摇醒。看着阿莫士疲惫的脸色,一段距离在他心中产生,痛在当事人身上,其他人希望代之承担是一种奢望,其他人的任何话语也解决不了任何皮毛之痒。
“我的脑子里总在想这件事,想起一些琐碎的回忆。”
“那你就回忆吧,不要回避,这是一种悼念。”他看着阿莫士即将入睡,说到一半的话流动成喃喃低语,“就如同他还陪伴着你一样,每天,很蹊跷,是他存在过是一场梦,还是他的离开是一场梦,又或者你的存在或者是连我的存在都是假的。”他说着这些,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阿莫士假装已经沉睡,他把这看成是敷衍,他不相信不幸的心情可以侃侃而谈,如果可以,那这种不幸的心情只是一种旁观态度。这种态度他不想在门雏身上有感。
阿莫士在黑夜的噩梦后醒来,尔后想起了一些几乎遗忘的童年记忆。小时候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定期给几座豪宅的园林做修剪,因为其中一家的砖瓦被风吹下来而砸到胳膊,还因此打了石膏,所以那一家给他们的补贴比较好。那家住的宅子在街道边缘的靠山处,外墙是深红与黄白相间的,有三层,房正面有一排落地玻璃窗,映出庭院内氤氲的景色。其他的庭院都是用铁栏杆围起来的,他们的庭院却被高高的石墙挡住,从外面可以隐约瞥见院内茂密的植被,活像一处秘密的监狱。他在父亲工作的时候常常跟随着,最在意的就是这所宅子。这里住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是那天不小心将砖瓦砸到他父亲的胆小鬼,名叫塔图,他面容娇好,像童话中的王子。从第一次见他,他就对他投注羡慕的眼光,直到他们混成朋友,他也相信塔图从未发现他的这种目光,这种目光和所有见过塔图的人的目光一样,泛滥到像是垃圾堆里的碎玻璃片折回来的光线。塔图对他像兄弟一样亲近,却从来不敢说砸到他父亲砖瓦的风就是他自己。宅子的主人是一个表情阴沉的老人,那里好像只有塔图和这个老人两个人住着。有一天老人领回来一个和塔图长得很像的小孩,说要带他们去旅行,那天他正好被父亲留在他们家,老人走得急急匆匆,塔图执意要带着他一起,后来他们两个人都被丢在了坞山上。他们在山下飘荡了几天,门雏就是在那个时候收留的他们。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日里见到的和塔图长得一样的人,大概就是当年老人领回来的那个小孩。可怕,那个人一直在他的记忆里,可是他一直都想不起他,这之间是何种鲜活的裂隙,以至于他大费周折地将怀疑引到自己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莫士渐渐不再被噩梦缠身。他开始走出户外,只是每天都跑过去徘徊在那小土丘旁,从秋天到下一个秋天,呼吸着树上的酸果子腐烂的味道,拥在落叶堆里取暖,将新鲜的野花采下来摆在周围,听着寒蝉鸣泣的起伏,把这四个场景不厌其烦地循环着。有一段时间他将小土丘周围用带刺的铁网围出一个区域,这一无意义的行为好像可以从他的手中变出一个时空,在这个时空中塔图仍然在同他对话。可是不久后他在铁网上发现了豁口,想象中的那个时空碎裂了,他没有考虑或许是什么生物弄破的,只觉得是塔图想要回避他了,就将铁网拆卸了。这片地方被他整得辛苦,连近处的树木也落下疲惫的光泽。门雏建议将塔图的头颅移出来埋到他们房子的地下。从那之后,阿莫士走出了阴影,下山去工作,极少再回山上住了。
对于这同一件事,远处还有一个人经历着折磨。那天鸣火和阿枚走散后先回到了家中,却没有看见塔图,不知为何意识中闪现出了塔图不会再回来的概念。他外出寻找了好几天,丝毫没有见到塔图的踪影,强烈的失落感牵涉出了一种直觉,塔图突然的消失或许是已经死了。他不想去揣测这件事与阿枚有关,但在阿枚一反常态的表现中他难以不去联系。
他不辞而别,去了以前和塔图一起待过的那个小洋楼里隐居起来。在这里的一段时间他经历了人生中不曾有过的荒凉,回想起很久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活着的实感,并不是因为时间的久远,那时候思维能力的不健全让印象不真不假,好像是作为人偶一样活在混沌与没有希望的时间里。阿枚在他的生命中是代替母亲的存在,她对他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他想当然的任性也不会被她抱怨。他从很小就非常依赖阿枚,然而无论多深爱的亲人,在久久被麻烦折磨后也会精疲力竭,现在这种无条件的爱幻灭了,塔图也没有再出现过,他放眼望去找不到生存的动机。绝望不能灭绝他的生命,他还得为了维持躯体的动力去行动,却丝毫没有行动的欲望。多少个从午后醒来的瞬间,他都感觉呼吸像铅块压得他陷进自己的身后,窗户在强光照射下映出几根弯曲树枝的黑色叠影,除此之外是一片白光,什么也看不到,安静得仿佛万物将死。
这是个安静惬意且又敞亮的空间。他看着它,惊觉自己从黑暗中出来,却总是躲在避光的阴影处。尚未闭合的明暗格差不断移动着,这种移动带来一种摇摆不定的痛苦,仿佛这个空间开始向他言说他不在此处时的此处。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已经创作不出什么音乐了,在这之前注意力被分散,他沉溺于改造自己的身体,开发更多可能的感觉。贝壳长入他的皮肤是个偶然,不过这是大自然给他的一个有效提示,他尝试与自然界更多与人体不融合的物质接合,使自己的身体在感觉上从世界那里获取更接近实质的内在。他尝试主动将石头接在自己的骨骼中,本来是抱着或死的心态,可是身体只是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比贝壳长入他的皮肤那次反应更强烈,他没日没夜地痛苦,却死不了。然而与此同时在他的身体里也的确产生了新的感觉,在他的理解里,是非任何人类拥有的感觉,是极大的不可思议,比颠覆重力还令他狂喜。但在人类的感觉中,输入的感觉有相对输出的途径。当然他向外获得的感觉找不到输出的途径,这导致感觉的诞生有一种欲望被遏制的错觉,一种不完整的破碎感,使他这种爱蒙上了一层痛苦的割裂面。当他体会到的意象恰到好处时,也无法将这种内心的澎湃用适当的方法宣泄,它积压起来,变成了一种不安。可能他还不知如何成全这种激情,在邂逅了这种惊艳之后,尤其不知如何去化解这种一厢情愿,使得欲望倍感迷惘,无法完全对等,留下了一部分空茫。要做好准备,投入一切回想和曾有的体验,才能对得起他感之所及的每个细节。他叹气,吮吸着那不存在的香,这种激情像看到闪电从身边经过……
于是他痛苦着却也无法自拔地沉溺着,为了破解那种割裂感又反复寻找新的方式。他参透自己的局限,打算从每个角落攻破,灭绝自己的局限来提升自己。他停不下来这个过程,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因为局限会反杀,要求他与它同行——局限本身就是生命,他将会遭到生命的离弃。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损失,他不是外在的生命,而是超越生命的能力。当然这能力是以局限作为磨练和台阶而产生的。
或微妙或浩瀚,他都能从感觉中提炼愉悦,痛苦只是副作用。他燃烧着自己的中心,生命在他的吞噬本能中被消耗,变得病态。然而他将新的知觉带来的精神兴奋连同这躯体的痛苦一起无私地送给了创作,无耻地把它们用做素材。他创作出的东西不再只是音乐,还有音乐的非旋律形式,音乐的题材,甚至音乐的感受途径。然而这些都不够,还不够!他的边缘神经变得异常敏感,从光的潜伏期最初的一刻就能察觉,它们在皮肤中逗留一阵才能变成现实的感应,远比声音的潜伏期长。对它们的感觉交织起来分分合合击碎他的征服欲,他新的作品征服了他的痛苦,也淡化了他的思念。
他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自己,他还无法成为他所要成为的,过去的与未完成的、与正在进行着的相颉颃,他是一个实际上的怪物。他的怪物不是形态,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他可以存于两处,怪物的概念将他拯救。这是一个变量,它为确定的时刻不断到来又逝去,在空间内构不成“在场”,在逻辑上却可以构成多个“在场”,所以在这个概念中他具有多种属性。
一个冲动的人总是容易错误估算,有一次他甚至长途跋涉,去活火山将岩浆注入到血液中,就是这次的实验使他久病不愈,没有痛苦也没有开发出新的感觉,只是整日整夜地疲惫不堪。他只能勉强维持自理,很久都不出门一次,偶尔摘些院子里的野菜充饥。等他注意到的时候,周围人都已经搬走了。
第三章
第十七节. 旧所
在这几年里时咲主持投资,将拆迁活动主要转移到坞山周边,将山顶上的信号屏蔽,以及山下的污染工厂处理掉,导致那片区域变得特别落后。他一直很活跃,只是最近总是待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有时塔仑会推开房间的门看他一眼,看见他冷清的肩膀和衰老的背影,以及一如既往地对于入侵者无所反应。时咲自己预感着一种死亡的迫近,虽然只有隐隐约约的身体不适,虽然这不适也只是困乏的累加也说不定,但这困乏的毒效开花结果,他的精神和智力都在往临界靠拢,他快要帮不上塔仑什么了。他躺在床上,浑浊的眼睛半开半阖,虚弱刻意在兴奋,各种场景迫切地闪入他的视象。所有的闪现都是回忆,没有任何新的想法,他久久张望着记忆的逆行回归,渴望以此来磐涅重生,气力的疲惫让他的思维和意志都变得消极。但即使他的气息微弱到将要散尽,也无法释放他体内蕴藏的全部情绪,一些遗憾郁结在某处,他终日的叹息似乎是想要强行宣泄出那些无法散尽的气氛。时咲看起来愚笨又惹人烦,塔仑怀疑他是打算将氧气生生吐完,他过去的决策与冷静绝对被他自己宣泄得干干净净了。他的萎靡发展地自然而然也很突然,只是从开春以来而已。
现在寻找鸣火的人不只有阿莫士,塔仑也在找,他走过的足迹和打问过的人也有一定数量了。这年塔仑正好长到和塔图死去时差不多大的年龄,他戴着一副厚重的圆眼镜,头上顶着一顶崭新的圆顶帽,盖住他那修剪得乱七八糟的亚麻色头发,外套的色泽滑落得极为凄惨,整个人的打扮滑稽得活像一个小老头。他开了辆旧式的小轿车,每次出门前时咲都会提醒他若是见了那些同样在寻找鸣火的人就先躲起来,免得尴尬。这天他将车开到一个旧城区背后的小村落,村落前还有一条大河和荒地隔开,此处城市败落的原因也许是二十几年前这里修筑起一层厚厚的围墙,墙垣高度足有六十米,将这片城区和其他城市隔离开来。墙上刻着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低处一些墙砖已经脱落了,显示出呼吸过的痕迹。他开车绕了很远的路程才来到这里,还有一些穷苦人守着这片荒地不走。他将车在一排平房前停下来,那些平房的房顶上铺着很干净的苇草,院子周圈用鹅卵石堆砌的矮墙圈起来,门前有个蹲坐着的老妇人,正在阳光下摘菜。
“请问您在附近有见到过这个人吗?”塔仑走上前,很有教养地脱下圆帽夹在腋下并双手握着照片递给老妇人。
老妇人接过照片,看了一下不能辨认,又一手拿着照片将它从眼前推开一段距离。“有见过,不过,也很久了。之前我们住在这河对岸,他住在一栋构造奇特的小洋楼里,偶尔见他走出院墙一副病弱的样子,却总是一个人,所以还比较有印象。”
“那栋房子现在还在吗?”
“唉,我也不清楚呀,这几年都没过去看过,这条大河的右岸经常泛滥,所以对岸的人几乎都搬到了这边,你过了河之后沿着被冲刷的砾石滩向西走去,直到看见有一排排高大的栎树的地方你再寻找好了。”
“好,我去找找看,谢谢您了。”
连接河对岸的只有一座简陋的木架桥,原来石桥被冲毁的痕迹还在,看来这木桥是临时搭建的。塔仑只能把车子留在这边,自己走过去,过桥之后,他找到了长满高大栎树的地方,树叶和掉落的树皮有被扫成堆的痕迹,这里应该还有人来过才对。树是沿着围墙长的,墙上也落满了叶子,在墙的拐角处仔细看时才可以发现掩藏在叶堆中间的一扇门,门是砖红色的木板凌乱拼凑的,但他随即意识到这扇门是类似于装饰品的存在,它与墙体并没有接合的地方。他将那周围墙上爬满的叶子拨开,发现了嵌在石墙上的玻璃,是一扇窗子,窗子内侧被杂物堵着,应该是底层储物用的。于是他仰起头来向上看,才看见有一道伸在半空中的楼梯,梯级很厚,在楼梯底部尽头的侧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铁门,有一定高度,在他所在的高度无法直接够到,估计进出的大门是在围墙的另一侧,而楼梯的顶部尽头在叶子的掩映下拐向了墙对面。房子的设计没有墙外敞开的入口,于是他从墙上翻了过去,在落地时踩到了支离破碎的触感,同时比预想的落地距离短。他踩在了高高堆起的叶片上,这些叶子的干枯程度像是往年残留下来的。它们很久没有被清理过了,躲在墙的阴凉处,散发着不祥的腐朽。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