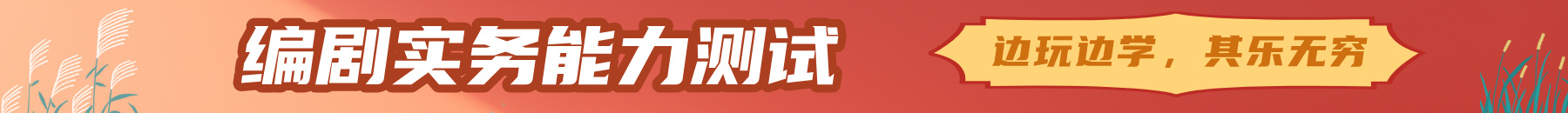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授权发表
字数:24526
阅读:3075
发表:2022/3/23
历史
小说
海豚人之死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五天后的晚上,克沙跑近家时,诧异地愣住了:家里亮了灯,窗前的灯光下堆着自己的行李衣服。惊骇之下忙去开门,没拽开。叫门没人应,喊敲没人理。克沙顿感绝望:完了,被彻底抛弃了。他像被抽了筋骨一样瘫软在行李上。
寒风吹散了克沙的热汗,吹透了皮肉,却吹不醒他的头脑。
邻居老汉去厕所回来惊见了这一幕,把克沙拖回了家。老太煮了姜水,陪着叹气。老汉摇了阵子头出去了。克沙僵尸一样,两眼直直地盯着水碗。
夜深了,老汉领来克沙的同事。克沙没看见一样,失魂地盯着水碗。同事劝解说他没叫开门,让克沙去单位,明天再来劝。克沙如泥塑的人毫无反应。老汉帮同事架走了克沙。
老汉帮同事安顿克沙躺下才离开宿舍。同事一直守着只眨眼的克沙,直到吸光了一盒半香烟才躺下睡去。
第二天,克沙没能起来。一动不动的深凹着眼睛,蜡黄着脸皮,枯裂着唇鼻,完全一具木乃伊。
同事给主任打了电话。主任命令同事拉克沙起来活动,叫医生输液。同事请来医生,一同拉克沙起来,架着他在屋里走动了一个多小时,给他喂了兑糖的米粥,挂了吊瓶。
下午,主任来电话,令同事加两人值班,专门护理克沙,十天一轮,一定让克沙吃喝,并汇集誊写单位年鉴。同事一一照办。克沙形同木偶,让吃就吃口,让走就走走,让写就写写,让烧锅炉就烧,就是不说话,问也不答,也不多活动,告诉走一圈就一圈,多一步不走。
第四天,主任带来医生。医生把形销骨立的克沙好一番折腾,诊断为焦虑后的刺激,处置为食物多样、室外运动、娱乐活动,一个月可自行恢复。主任重新做了部署:三人一组专门陪护;除急重工作外,都由克沙做;饮食改为营养餐;晚上户外活动后三人陪同打牌,输家喝啤酒,克沙输不输都至少喝一瓶;三天一次的集中学习由克沙读报发言;家庭变故上班后再说。
主任的指示如同军令,谁也不能怠慢。三人小组商议了周详措施后立即工作。三人的好奇心不比责任心小,营养餐和玩牌喝酒更是梦寐的福利。他们十分珍惜这些主任都无法享受的福利,自然奉克沙如父母,如影随形地尽心尽力服伺。
对三人来说,美中不足的是克沙玩牌的技术仅仅处于初始阶段,无论三人怎样的作弊输牌,都很难喝到酒,读报发言也费尽了心思,恨不得自己替了克沙。
十天后,克沙的睡眠虽没好转,工作和生活却渐成规律。这些都是他对回家的绝望和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的作用。
在汇集年鉴中,克沙一直克制情绪,坚持动手不动脑。但他的好奇屡屡冲破这道防线,比如训练海鸟的方向、距离等问题就引发了他的深思,怎么也想不出上千海里的训练是为了研究和表演。由此引起警觉,怀疑是执行海豚同样的使命——投掷“饼袋”。克沙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测,又否定了:海面上的舰船和航母在江河湖海都能浮航,不像潜艇在海下受盐度影响得那么强烈而发生“掉深”。另外,海鸟也绝不可能像海豚那样准确的在舰船底下使用“饼袋”,极有可能投掷到舰船上。一旦投掷在舰船上就会被发现收缴,被剖析仿制,被反过来“掉深”自己。想到这,克沙就彻底否定了海鸟投掷“饼袋”的猜测,又神不由已的把心思落到“饼袋”上。
克沙推测了“饼袋”的工作原理:海豚经日常的声导训练,能很快游向声导源的潜艇下方。受潜艇声频影响,吐出“饼袋”。“袋”被海水溶解掉,“袋”里的“饼”立刻凝聚海水中的盐,使海水在一刹那被分解为盐和淡水。淡水浮力远远低于海水而使潜艇“掉深”。这个原理让克沙深信不疑。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加里分所生物水化学应是专门研究这项技术的。但他们研究的“饼”是什么又成了克沙的下一道思考题。
克沙的思考不敢表现在同事的视线中,否则会引发同事们的猜疑,只能在独自一人跑步和睡前暗自进行。几天里,克沙总在冥思苦想,总是衔接不上,总是从隐约到明晰到否决的循环。后来,他从海水盐类物质来推导了几次,觉得柳岸花明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析出海水中氯化钠的那个东西就是“饼”。他为这个破解而兴奋。这个兴奋使他无法入眠,但他担心出现黑眼圈和精力不支,他不得不终止了思考,天天晚上到家门前望上一阵子,或者清雪扫院、劈柴码垛,希望能看到米莉娅和孩子、能说上一句。虽然一直被躲避,但他一直坚守。
这一个月里,克沙只与孩子说了几句。孩子顾左右而言他,极尽应付。克沙知道这是米莉娅的严厉要求。如他再纠缠,孩子必将受到米莉娅的责难。所以,克沙只能争取多见面少说话。尽管如此,两个孩子仍然变更着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和时间,尽量躲避克沙。这让克沙苦恼又无奈,只能把父子情收到心底,用工作激情来暂时代替对妻儿的思恋。
在抄录年鉴时,克沙无意中发现,海鸟的训练似乎纯粹用于境外的破坏——高温季节的森林大燃烧。这个发现让他惊悸万分。他竭力地用种种信息来否定这个发现,却越被证明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工作纪实中载明了对海鸟的突出训导是定向、耐力和定点投掷“火种”。“火种”是克沙自己对海鸟投掷物的命名。海鸟的这些工作无法与火灾相联系,这是主任他们让克沙公开记于年鉴的原因,也可能是主任他们掩人耳目的手段。但对克沙来说是欲盖弥彰。可其他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的。即便是克沙,也只有把放飞海鸟的方向和时间与旧新闻中的火灾位置和时间联结起来,才能推测出其中的奥秘。最能说明事实的是在尖尾雨燕南迁非洲和燕鸥迁徙南极的时节里,从加里分所向西放飞中,那国南部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火灾;由黑海向北放飞后乌国南部林区发生火灾;向西,保国森林大火;向西南,希国火灾,还有西部葡国和四次的班国。这九次大火焚毁森林二十九万公顷,撤离疏散四万多人,数百人死亡。这九次仅是克沙从年鉴和旧新闻的互相印证中坐实了的,另有一些年鉴中记载的,因找不到旧报纸而无法链接。但类比起来,只要放飞定有火灾。
这些火灾不在身边,克沙又心转家里,自然不太注意灾难的后果。但他胡思乱想的习惯是无法改变的。九次火灾中,令他无法理解的是班国不是北约成员国,又隔着意国、希国这些北约国,为什么要烧他?保国既是华约成员国,又隔断了北约国,为什么也烧他?更不能理解的是烧乌国这个加盟共和国。烧他们是失误?可鸟的天性、严格的训练、精准的演习是绝不会失误的,也绝不允许失误。那还能是什么?克沙苦苦思索,终于猜想到这是以自残手段来掩人耳目的策略。
抄录中,克沙会查阅书刋等资料来核对勘正原稿。出于好奇,克沙就利用这些机会对火灾地点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比较系统地思索,陆续取得了惊天的发现:火灾地点均为原始冻源,焚烧暖化了冻层,冻层中动物遗尸携带的炭疽菌遇热苏醒并活跃,继而感染地表上的一切,再经各种动物的四下传播,人类就在劫难逃了。
这万劫不复的无声无息的毁灭,一时令克沙惊恐万状。努力了许久才被他刻意的天天去堵截孩子、天天都失望的事情遮掩了过去,就连主任也只当克沙是对家的变故而愁眉不展,丝毫没料到克沙已经窥测到核心绝密,自然就没有丝毫的防范。
令克沙百思不解的是海鸟投掷的“火种”是什么材料。什么材料在海鸟吐到或排泄到森林能即刻起火?这个问题就像“饼袋”一样,令克沙无法分析出内在成份是袋装钠还是糖、水、浓硫酸的铅皮弹。不管是什么,肯定不能太复杂了。另一不解是和平时期为什么要冒险玩火?就像“掉深”潜艇一样,一旦被发觉必将受到天翻地覆的报复。这些问题如同千钧砣,压得克沙胸闷心慌,难闭眼难入眠,折磨得克沙痛苦不堪又不敢流露,更不敢用药调节,只能透支体能把自己累得死过去。可过量的运动又使他异常兴奋,更难安定下来。
克沙只能用孩子来掩盖同事们的亲切问讯。
熬了数日,主任回来,单独问克沙想不想正式离家?如离开,单位把他列入今年的楼房分配计划,他将单独享有楼房。克沙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离不弃。主任尊重克沙,说不离只能用自有私房兑换楼房,且可能被米莉娅占有。克沙盼望妻儿早日住上福利楼房,没有顾及主任提醒的自己仍将两手空空的后果,就定了下来。
克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学的孩子,让转告米莉娅,企望自己被重视被接回家。但孩子仍然冷淡地对待他,使他感到回家的渺茫。但克沙仍然感到给妻儿争取楼房是自己的责任,是对家庭的贡献。他为此而欣慰。
只有誊写年鉴,克沙才能暂时放下对妻儿的思念。可正如前面的赘述,克沙一直在破解着为什么玩火这个难题。在一次休息时,他习惯地用手指在世界地图上比划着“掉深”潜艇和火灾的位置时,无意中发现祖国在世敌火力的完全覆盖之下。除北冰洋,其他都是对方强大的军事基地。一旦战起,三面攻击就覆盖了祖国的角角落落,而祖国几乎没有还手空间。这时的克沙才恍然大悟:削弱武装、破坏经济、引爆瘟疫,毁灭敌人。
克沙为得到答案而兴奋不已。他把“掉深”“火灾”“瘟疫”视为绝对的“突破”战略,认为“突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反制世敌。他开始把主任他们当作二战中的将军来膜拜,把“饼袋”“火种”和激活冻源炭疽菌的技术视作最杰出的科研成果。当然,这个狂喜只能沸腾在心底,不敢丝毫喜形于色。
不知是收获了这个答案还是为祖国的“突破”而亢奋,克沙又陷极难入睡和倾力掩饰的憔悴中。
年鉴抄录刚要结束,克沙父母来信借钱。父母都有退休工资,医食住行都有保障还借钱干什么?信上没说,克沙不解。如数寄去后,克沙琢磨一定是“大玉米运动”恶变为大饥饿,导致食物匮乏,供应迟滞,父母不得不去黑市高价购买口粮。克沙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待遇福利全被取消,食堂主食定人定量,主任增人捕捞海产品来补充的这些情况,猜想父母一定饿得不行了。但孩子还很好,他们住校后能吃饱,没让克沙分心作难。但身边的形势却愈加紧张:一些父母亲属来投靠同事,造成本地的主副食供应紧张,引起居民的强烈不满,几乎发生哄抢骚乱。邻居老汉参与其中被送学习班,有的市民被控组织、串联和煽动被捕走,米莉娅无意的抱怨招致严厉警告。随即,分所连续开了几天的大会,宣告要坚定经济好转信心,严格执行国家政策,严厉打击黑市犯罪,严禁邮寄干海品等食物,要勤谨工作,杜绝懈怠。随后开了几次内部会议,一方面强调垂范和带领工人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强调纪律。最后一次会议失控得让克沙崩溃了。会议算了克沙的秋后帐:经常给父母亲属邮寄干海品,扰乱经济秩序,给予处分;对米莉娅的言行负有责任,收回福利楼;退赔三人小组照顾他的一切费用。同时,主任受牵连被批评,随后被调离。众矢之的的克沙孤立得无依无靠,消沉得无地自容无处躲藏,也使他失眠得不分昼夜、痛不欲生了。
克沙心挂妻儿,不能轻言生命,只能把精力从妻儿父母亲属、主任同事新领导的身上,以及一再衰退的经济形势上全部转移到训导新海豚的工作上,俨然一个罪孽深重的认罪改造的犯人,不敢抬头,不敢言语,木偶一样活着。可在他的内心深处,懊悔、自责轮番地猛烈撞击着他的心胸,仿佛辜负了妻儿父母亲属和主任他们,仿佛自己是他们的累赘,是世上最最多余的只能牵累别人的边缘人,不,应是垃圾人。克沙越内疚越恨自己的无能,恨不得终结自己来换取他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他曾经幻想一听《黑色的星期天》,快速地巧妙地无声息地结束自己。但他实在无法舍弃妻儿父母,一直在结束的边缘徘徊。
由于“大玉米运动”的失败,粮食供给日趋紧张。克沙对父母亲属一而再地求援求救无力施助,加上邻居和一些老人的相继饿死,使克沙开始怀疑政策的方向。这个怀疑逐渐取代了自卑,逐渐颠覆了先前的敬业,逐渐产生了抵触“突破”战略的念头,逐渐地想要扭转这项战略来迫使政府增加粮食。
寒风吹散了克沙的热汗,吹透了皮肉,却吹不醒他的头脑。
邻居老汉去厕所回来惊见了这一幕,把克沙拖回了家。老太煮了姜水,陪着叹气。老汉摇了阵子头出去了。克沙僵尸一样,两眼直直地盯着水碗。
夜深了,老汉领来克沙的同事。克沙没看见一样,失魂地盯着水碗。同事劝解说他没叫开门,让克沙去单位,明天再来劝。克沙如泥塑的人毫无反应。老汉帮同事架走了克沙。
老汉帮同事安顿克沙躺下才离开宿舍。同事一直守着只眨眼的克沙,直到吸光了一盒半香烟才躺下睡去。
第二天,克沙没能起来。一动不动的深凹着眼睛,蜡黄着脸皮,枯裂着唇鼻,完全一具木乃伊。
同事给主任打了电话。主任命令同事拉克沙起来活动,叫医生输液。同事请来医生,一同拉克沙起来,架着他在屋里走动了一个多小时,给他喂了兑糖的米粥,挂了吊瓶。
下午,主任来电话,令同事加两人值班,专门护理克沙,十天一轮,一定让克沙吃喝,并汇集誊写单位年鉴。同事一一照办。克沙形同木偶,让吃就吃口,让走就走走,让写就写写,让烧锅炉就烧,就是不说话,问也不答,也不多活动,告诉走一圈就一圈,多一步不走。
第四天,主任带来医生。医生把形销骨立的克沙好一番折腾,诊断为焦虑后的刺激,处置为食物多样、室外运动、娱乐活动,一个月可自行恢复。主任重新做了部署:三人一组专门陪护;除急重工作外,都由克沙做;饮食改为营养餐;晚上户外活动后三人陪同打牌,输家喝啤酒,克沙输不输都至少喝一瓶;三天一次的集中学习由克沙读报发言;家庭变故上班后再说。
主任的指示如同军令,谁也不能怠慢。三人小组商议了周详措施后立即工作。三人的好奇心不比责任心小,营养餐和玩牌喝酒更是梦寐的福利。他们十分珍惜这些主任都无法享受的福利,自然奉克沙如父母,如影随形地尽心尽力服伺。
对三人来说,美中不足的是克沙玩牌的技术仅仅处于初始阶段,无论三人怎样的作弊输牌,都很难喝到酒,读报发言也费尽了心思,恨不得自己替了克沙。
十天后,克沙的睡眠虽没好转,工作和生活却渐成规律。这些都是他对回家的绝望和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的作用。
在汇集年鉴中,克沙一直克制情绪,坚持动手不动脑。但他的好奇屡屡冲破这道防线,比如训练海鸟的方向、距离等问题就引发了他的深思,怎么也想不出上千海里的训练是为了研究和表演。由此引起警觉,怀疑是执行海豚同样的使命——投掷“饼袋”。克沙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测,又否定了:海面上的舰船和航母在江河湖海都能浮航,不像潜艇在海下受盐度影响得那么强烈而发生“掉深”。另外,海鸟也绝不可能像海豚那样准确的在舰船底下使用“饼袋”,极有可能投掷到舰船上。一旦投掷在舰船上就会被发现收缴,被剖析仿制,被反过来“掉深”自己。想到这,克沙就彻底否定了海鸟投掷“饼袋”的猜测,又神不由已的把心思落到“饼袋”上。
克沙推测了“饼袋”的工作原理:海豚经日常的声导训练,能很快游向声导源的潜艇下方。受潜艇声频影响,吐出“饼袋”。“袋”被海水溶解掉,“袋”里的“饼”立刻凝聚海水中的盐,使海水在一刹那被分解为盐和淡水。淡水浮力远远低于海水而使潜艇“掉深”。这个原理让克沙深信不疑。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加里分所生物水化学应是专门研究这项技术的。但他们研究的“饼”是什么又成了克沙的下一道思考题。
克沙的思考不敢表现在同事的视线中,否则会引发同事们的猜疑,只能在独自一人跑步和睡前暗自进行。几天里,克沙总在冥思苦想,总是衔接不上,总是从隐约到明晰到否决的循环。后来,他从海水盐类物质来推导了几次,觉得柳岸花明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析出海水中氯化钠的那个东西就是“饼”。他为这个破解而兴奋。这个兴奋使他无法入眠,但他担心出现黑眼圈和精力不支,他不得不终止了思考,天天晚上到家门前望上一阵子,或者清雪扫院、劈柴码垛,希望能看到米莉娅和孩子、能说上一句。虽然一直被躲避,但他一直坚守。
这一个月里,克沙只与孩子说了几句。孩子顾左右而言他,极尽应付。克沙知道这是米莉娅的严厉要求。如他再纠缠,孩子必将受到米莉娅的责难。所以,克沙只能争取多见面少说话。尽管如此,两个孩子仍然变更着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和时间,尽量躲避克沙。这让克沙苦恼又无奈,只能把父子情收到心底,用工作激情来暂时代替对妻儿的思恋。
在抄录年鉴时,克沙无意中发现,海鸟的训练似乎纯粹用于境外的破坏——高温季节的森林大燃烧。这个发现让他惊悸万分。他竭力地用种种信息来否定这个发现,却越被证明这是铁一样的事实:工作纪实中载明了对海鸟的突出训导是定向、耐力和定点投掷“火种”。“火种”是克沙自己对海鸟投掷物的命名。海鸟的这些工作无法与火灾相联系,这是主任他们让克沙公开记于年鉴的原因,也可能是主任他们掩人耳目的手段。但对克沙来说是欲盖弥彰。可其他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的。即便是克沙,也只有把放飞海鸟的方向和时间与旧新闻中的火灾位置和时间联结起来,才能推测出其中的奥秘。最能说明事实的是在尖尾雨燕南迁非洲和燕鸥迁徙南极的时节里,从加里分所向西放飞中,那国南部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火灾;由黑海向北放飞后乌国南部林区发生火灾;向西,保国森林大火;向西南,希国火灾,还有西部葡国和四次的班国。这九次大火焚毁森林二十九万公顷,撤离疏散四万多人,数百人死亡。这九次仅是克沙从年鉴和旧新闻的互相印证中坐实了的,另有一些年鉴中记载的,因找不到旧报纸而无法链接。但类比起来,只要放飞定有火灾。
这些火灾不在身边,克沙又心转家里,自然不太注意灾难的后果。但他胡思乱想的习惯是无法改变的。九次火灾中,令他无法理解的是班国不是北约成员国,又隔着意国、希国这些北约国,为什么要烧他?保国既是华约成员国,又隔断了北约国,为什么也烧他?更不能理解的是烧乌国这个加盟共和国。烧他们是失误?可鸟的天性、严格的训练、精准的演习是绝不会失误的,也绝不允许失误。那还能是什么?克沙苦苦思索,终于猜想到这是以自残手段来掩人耳目的策略。
抄录中,克沙会查阅书刋等资料来核对勘正原稿。出于好奇,克沙就利用这些机会对火灾地点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比较系统地思索,陆续取得了惊天的发现:火灾地点均为原始冻源,焚烧暖化了冻层,冻层中动物遗尸携带的炭疽菌遇热苏醒并活跃,继而感染地表上的一切,再经各种动物的四下传播,人类就在劫难逃了。
这万劫不复的无声无息的毁灭,一时令克沙惊恐万状。努力了许久才被他刻意的天天去堵截孩子、天天都失望的事情遮掩了过去,就连主任也只当克沙是对家的变故而愁眉不展,丝毫没料到克沙已经窥测到核心绝密,自然就没有丝毫的防范。
令克沙百思不解的是海鸟投掷的“火种”是什么材料。什么材料在海鸟吐到或排泄到森林能即刻起火?这个问题就像“饼袋”一样,令克沙无法分析出内在成份是袋装钠还是糖、水、浓硫酸的铅皮弹。不管是什么,肯定不能太复杂了。另一不解是和平时期为什么要冒险玩火?就像“掉深”潜艇一样,一旦被发觉必将受到天翻地覆的报复。这些问题如同千钧砣,压得克沙胸闷心慌,难闭眼难入眠,折磨得克沙痛苦不堪又不敢流露,更不敢用药调节,只能透支体能把自己累得死过去。可过量的运动又使他异常兴奋,更难安定下来。
克沙只能用孩子来掩盖同事们的亲切问讯。
熬了数日,主任回来,单独问克沙想不想正式离家?如离开,单位把他列入今年的楼房分配计划,他将单独享有楼房。克沙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离不弃。主任尊重克沙,说不离只能用自有私房兑换楼房,且可能被米莉娅占有。克沙盼望妻儿早日住上福利楼房,没有顾及主任提醒的自己仍将两手空空的后果,就定了下来。
克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学的孩子,让转告米莉娅,企望自己被重视被接回家。但孩子仍然冷淡地对待他,使他感到回家的渺茫。但克沙仍然感到给妻儿争取楼房是自己的责任,是对家庭的贡献。他为此而欣慰。
只有誊写年鉴,克沙才能暂时放下对妻儿的思念。可正如前面的赘述,克沙一直在破解着为什么玩火这个难题。在一次休息时,他习惯地用手指在世界地图上比划着“掉深”潜艇和火灾的位置时,无意中发现祖国在世敌火力的完全覆盖之下。除北冰洋,其他都是对方强大的军事基地。一旦战起,三面攻击就覆盖了祖国的角角落落,而祖国几乎没有还手空间。这时的克沙才恍然大悟:削弱武装、破坏经济、引爆瘟疫,毁灭敌人。
克沙为得到答案而兴奋不已。他把“掉深”“火灾”“瘟疫”视为绝对的“突破”战略,认为“突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反制世敌。他开始把主任他们当作二战中的将军来膜拜,把“饼袋”“火种”和激活冻源炭疽菌的技术视作最杰出的科研成果。当然,这个狂喜只能沸腾在心底,不敢丝毫喜形于色。
不知是收获了这个答案还是为祖国的“突破”而亢奋,克沙又陷极难入睡和倾力掩饰的憔悴中。
年鉴抄录刚要结束,克沙父母来信借钱。父母都有退休工资,医食住行都有保障还借钱干什么?信上没说,克沙不解。如数寄去后,克沙琢磨一定是“大玉米运动”恶变为大饥饿,导致食物匮乏,供应迟滞,父母不得不去黑市高价购买口粮。克沙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待遇福利全被取消,食堂主食定人定量,主任增人捕捞海产品来补充的这些情况,猜想父母一定饿得不行了。但孩子还很好,他们住校后能吃饱,没让克沙分心作难。但身边的形势却愈加紧张:一些父母亲属来投靠同事,造成本地的主副食供应紧张,引起居民的强烈不满,几乎发生哄抢骚乱。邻居老汉参与其中被送学习班,有的市民被控组织、串联和煽动被捕走,米莉娅无意的抱怨招致严厉警告。随即,分所连续开了几天的大会,宣告要坚定经济好转信心,严格执行国家政策,严厉打击黑市犯罪,严禁邮寄干海品等食物,要勤谨工作,杜绝懈怠。随后开了几次内部会议,一方面强调垂范和带领工人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强调纪律。最后一次会议失控得让克沙崩溃了。会议算了克沙的秋后帐:经常给父母亲属邮寄干海品,扰乱经济秩序,给予处分;对米莉娅的言行负有责任,收回福利楼;退赔三人小组照顾他的一切费用。同时,主任受牵连被批评,随后被调离。众矢之的的克沙孤立得无依无靠,消沉得无地自容无处躲藏,也使他失眠得不分昼夜、痛不欲生了。
克沙心挂妻儿,不能轻言生命,只能把精力从妻儿父母亲属、主任同事新领导的身上,以及一再衰退的经济形势上全部转移到训导新海豚的工作上,俨然一个罪孽深重的认罪改造的犯人,不敢抬头,不敢言语,木偶一样活着。可在他的内心深处,懊悔、自责轮番地猛烈撞击着他的心胸,仿佛辜负了妻儿父母亲属和主任他们,仿佛自己是他们的累赘,是世上最最多余的只能牵累别人的边缘人,不,应是垃圾人。克沙越内疚越恨自己的无能,恨不得终结自己来换取他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他曾经幻想一听《黑色的星期天》,快速地巧妙地无声息地结束自己。但他实在无法舍弃妻儿父母,一直在结束的边缘徘徊。
由于“大玉米运动”的失败,粮食供给日趋紧张。克沙对父母亲属一而再地求援求救无力施助,加上邻居和一些老人的相继饿死,使克沙开始怀疑政策的方向。这个怀疑逐渐取代了自卑,逐渐颠覆了先前的敬业,逐渐产生了抵触“突破”战略的念头,逐渐地想要扭转这项战略来迫使政府增加粮食。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