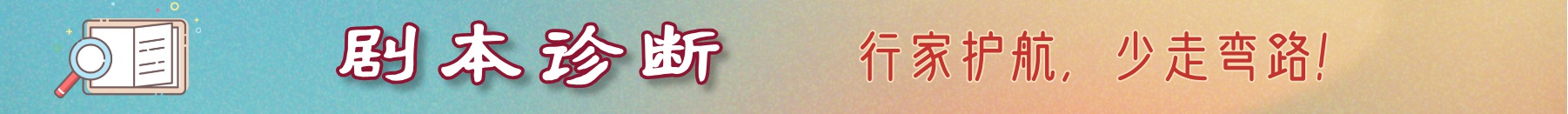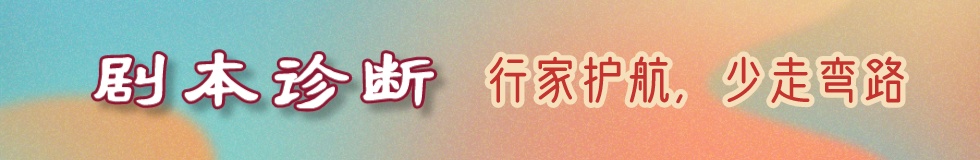权属:原创 · 独家授权
字数:27353
阅读:9652
发表:2012/4/4
20章 其他 小说
《飞山明烛》第1章
1
2
3
4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小伙子,你的包谷粑不卖,又背这么多干啥?
——盘缠,路费。(小王插话:“明明是包谷粑,怎么又成了路费?)
——(随和地)安步当车嘛!路费,路粮,都差不多,都重要。小王,不要门缝里瞧人。(笑着对小伙子说)你自有你的道理,对不对?
——对!(从脸上和话声里读出了对面这个中年人的和蔼、慈祥、诙谐语言中深邃的含意,又仔细打量一下)你……(努力回忆)好像……你是县委罗书记吧?
——我正是罗之英,你眼力不错,你叫什么名字?
——冉海洋。
——(若有所思)你就是那个模范共青团员冉海洋吧?
——算不上什么模范,这是上级和组织的信任。
——你背这一背“路费”到哪里去?
——上学。
——龙潭中学毕业的?
——是。
——上哪个大学?
——清华。
一字千钧,份量够重!“清华”两字击在县委书记心坎上,“格登”一下,不禁一颤,他脸上顿时严肃起来。
冉、王二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双双愣在当地。
罗之英在黑水区检查了工作,还准备到丁市区去,现在改变了注意:先解冉海洋的燃眉之急再说。
冉、王二人还在捉摸呢,就听到罗之英极为严肃认真地说:“冉海洋同学,上车吧!我把你的‘盘缠’强买了。今天,最迟明天,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给你一个妥贴之计。”
小轿车向古城县城飞奔。
当天下午,县委、县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县委各部委、县人委各科室的同志,都来到了古城县大礼堂。
大家看着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县委书记身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青年,罗之英和青年面前,放着满满一背包谷粑。人们对此大惑不解:这个粑粑客“厉害”到家了,卖包谷粑卖到“老爷大堂”上来了!
人们七嘴八舌,纷纷议论,都想解破这个奇特的谜语。
会议开始。第一个议程:吃包谷粑,由县委书记亲自发放,一人一个,未领到的就继续“猜谜”。
吃包谷粑的,“猜谜的”,个个傻了眼!今天遇到了特别的人物、特别的事情、特别的场景,感受着特别的氛围。
一位“眼镜”品尝得最细,吃一口,嚼一阵,觉得合口,还真想再吃一个。
待大家吃完了神秘的“特餐”,县委书记罗之英发话了:“同志们,包谷粑味道如何?”
“好吃,好吃,又香又甜!”一片赞扬声,又一齐把欲知下文的目光投向县委书记和那青年。
冉海洋从容自若,并不惊慌。
“眼镜”最后一个吃完,用手巾擦擦手,一边“抛”出“文”来:“此粑粑味纯而美,惟不知价值几何?”
会场里哄堂大笑。
罗之英没有笑,也没有责怪“眼镜”,而是以包谷粑为“引子”,徐徐入题地演说起来:“同志们,这包谷粑价值几何呢?可以说它不值几个钱,也可以说它价值无限。说它价值无限,因为这是古城人民对我们的鞭策和教育!(把冉海洋拉在身边,激动地,对着县团委书记吴青问,然后又自问自答)你不认识他吗?应该说你认识他。同志们,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青年,不是粑粑客,他就是县团委去年表彰的那个模范共青团员冉海洋,就是到旋涡潭抢救两个落水儿童的青年英雄。(此时,听众情绪激昂,“眼镜”也从眼镜里射出敬佩的光)冉海洋同学德才兼备,考上了中国的第一名牌——清华大学。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这是我们古城人民的骄傲!话又说回来,古城已经解放十多年了,我们为人民清除了匪患,清除了一些旧风俗,但我们却没有清除贫穷。我们的责任没尽到,我们是不称职的。冉海洋考取清华大学,他的父母无法给他拿路费、生活费。大热天,包谷粑很快就会臭馊的,吃了不生病才怪!这些责任我第一个该负,我们大家都应承担!我们宁愿节衣缩食,也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冉海洋同学穿着草鞋、背着臭馊的包谷粑上北京!那将是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耻辱!”
全场哗然,唏嘘叹息之声不绝于耳。
语惊四座,人人心里卷起阵阵风暴。
难忘的一幕,深深地烙进了冉海洋的心灵。
罗之英继续说:“同志们,静一静。现在我郑重提议,每人给冉海洋同学献上一份爱心。”他率先拿出200元,郑重地放进了敞口“募捐箱”——冉海洋的包谷粑背篼。人们接着纷纷解囊,50元、20元、10元……面额不等的人民币都进了背篼。
除了上街,“眼镜”从来不爱带钱在身上,此时便掏出他心爱的金壳怀表递给冉海洋。冉海洋认为是奢侈品,坚持不要。经罗之英从旁帮着劝说再三,冉海洋才勉强收下。
特殊会议结束之时,冉海洋捧着古城人民赤诚的爱,热泪盈眶,泣声带颤:“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为——为古城人民——争光!”
路费、生活费,总起来已超过三千之数。由于与会者把这个激动人心的信息到处传开,又有不少人找到县委招待所冉海洋的临时住处,把一份份爱心和鼓励,交给了冉海洋。
当晚,冉海洋以无限欣慰的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县委书记和县上领导为他解决了路费、生活费问题,好让父母放心。
翌日早晨,朝阳刚刚升起,司机小王遵照罗之英的吩咐,把冉海洋送到县车站,并递给他一张船票:“这张船票是给你送金壳表那位‘眼镜’,也就是县委办公室杨主任几天前为他表妹预订的。客车到龚滩,从龚滩坐船下涪陵,然后直下武汉就可以坐火车了。”“那他的表妹呢?”“她是武汉歌舞团的一个编剧,昨晚听杨主任讲了你的故事,声言船票无偿转让,并要到你家乡去熟悉生活,去看望你的父母,然后编个什么歌舞之类,我就说不圆范了。”
冉海洋别了司机小王师傅,登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徐徐启动,他耳畔还响着罗之英的演说,脑际还回味着捐资的场景。他深情地回望古城山川:故乡啊亲人,亲人啊故乡,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我一定要用最好的成绩向你们报喜!
尾声:
冉海洋巧遇县委书记罗之英,罗书记动员县委、县人委机关所有干部职工为他化缘,“买”下了他的一背包谷粑,他才有钱乘车到北京。这份情,这份爱,冉海洋不仅铭记了一生,还以此教育子侄辈。
文化大革命中,罗之英在古城备受冲击,有一派群众组织甚至扬言要将他置于死地。在国务院工作的冉海洋从父母的家书中得知这一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此事。有关领导采纳了冉海洋的建议,把罗之英调到了北京。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国家日益昌盛、富裕,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也吹响了。可是冉海洋的家乡,贺龙元帅当年开创川鄂湘黔根据地的地方,难与沿海地区相比,这几十年来一直变化不大。他儿子冉恩的姑姑、姑父,舅舅、舅娘,一个个血老表、姨老表,凡未参加工作的,都还头戴贫困帽子,身处贫困环境。冉海洋一家的周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冉恩大学一毕业,就赞同父亲的提议,将攻读硕士研究生从脱产改为函授,到渝东南家乡去当村官,因为c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是统筹城乡的试点,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冉恩的想法,就是要闯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子,也代父亲报答古城故土乡亲的恩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有了罗书记的捐助,才解决了他父亲上大学缺路费与生活费的问题,正因为这份爱,才让爱得以延续。这份情意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永世难忘。西部大开发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开发的大潮中,古城这个地方终究有一天会摆脱现状的。
三、艰辛求学路
彭长贵考上了祥云县第一中学后,只身到校报名。校长叶伊理听说彭长贵家非常困难,学杂费交不起,就让彭长贵回家把母亲接来,给叶校长家当保姆。16岁的彭长贵头天进城,第二天回家,每天步行130多里,一路苦,两头黑,母亲听说后,非常感动,但有点不敢相信。没有办法,彭长贵又往城里走去。叶校长给彭母写了一封短信。彭长贵就这样往返几趟,终于把事情办好,可以进校读书了。
救了蛤蟆死了蛇。母亲冉凤英带着儿子离开大元乡政府机关时,还清所有欠账,已经所剩无几了。
如果不是叶校长拉了一把,真不知要想什么办法才好。但是,她半点也不后悔:外甥冉海洋有了出头之日;儿子呢,螺蛳屙屎有出处;又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母坚强,儿坚强,彭长贵一边读书,一边向老师和其他人打听:“像我这样又瞎又麻的人读书有用吗?”问了一次又一次,谁也无法答复他。
但是,母亲总是鼓励着他,支撑着他,他也很努力。母子俩都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三年初中读下来,祥云一中出了有名的“大元三学子”:60级1班第一名白云中,大元公社鱼塘溪人;60级2班第一名方长印,班长兼班团支部副书记,大元公社邱窠土人;60级2班第二名彭长贵,班团支部书记。
当然,那两位同学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他们被保送到本校高中部学习;但又麻又瞎的彭长贵就没那么幸运了,眼睛残疾决定了他不能升学、不能考干、不能进厂当工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啊!
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师毕业生里的中共党员可以进入高等师范院校读书,虽然特别不容易,但彭长贵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还好,他被保送到祥云师范学校就读了。作为团员考生,他优先得到了录取通知书。
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后,母亲第一句话就是:“我到师范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积极参加团组织工作,争取尽快入党,争取保送到高等师范院校学习,将来我要当个好教师,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母亲很支持他:“行,就这样办吧!”
祥云师范学校坐落在祥云县城南部怀龙镇, 地处梅江河南岸。
1960年9月,彭长贵荣幸地进入祥云师范学校读书。从进校学习的第一天起,彭长贵就准备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无比壮丽的人民教育事业。
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他珍惜每分每秒,显示了超乎常人的刻苦。理想激励着他,他时时憧憬着当一名教师。他很少休息,一直信心满怀而执著地学习每一门课程,还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团组织生活。作为校团委宣传委员,他更感到搞好业余文艺宣传活动是他的本份,责无旁贷。
校舍的简陋,他竟然视而不见;自己的残疾,此时也毫不在乎了。谁知未来的日子,他却经历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和坎坷,一圈又一圈曲折,一重又一重难关。大气候、历史、地理、自然种种因素,都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进程,都制约着重每个人的人生。
但是,彭长贵深知事在人为,地在人耕,他把表哥冉海洋作为榜样,以钢铁和信念,以大半生的自强拼搏、努力奋斗,最终实现了自已的理想和抱负。虽然他54岁才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是并不觉得委屈,并不觉得这好事姗姗来迟,并不觉得有任何后悔,因为他把大半生心血都毫不保留地献给了伟大的党和人民,因而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家乡和祖国。
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及农村教育的状况,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那是被左倾理想搅拌的年月,都搅拌成什么样了呢?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全国有7千万人口死于饥饿。党中央为了力挽狂澜,发出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祥云师范不得不停办,同学们慷慨而激昂。彭长贵和其他几个同学在当晚学校召开的毕业晚会上,登上了主席台向全体师生大表而特表决心: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大有作为,我们要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当中去锻炼自己,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彭长贵在讲台上,用非常激动的语言向党和人民、向祖国表决心:“我要到农村去书写最好最好的文章,画最美最美的图画,谱写最美最美的乐章,同学们,大家在劳模会上再见吧!”
飞山明烛第二章顽强的拉锯战
彭长贵回到力大坳老家,所见到的一切与他想象的简直有天壤之别:自家的阶沿都被别人种菜了,房子因多年失修,现已变成了生产队的牛圈,天通地漏,屋内所有的动用家私已不存在。生产队说要给他家退赔,彭长贵知道那只是口头上说说,行动上不知要等上多少年,目前到哪里去住呢?没有办法,母子俩只有投奔秋窠土姐姐家居住。
一天,彭长贵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来了衣帽非常破旧的两个中年人,开口就问“你就是彭长贵吧?听说你是一大知识分子,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居住好吗?”原来二位中年人,一个是再丰大队副大队长张贵华;一个是复员军人张兴富。
彭长贵好生奇怪:“难道说你们那里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如果有,我今天就不用来了。这两年,我们队连一个记分员都没有,实在没有办法分粮食就只好拿家私印,一年生产多少粮食,交多少公粮,留多少种子,大家分多少口粮都不知道。”在二位的一再请求下,彭长贵一家从此由秋窠土迁往飞山居住。由于再丰大队有文化的人实在太少,彭长贵不但担任飞山生产队会计,还担任了再丰大队会计、第二生产队会计,另外又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
那时贫困落后的穷山沟,吃饭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饥饿和疾病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他们连做梦也不敢想办学读书的事,彭长贵却深深地知道要想改变如此贫穷落后的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大山里的人识文断字,同时彭长贵也清楚地知道要想在这里办学,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绝大部分人是不会支持的,因为他们对办学的好处根本不理解。彭长贵天生犟脾气――再难也要办,没有其它选择。
彭长贵所担任的三份会计工作本身就是很难做的了,部分社员对国家的分配政策不了解,对按工分、人口、肥料比例分配的方式不理解,大吵大闹的大有人在。彭长贵算账时,一些不能上坡干活的老头就围在彭长贵周围,监督他做账,生怕他做账不公。但时间一长,大家就信任彭长贵了,总觉得比他们原来的用家私量要简单和准确得多了。
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原生产队长姚明武眼看他扶持上阵的几位亲信败下阵来,自己捞不到油水了,就千方百计在背后大搞阴诡计,想方设法要把彭长贵排挤掉。
小春预算、大春预算,姚明武眼看彭长贵在一、二、三、四队走来走去,他一脑壳火冒,歪起嘴巴说彭长贵是游山玩水,专混大队报酬,其实彭长贵既要给大队和一二三四队算账,又要去三队、四队辅导会计业务,到一个队或两天或三天不等。姚明武什么也不懂,总觉得彭长贵是懒惰,他说:“火热的大太阳天,我们在坡上晒,他在家里享福,太便宜他了。”
更有甚者,姚明武一遇到公社干部或县、区工作队的干部,就要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以泄私愤;姚明武多次采取同一个办法:“某同志,我们队上会计不见了,我已经登寻人启示了,你们要是在哪里看到彭长贵,就把他带到我们生产队来。”
由于“寻人启示”多次登载,干部们已司空见惯,都懒得理他了。干部们又知道彭长贵是在干正常业务,谁也不去责怪彭长贵。
后来姚明武一登“寻人启示”对方就立即反唇相讥:“你的寻人启示都登到省里去了,文章做大啦!”由于姚明武做事不是出于公心,受到众人的反对,最后他就不再登“寻人启示”了。
飞山人没有文化的难处,彭长贵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而飞山人却身处困境而不觉,反而觉得习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祖祖辈辈不都有这样过来了吗?彭长贵提出办学的事,,姚明武等人一唱一合,振振有词,唾沫乱飞,说得头头是道:只要肯劳动就有饭吃,读书有什么用,书能当饭吃吗?
飞山人由于没有文化,吃了不少苦头,他们还不以为然。如一个不识文化的人,一次上街买肥料,把猪税票当作肥料票;又一个用除草剂当农药使用,结果是几亩秧苗死掉了,教训十分深刻。
可是,彭长贵要招生办学的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管难度多大彭长贵就是初衷不改,信念不移。
机会终于来了。
1964年2月29日,莲花学区书记田力召集全区5个公社(大元、莲花、海洋、里仁、大元)的有文化而又愿意教书的人到学区开会,向他们宣传介绍了外地办耕读学校(后改称民办学校)的情况和经验,发动和鼓励与会人员回到各地依靠党的好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文化教育的翻身仗。
县教育局财会股还派杨胜冲到莲花学区主持总务工作,给各耕读学校发放纸张、粉笔等教学必需品。
会议期间,彭长贵巧遇了老同学龚泽龙。龚泽龙对他说:“我每天划一个船到对面的梨坪教耕读班,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不搞这个搞什么?学来的知识不用,未必拿去沤大粪?”彭长贵听后非常激动,更加坚定了办学的决心。
回到飞山的当晚,正好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彭长贵便高高兴兴的向社员群众传达了学区会议精神。彭长贵话音刚落,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立即电光石火,短兵相接。
第一个发表火爆意见的,是一队最高掌权人——队长姚明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姚明武有着根深蒂固的世袭眼光,对彭长贵当会计一事他就心生嫉妒,此时看到彭长贵又要招生办学,更是妒火中烧。在姚明武眼中,彭长贵只是一个残废,他只应该低人一等,不做讨米叫花,也是碌碌无为,怎么他反而比我还神气,还快活?不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比同等劳力还要多拿15%的工分,每月还有6元津贴,太便宜他了;有我姚明武在,就决不能让彭长贵办学教书。
想到此,只见姚明武红眉毛绿眼睛嗓子粗大,恶狠狠怒冲冲咬紧黄牙,声音洪亮,秽语污言,唾沫直溅:“喂羊子也能吃屎,何必喂狗?公办教师也教得不怎么样,你彭长贵能行吗?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彭长贵一心只想吃活乐食,你还宣传什么加15%工分,那么容易?我讲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硬是痴心妄想!你宣传的东西到别处去恐怕也行不通,到我这里更行不通。你要办学?我不答应,我不让大家送子女来。你如果实在要教书也只能拿妇女工分的一半,就是一天四分,怎么样?你干不干?你还想不想教书?”
彭长贵的回答很干脆、斩钉截铁,简直是寸步不让、义无反顾:“我干,我愿意,一个工分都可以不要,但这书我是教定了。只要我教会孩子们识字,有了文化,他们这一代不再像祖祖辈辈一样当睁眼瞎,我想学生家长会支持我的,他们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虽然会场上没有发出掌声,但是彭长贵的城实和决心、真言和真情,打动了大家的心。
会场沉静一会儿,姚明武满脸得意。
可是,姚明武万万没有想到――沉静之后是沸腾。
人民需要文化,山区需要文化,孩子们需要文化。
大队支书吴景富、副大队长张贵华和另外一些干部和群众都站在彭长贵一边,坚决支持招生办学。
这时老农民吴明亮站了起来,大声吼道:“没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生活。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队,彭长贵来我队以前,我队所有分配没兴记账,不搞找补,实在不公平,不像话,决算前出生的小孩分不到口粮,这太不合理了!婴儿出生后赶到小春分小春,赶到大春分大春,赶不到就分不到,分不到就吃不成,没搞决算和找补,我们心里没底,一塌糊涂。由于分配不公,社员们胀的胀死,饿的饿死,大家会忘记吗?没有文化的苦头我们吃够了,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文化,那可不行,彭长贵办学是积德,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
只要有人站了出来,心里早就想说话的大部分社员说话了,生产队长不给彭长贵记工分不怕,我们私人给彭长贵称口粮,还凑钱,比工分管用。不论怎样,生产队长不支持,我们社员支持, 一定要把我们的学校办起来。
眼看支持彭长贵的人占了上风,姚明武就像泄气的皮球,虽然他很不甘心,但在众多支持办学的人面前,无可奈何,不敢再说反对和拆台的话了。
会议趋向平静,经过大家讨论,最后作出决定,每年给彭长贵的报酬是700斤粗粮,70元钱,分别由招生范围的3个生产队按人口平均分摊,粮出称粮、油出称油。
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3月1日,张贵华的女儿张鲜花、吴明亮的女儿吴显菊、李元章的儿子李顺富等20多个孩子都来上学了。
耕读学校初办时,大孩子能就近照顾小弟小妹,也能帮助大人做家务,因此学校就分下午班和上午班,一、二队学生为上午班,在飞山上课,三队的16个学生为下午班,在新寨上课。
再丰大队地处天龙山脚,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边远、贫穷,又没有文化,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赶集要到f省天龙县土茶镇,去来要走80多里山路,山路崎岖很是难走,不论去来都要身负100多斤重担。
彭长贵上课的条件也很艰苦,从飞山到新寨,其间相距3里多路,羊肠小道,弯弯拐拐,彭长贵每天要来回走两次,其工作之艰苦可想而知。
但是,彭长贵不仅不叫苦,还高兴有余。
彭长贵不认为自己有多能干,他深知只有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才能使广大社员群众走向进步、文明和幸福,自己只是享受幸福的一员。再丰大队耕读学校的建立,并非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上级和大队党支部、管委会和广大社员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他决心在教育事业上做出成绩来回报党和人民。
几年来盼啊盼啊,盼的就是这一天,他怎么能不努力呢?
他每天9—12点在飞山教上午课;中午从飞山往新寨走,算是“休息”了一会;12点半—16点半在新寨教下午课。上午班和下午班都是(一、二年级)复式班,彭长贵上课,一天喊个不停,每天下午嗓子就沙哑,最严重的时候嗓子大量出血。后来学生大一点,有时他让尖子生当“小先生”替他一阵,放学后吃了一些保护嗓子的药,嗓子才渐渐好起来。
晚饭后,他又走3里路到新寨,与大队团支部书记张贵友一起组织团员、青年排节目,搞业余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彭长贵当导演,必须每晚到场,有时搞到半夜,彭长贵一个人要走3里多的夜路回家。他们为了宣传党的政策,经常到各生产小组演出,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的。
当然,他每天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教书工作上。他一天跑上跑下,忙里忙外,辛勤的耕耘开始有了收获。
耕读学校的学生,年龄都有在十岁左右,年龄小的相对较少,因此,学生学得快,才学两个多月,尖子生如张鲜花、吴显菊、李顺富、李长生、张贵万等人,就可以拿起话筒和稿子喊广播了,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出了贡献,成为名符其实的宣传员。
听了学生的广播,家长乐了:彭长贵有本事,孩子们有出息!
听了学生的广播,彭长贵更是高兴得热泪盈眶。
新寨学生张贵万力气大,脾气好,每天背三个小妹妹上学,不仅能取得好成绩,而且还经常帮家里做很多农活,因此,全村人对彭长贵和他的学校都刮目相看了。
正当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谁知又有一股冷风吹来。
吹冷风的还是再丰一队队长姚明武,他手上有权,说话最具煽动性:“你们看,彭长贵9点钟上课,下午4点半就放学,我们呢?天一亮就上坡,天黑才收工,累得要死;他玩得要死还不算,每天还要多加15%的工分,我们划得来吗?以后,你们不送小孩上学,他就快活不起来了。那么多公办教师都没教出几个好学生来,他还搞得出什么名堂来?”
他的毒计确实起到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天就有3个学生没来上课了;第三天又有5个学生没到校了。彭老师一问学生,才知道真相:“我们队长说:‘我已经决定了,不给彭长贵称粮食;谁去读书,谁家就给他称粮食。’所以我们就不敢来读书了。”
如此下去,不要几天时间,学生就会都不来上课了。
眼看学校难保,彭长贵心急如焚,立即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到莲花,向学区领导汇报。学区书记田力看信后,立即来到再丰大队。他找到大队干部和有关生产队干部,教育他们充分认识办学的重要性,劝告他们一定要重视教育事业:只有这样,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才能改变。田力又讲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很多农村人进城,由于没有文化,说一句不怕笑人的话,尿胀了连厕所都找不到。”接着大队支书吴景富说:“我们的学校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上午班和下午班要合并,耕读学校要办成全日制民办小学。”
辍学的学生都回校读书了,新寨的下午班所有学生来到飞山,上午班与下午班合成了全日制。对学习进步很大的学生,立即设立五年级。飞山民办小学有了三级复式班,三级复式一直持续到1976年春期。
姚明武再次失败了,但是他思想还顽固得非同一般。当年收割季节,眼看分配在即,劳动果实要被彭长贵分走一些,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再搞阴谋活动:“你们看,我们打谷子,汗水满脸满身都是,裤子都湿尽了,彭长贵却在那里和学生丢帕帕,你们看得过意吗?”,原来动摇过的学生家长再次被说动了,又不让子女上学了。
好事多磨。这一磨,却磨出了几首诗来,水平虽然不高,但可抒情励志
粉笔
没有宏大的称号,没有珠宝的闪光。
纯真的灵魂洁白无瑕,
智慧的凝聚言行高尚。
没有雷人的高调,没有喧哗的吵嚷。
沙沙的细语默默润物,
清清的泉水微澜小唱。
没有一己的私利,没有个人的奢望。
奔月的飞船由她链接,
未来的大门是她叩响。
没有灿烂的桂冠,没有华丽的外装。
既是朴实无华的象征,
又是宁折不弯的榜样。
黑土地
从包公脸上刮来的颜色
你信吗
——盘缠,路费。(小王插话:“明明是包谷粑,怎么又成了路费?)
——(随和地)安步当车嘛!路费,路粮,都差不多,都重要。小王,不要门缝里瞧人。(笑着对小伙子说)你自有你的道理,对不对?
——对!(从脸上和话声里读出了对面这个中年人的和蔼、慈祥、诙谐语言中深邃的含意,又仔细打量一下)你……(努力回忆)好像……你是县委罗书记吧?
——我正是罗之英,你眼力不错,你叫什么名字?
——冉海洋。
——(若有所思)你就是那个模范共青团员冉海洋吧?
——算不上什么模范,这是上级和组织的信任。
——你背这一背“路费”到哪里去?
——上学。
——龙潭中学毕业的?
——是。
——上哪个大学?
——清华。
一字千钧,份量够重!“清华”两字击在县委书记心坎上,“格登”一下,不禁一颤,他脸上顿时严肃起来。
冉、王二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双双愣在当地。
罗之英在黑水区检查了工作,还准备到丁市区去,现在改变了注意:先解冉海洋的燃眉之急再说。
冉、王二人还在捉摸呢,就听到罗之英极为严肃认真地说:“冉海洋同学,上车吧!我把你的‘盘缠’强买了。今天,最迟明天,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给你一个妥贴之计。”
小轿车向古城县城飞奔。
当天下午,县委、县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县委各部委、县人委各科室的同志,都来到了古城县大礼堂。
大家看着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县委书记身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青年,罗之英和青年面前,放着满满一背包谷粑。人们对此大惑不解:这个粑粑客“厉害”到家了,卖包谷粑卖到“老爷大堂”上来了!
人们七嘴八舌,纷纷议论,都想解破这个奇特的谜语。
会议开始。第一个议程:吃包谷粑,由县委书记亲自发放,一人一个,未领到的就继续“猜谜”。
吃包谷粑的,“猜谜的”,个个傻了眼!今天遇到了特别的人物、特别的事情、特别的场景,感受着特别的氛围。
一位“眼镜”品尝得最细,吃一口,嚼一阵,觉得合口,还真想再吃一个。
待大家吃完了神秘的“特餐”,县委书记罗之英发话了:“同志们,包谷粑味道如何?”
“好吃,好吃,又香又甜!”一片赞扬声,又一齐把欲知下文的目光投向县委书记和那青年。
冉海洋从容自若,并不惊慌。
“眼镜”最后一个吃完,用手巾擦擦手,一边“抛”出“文”来:“此粑粑味纯而美,惟不知价值几何?”
会场里哄堂大笑。
罗之英没有笑,也没有责怪“眼镜”,而是以包谷粑为“引子”,徐徐入题地演说起来:“同志们,这包谷粑价值几何呢?可以说它不值几个钱,也可以说它价值无限。说它价值无限,因为这是古城人民对我们的鞭策和教育!(把冉海洋拉在身边,激动地,对着县团委书记吴青问,然后又自问自答)你不认识他吗?应该说你认识他。同志们,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青年,不是粑粑客,他就是县团委去年表彰的那个模范共青团员冉海洋,就是到旋涡潭抢救两个落水儿童的青年英雄。(此时,听众情绪激昂,“眼镜”也从眼镜里射出敬佩的光)冉海洋同学德才兼备,考上了中国的第一名牌——清华大学。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这是我们古城人民的骄傲!话又说回来,古城已经解放十多年了,我们为人民清除了匪患,清除了一些旧风俗,但我们却没有清除贫穷。我们的责任没尽到,我们是不称职的。冉海洋考取清华大学,他的父母无法给他拿路费、生活费。大热天,包谷粑很快就会臭馊的,吃了不生病才怪!这些责任我第一个该负,我们大家都应承担!我们宁愿节衣缩食,也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冉海洋同学穿着草鞋、背着臭馊的包谷粑上北京!那将是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耻辱!”
全场哗然,唏嘘叹息之声不绝于耳。
语惊四座,人人心里卷起阵阵风暴。
难忘的一幕,深深地烙进了冉海洋的心灵。
罗之英继续说:“同志们,静一静。现在我郑重提议,每人给冉海洋同学献上一份爱心。”他率先拿出200元,郑重地放进了敞口“募捐箱”——冉海洋的包谷粑背篼。人们接着纷纷解囊,50元、20元、10元……面额不等的人民币都进了背篼。
除了上街,“眼镜”从来不爱带钱在身上,此时便掏出他心爱的金壳怀表递给冉海洋。冉海洋认为是奢侈品,坚持不要。经罗之英从旁帮着劝说再三,冉海洋才勉强收下。
特殊会议结束之时,冉海洋捧着古城人民赤诚的爱,热泪盈眶,泣声带颤:“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为——为古城人民——争光!”
路费、生活费,总起来已超过三千之数。由于与会者把这个激动人心的信息到处传开,又有不少人找到县委招待所冉海洋的临时住处,把一份份爱心和鼓励,交给了冉海洋。
当晚,冉海洋以无限欣慰的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县委书记和县上领导为他解决了路费、生活费问题,好让父母放心。
翌日早晨,朝阳刚刚升起,司机小王遵照罗之英的吩咐,把冉海洋送到县车站,并递给他一张船票:“这张船票是给你送金壳表那位‘眼镜’,也就是县委办公室杨主任几天前为他表妹预订的。客车到龚滩,从龚滩坐船下涪陵,然后直下武汉就可以坐火车了。”“那他的表妹呢?”“她是武汉歌舞团的一个编剧,昨晚听杨主任讲了你的故事,声言船票无偿转让,并要到你家乡去熟悉生活,去看望你的父母,然后编个什么歌舞之类,我就说不圆范了。”
冉海洋别了司机小王师傅,登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徐徐启动,他耳畔还响着罗之英的演说,脑际还回味着捐资的场景。他深情地回望古城山川:故乡啊亲人,亲人啊故乡,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我一定要用最好的成绩向你们报喜!
尾声:
冉海洋巧遇县委书记罗之英,罗书记动员县委、县人委机关所有干部职工为他化缘,“买”下了他的一背包谷粑,他才有钱乘车到北京。这份情,这份爱,冉海洋不仅铭记了一生,还以此教育子侄辈。
文化大革命中,罗之英在古城备受冲击,有一派群众组织甚至扬言要将他置于死地。在国务院工作的冉海洋从父母的家书中得知这一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此事。有关领导采纳了冉海洋的建议,把罗之英调到了北京。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国家日益昌盛、富裕,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也吹响了。可是冉海洋的家乡,贺龙元帅当年开创川鄂湘黔根据地的地方,难与沿海地区相比,这几十年来一直变化不大。他儿子冉恩的姑姑、姑父,舅舅、舅娘,一个个血老表、姨老表,凡未参加工作的,都还头戴贫困帽子,身处贫困环境。冉海洋一家的周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冉恩大学一毕业,就赞同父亲的提议,将攻读硕士研究生从脱产改为函授,到渝东南家乡去当村官,因为c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是统筹城乡的试点,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冉恩的想法,就是要闯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子,也代父亲报答古城故土乡亲的恩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有了罗书记的捐助,才解决了他父亲上大学缺路费与生活费的问题,正因为这份爱,才让爱得以延续。这份情意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永世难忘。西部大开发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开发的大潮中,古城这个地方终究有一天会摆脱现状的。
三、艰辛求学路
彭长贵考上了祥云县第一中学后,只身到校报名。校长叶伊理听说彭长贵家非常困难,学杂费交不起,就让彭长贵回家把母亲接来,给叶校长家当保姆。16岁的彭长贵头天进城,第二天回家,每天步行130多里,一路苦,两头黑,母亲听说后,非常感动,但有点不敢相信。没有办法,彭长贵又往城里走去。叶校长给彭母写了一封短信。彭长贵就这样往返几趟,终于把事情办好,可以进校读书了。
救了蛤蟆死了蛇。母亲冉凤英带着儿子离开大元乡政府机关时,还清所有欠账,已经所剩无几了。
如果不是叶校长拉了一把,真不知要想什么办法才好。但是,她半点也不后悔:外甥冉海洋有了出头之日;儿子呢,螺蛳屙屎有出处;又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母坚强,儿坚强,彭长贵一边读书,一边向老师和其他人打听:“像我这样又瞎又麻的人读书有用吗?”问了一次又一次,谁也无法答复他。
但是,母亲总是鼓励着他,支撑着他,他也很努力。母子俩都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三年初中读下来,祥云一中出了有名的“大元三学子”:60级1班第一名白云中,大元公社鱼塘溪人;60级2班第一名方长印,班长兼班团支部副书记,大元公社邱窠土人;60级2班第二名彭长贵,班团支部书记。
当然,那两位同学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他们被保送到本校高中部学习;但又麻又瞎的彭长贵就没那么幸运了,眼睛残疾决定了他不能升学、不能考干、不能进厂当工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啊!
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师毕业生里的中共党员可以进入高等师范院校读书,虽然特别不容易,但彭长贵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还好,他被保送到祥云师范学校就读了。作为团员考生,他优先得到了录取通知书。
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后,母亲第一句话就是:“我到师范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积极参加团组织工作,争取尽快入党,争取保送到高等师范院校学习,将来我要当个好教师,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母亲很支持他:“行,就这样办吧!”
祥云师范学校坐落在祥云县城南部怀龙镇, 地处梅江河南岸。
1960年9月,彭长贵荣幸地进入祥云师范学校读书。从进校学习的第一天起,彭长贵就准备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无比壮丽的人民教育事业。
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他珍惜每分每秒,显示了超乎常人的刻苦。理想激励着他,他时时憧憬着当一名教师。他很少休息,一直信心满怀而执著地学习每一门课程,还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团组织生活。作为校团委宣传委员,他更感到搞好业余文艺宣传活动是他的本份,责无旁贷。
校舍的简陋,他竟然视而不见;自己的残疾,此时也毫不在乎了。谁知未来的日子,他却经历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和坎坷,一圈又一圈曲折,一重又一重难关。大气候、历史、地理、自然种种因素,都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进程,都制约着重每个人的人生。
但是,彭长贵深知事在人为,地在人耕,他把表哥冉海洋作为榜样,以钢铁和信念,以大半生的自强拼搏、努力奋斗,最终实现了自已的理想和抱负。虽然他54岁才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是并不觉得委屈,并不觉得这好事姗姗来迟,并不觉得有任何后悔,因为他把大半生心血都毫不保留地献给了伟大的党和人民,因而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家乡和祖国。
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及农村教育的状况,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那是被左倾理想搅拌的年月,都搅拌成什么样了呢?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全国有7千万人口死于饥饿。党中央为了力挽狂澜,发出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祥云师范不得不停办,同学们慷慨而激昂。彭长贵和其他几个同学在当晚学校召开的毕业晚会上,登上了主席台向全体师生大表而特表决心: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大有作为,我们要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当中去锻炼自己,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彭长贵在讲台上,用非常激动的语言向党和人民、向祖国表决心:“我要到农村去书写最好最好的文章,画最美最美的图画,谱写最美最美的乐章,同学们,大家在劳模会上再见吧!”
飞山明烛第二章顽强的拉锯战
彭长贵回到力大坳老家,所见到的一切与他想象的简直有天壤之别:自家的阶沿都被别人种菜了,房子因多年失修,现已变成了生产队的牛圈,天通地漏,屋内所有的动用家私已不存在。生产队说要给他家退赔,彭长贵知道那只是口头上说说,行动上不知要等上多少年,目前到哪里去住呢?没有办法,母子俩只有投奔秋窠土姐姐家居住。
一天,彭长贵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来了衣帽非常破旧的两个中年人,开口就问“你就是彭长贵吧?听说你是一大知识分子,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居住好吗?”原来二位中年人,一个是再丰大队副大队长张贵华;一个是复员军人张兴富。
彭长贵好生奇怪:“难道说你们那里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如果有,我今天就不用来了。这两年,我们队连一个记分员都没有,实在没有办法分粮食就只好拿家私印,一年生产多少粮食,交多少公粮,留多少种子,大家分多少口粮都不知道。”在二位的一再请求下,彭长贵一家从此由秋窠土迁往飞山居住。由于再丰大队有文化的人实在太少,彭长贵不但担任飞山生产队会计,还担任了再丰大队会计、第二生产队会计,另外又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
那时贫困落后的穷山沟,吃饭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饥饿和疾病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他们连做梦也不敢想办学读书的事,彭长贵却深深地知道要想改变如此贫穷落后的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大山里的人识文断字,同时彭长贵也清楚地知道要想在这里办学,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绝大部分人是不会支持的,因为他们对办学的好处根本不理解。彭长贵天生犟脾气――再难也要办,没有其它选择。
彭长贵所担任的三份会计工作本身就是很难做的了,部分社员对国家的分配政策不了解,对按工分、人口、肥料比例分配的方式不理解,大吵大闹的大有人在。彭长贵算账时,一些不能上坡干活的老头就围在彭长贵周围,监督他做账,生怕他做账不公。但时间一长,大家就信任彭长贵了,总觉得比他们原来的用家私量要简单和准确得多了。
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原生产队长姚明武眼看他扶持上阵的几位亲信败下阵来,自己捞不到油水了,就千方百计在背后大搞阴诡计,想方设法要把彭长贵排挤掉。
小春预算、大春预算,姚明武眼看彭长贵在一、二、三、四队走来走去,他一脑壳火冒,歪起嘴巴说彭长贵是游山玩水,专混大队报酬,其实彭长贵既要给大队和一二三四队算账,又要去三队、四队辅导会计业务,到一个队或两天或三天不等。姚明武什么也不懂,总觉得彭长贵是懒惰,他说:“火热的大太阳天,我们在坡上晒,他在家里享福,太便宜他了。”
更有甚者,姚明武一遇到公社干部或县、区工作队的干部,就要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以泄私愤;姚明武多次采取同一个办法:“某同志,我们队上会计不见了,我已经登寻人启示了,你们要是在哪里看到彭长贵,就把他带到我们生产队来。”
由于“寻人启示”多次登载,干部们已司空见惯,都懒得理他了。干部们又知道彭长贵是在干正常业务,谁也不去责怪彭长贵。
后来姚明武一登“寻人启示”对方就立即反唇相讥:“你的寻人启示都登到省里去了,文章做大啦!”由于姚明武做事不是出于公心,受到众人的反对,最后他就不再登“寻人启示”了。
飞山人没有文化的难处,彭长贵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而飞山人却身处困境而不觉,反而觉得习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祖祖辈辈不都有这样过来了吗?彭长贵提出办学的事,,姚明武等人一唱一合,振振有词,唾沫乱飞,说得头头是道:只要肯劳动就有饭吃,读书有什么用,书能当饭吃吗?
飞山人由于没有文化,吃了不少苦头,他们还不以为然。如一个不识文化的人,一次上街买肥料,把猪税票当作肥料票;又一个用除草剂当农药使用,结果是几亩秧苗死掉了,教训十分深刻。
可是,彭长贵要招生办学的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管难度多大彭长贵就是初衷不改,信念不移。
机会终于来了。
1964年2月29日,莲花学区书记田力召集全区5个公社(大元、莲花、海洋、里仁、大元)的有文化而又愿意教书的人到学区开会,向他们宣传介绍了外地办耕读学校(后改称民办学校)的情况和经验,发动和鼓励与会人员回到各地依靠党的好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文化教育的翻身仗。
县教育局财会股还派杨胜冲到莲花学区主持总务工作,给各耕读学校发放纸张、粉笔等教学必需品。
会议期间,彭长贵巧遇了老同学龚泽龙。龚泽龙对他说:“我每天划一个船到对面的梨坪教耕读班,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不搞这个搞什么?学来的知识不用,未必拿去沤大粪?”彭长贵听后非常激动,更加坚定了办学的决心。
回到飞山的当晚,正好召开生产队社员大会,彭长贵便高高兴兴的向社员群众传达了学区会议精神。彭长贵话音刚落,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立即电光石火,短兵相接。
第一个发表火爆意见的,是一队最高掌权人——队长姚明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姚明武有着根深蒂固的世袭眼光,对彭长贵当会计一事他就心生嫉妒,此时看到彭长贵又要招生办学,更是妒火中烧。在姚明武眼中,彭长贵只是一个残废,他只应该低人一等,不做讨米叫花,也是碌碌无为,怎么他反而比我还神气,还快活?不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比同等劳力还要多拿15%的工分,每月还有6元津贴,太便宜他了;有我姚明武在,就决不能让彭长贵办学教书。
想到此,只见姚明武红眉毛绿眼睛嗓子粗大,恶狠狠怒冲冲咬紧黄牙,声音洪亮,秽语污言,唾沫直溅:“喂羊子也能吃屎,何必喂狗?公办教师也教得不怎么样,你彭长贵能行吗?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彭长贵一心只想吃活乐食,你还宣传什么加15%工分,那么容易?我讲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硬是痴心妄想!你宣传的东西到别处去恐怕也行不通,到我这里更行不通。你要办学?我不答应,我不让大家送子女来。你如果实在要教书也只能拿妇女工分的一半,就是一天四分,怎么样?你干不干?你还想不想教书?”
彭长贵的回答很干脆、斩钉截铁,简直是寸步不让、义无反顾:“我干,我愿意,一个工分都可以不要,但这书我是教定了。只要我教会孩子们识字,有了文化,他们这一代不再像祖祖辈辈一样当睁眼瞎,我想学生家长会支持我的,他们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虽然会场上没有发出掌声,但是彭长贵的城实和决心、真言和真情,打动了大家的心。
会场沉静一会儿,姚明武满脸得意。
可是,姚明武万万没有想到――沉静之后是沸腾。
人民需要文化,山区需要文化,孩子们需要文化。
大队支书吴景富、副大队长张贵华和另外一些干部和群众都站在彭长贵一边,坚决支持招生办学。
这时老农民吴明亮站了起来,大声吼道:“没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生活。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队,彭长贵来我队以前,我队所有分配没兴记账,不搞找补,实在不公平,不像话,决算前出生的小孩分不到口粮,这太不合理了!婴儿出生后赶到小春分小春,赶到大春分大春,赶不到就分不到,分不到就吃不成,没搞决算和找补,我们心里没底,一塌糊涂。由于分配不公,社员们胀的胀死,饿的饿死,大家会忘记吗?没有文化的苦头我们吃够了,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文化,那可不行,彭长贵办学是积德,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
只要有人站了出来,心里早就想说话的大部分社员说话了,生产队长不给彭长贵记工分不怕,我们私人给彭长贵称口粮,还凑钱,比工分管用。不论怎样,生产队长不支持,我们社员支持, 一定要把我们的学校办起来。
眼看支持彭长贵的人占了上风,姚明武就像泄气的皮球,虽然他很不甘心,但在众多支持办学的人面前,无可奈何,不敢再说反对和拆台的话了。
会议趋向平静,经过大家讨论,最后作出决定,每年给彭长贵的报酬是700斤粗粮,70元钱,分别由招生范围的3个生产队按人口平均分摊,粮出称粮、油出称油。
第二天,也就是1964年3月1日,张贵华的女儿张鲜花、吴明亮的女儿吴显菊、李元章的儿子李顺富等20多个孩子都来上学了。
耕读学校初办时,大孩子能就近照顾小弟小妹,也能帮助大人做家务,因此学校就分下午班和上午班,一、二队学生为上午班,在飞山上课,三队的16个学生为下午班,在新寨上课。
再丰大队地处天龙山脚,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边远、贫穷,又没有文化,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赶集要到f省天龙县土茶镇,去来要走80多里山路,山路崎岖很是难走,不论去来都要身负100多斤重担。
彭长贵上课的条件也很艰苦,从飞山到新寨,其间相距3里多路,羊肠小道,弯弯拐拐,彭长贵每天要来回走两次,其工作之艰苦可想而知。
但是,彭长贵不仅不叫苦,还高兴有余。
彭长贵不认为自己有多能干,他深知只有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才能使广大社员群众走向进步、文明和幸福,自己只是享受幸福的一员。再丰大队耕读学校的建立,并非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上级和大队党支部、管委会和广大社员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他决心在教育事业上做出成绩来回报党和人民。
几年来盼啊盼啊,盼的就是这一天,他怎么能不努力呢?
他每天9—12点在飞山教上午课;中午从飞山往新寨走,算是“休息”了一会;12点半—16点半在新寨教下午课。上午班和下午班都是(一、二年级)复式班,彭长贵上课,一天喊个不停,每天下午嗓子就沙哑,最严重的时候嗓子大量出血。后来学生大一点,有时他让尖子生当“小先生”替他一阵,放学后吃了一些保护嗓子的药,嗓子才渐渐好起来。
晚饭后,他又走3里路到新寨,与大队团支部书记张贵友一起组织团员、青年排节目,搞业余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彭长贵当导演,必须每晚到场,有时搞到半夜,彭长贵一个人要走3里多的夜路回家。他们为了宣传党的政策,经常到各生产小组演出,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的。
当然,他每天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教书工作上。他一天跑上跑下,忙里忙外,辛勤的耕耘开始有了收获。
耕读学校的学生,年龄都有在十岁左右,年龄小的相对较少,因此,学生学得快,才学两个多月,尖子生如张鲜花、吴显菊、李顺富、李长生、张贵万等人,就可以拿起话筒和稿子喊广播了,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出了贡献,成为名符其实的宣传员。
听了学生的广播,家长乐了:彭长贵有本事,孩子们有出息!
听了学生的广播,彭长贵更是高兴得热泪盈眶。
新寨学生张贵万力气大,脾气好,每天背三个小妹妹上学,不仅能取得好成绩,而且还经常帮家里做很多农活,因此,全村人对彭长贵和他的学校都刮目相看了。
正当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谁知又有一股冷风吹来。
吹冷风的还是再丰一队队长姚明武,他手上有权,说话最具煽动性:“你们看,彭长贵9点钟上课,下午4点半就放学,我们呢?天一亮就上坡,天黑才收工,累得要死;他玩得要死还不算,每天还要多加15%的工分,我们划得来吗?以后,你们不送小孩上学,他就快活不起来了。那么多公办教师都没教出几个好学生来,他还搞得出什么名堂来?”
他的毒计确实起到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二天就有3个学生没来上课了;第三天又有5个学生没到校了。彭老师一问学生,才知道真相:“我们队长说:‘我已经决定了,不给彭长贵称粮食;谁去读书,谁家就给他称粮食。’所以我们就不敢来读书了。”
如此下去,不要几天时间,学生就会都不来上课了。
眼看学校难保,彭长贵心急如焚,立即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到莲花,向学区领导汇报。学区书记田力看信后,立即来到再丰大队。他找到大队干部和有关生产队干部,教育他们充分认识办学的重要性,劝告他们一定要重视教育事业:只有这样,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才能改变。田力又讲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很多农村人进城,由于没有文化,说一句不怕笑人的话,尿胀了连厕所都找不到。”接着大队支书吴景富说:“我们的学校不但要办,而且要办好。上午班和下午班要合并,耕读学校要办成全日制民办小学。”
辍学的学生都回校读书了,新寨的下午班所有学生来到飞山,上午班与下午班合成了全日制。对学习进步很大的学生,立即设立五年级。飞山民办小学有了三级复式班,三级复式一直持续到1976年春期。
姚明武再次失败了,但是他思想还顽固得非同一般。当年收割季节,眼看分配在即,劳动果实要被彭长贵分走一些,心里很不舒服,于是再搞阴谋活动:“你们看,我们打谷子,汗水满脸满身都是,裤子都湿尽了,彭长贵却在那里和学生丢帕帕,你们看得过意吗?”,原来动摇过的学生家长再次被说动了,又不让子女上学了。
好事多磨。这一磨,却磨出了几首诗来,水平虽然不高,但可抒情励志
粉笔
没有宏大的称号,没有珠宝的闪光。
纯真的灵魂洁白无瑕,
智慧的凝聚言行高尚。
没有雷人的高调,没有喧哗的吵嚷。
沙沙的细语默默润物,
清清的泉水微澜小唱。
没有一己的私利,没有个人的奢望。
奔月的飞船由她链接,
未来的大门是她叩响。
没有灿烂的桂冠,没有华丽的外装。
既是朴实无华的象征,
又是宁折不弯的榜样。
黑土地
从包公脸上刮来的颜色
你信吗
到头了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