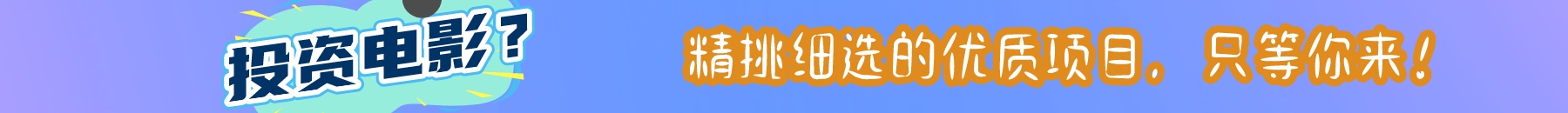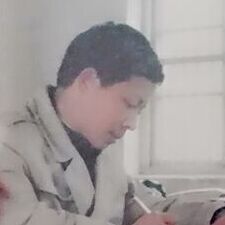权属:原创 · 独家授权
字数:2898
阅读:2116
发表:2022/4/27 修改:2023/9/24
180章 历史 小说
《荆公为政》第33章:高雅的愤怒
1-2
…
32
33
34
…
180
全部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第33章 高雅的愤怒
一个休假日,荆公正在家为选拔不到理想的变法班子成员感到焦虑,都知蓝天震来了,说有宗杀人案定谳时,大理寺和审刑院与登州的知府各执一词,无法决断,皇上诏翰林学士院司马光、王安石两位政治最敏感的学士拿出处理意见,以供圣裁参考。
此案荆公早已听说。
登州有位孤苦伶仃的少女阿云,这年十三岁,正在家为母守孝,不料她的叔父贪图钱财,竟以几石麦子将其卖给一位叫韦大的光棍为妻。韦大不仅大阿云三十多岁,更是容貌丑陋,阿云对这门亲事死活不肯接受,可又拗不过叔父,于是阿云趁成婚之夜,拿柴刀对着熟睡的韦大一阵乱砍,被惊醒的阿韦大惊醒,但仍被砍掉一个指头。
韦大报了官。
知县接到报案,立即将阿云捉拿。阿云毫无隐瞒地将事情经过交待清楚。招供后,知县以谋杀亲夫罪判处阿云死刑。
宋朝律法规定,地方判处死刑,案件须逐级上达,先是报到登州知府那里,知府许遵觉得此判决过重。
他认为:阿云许配韦大时尚处于母亲守孝期间,按照大宋律法规定,守孝期间的婚约无效;再者,阿云是被叔父逼婚,自己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因此这门亲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合法,既然婚约不合法,阿云就不是韦大的妻子,也就没有谋杀亲夫之罪一说;还有,案情的后果也不严重,韦大只是被砍断一根指头,并无大碍,阿云罪不至死。于是许遵签署了意见,将案子报送到大理寺和审刑院。
大理寺与审刑院审核后认为,即便阿云不是韦大的妻子,但是其蓄意谋杀,并且造成了对方人身伤害;按照大宋律令,母亲丧葬期间出嫁,更应罪加一等。纵上两条,阿云已属十恶不赦,应判处立斩。
翰林学士本为皇上的智囊。荆公接到诏令,得知皇上要听听他与司马学士对此案的意见,机灵一动,便想借机去会会好友司马光,此一是为商谈此案的处理办法,二是借机向那次在经筵上被气走的好友作个解释,三要与好友司马光探讨组建变法班子一事。想妥后,荆公也不换装,仍是穿着那身灰袍,带着石子,乘着马车去了司马府上,一打听,说司马大人出门去了。
荆公问去了哪里?家人说老爷与几位好友去酒楼吃茶去了。
荆公问:“在哪吃茶?”
家人说:“在潘楼东街北山茶坊。”
荆公谢过,乘车赶了过去。
此时,吕公著、韩维、吕诲、苏轼等几位好友正在北山茶坊请司马学士品茶。
在几位好友的心目中,司马光简直就是他们道德文章中的一面大纛,那天在经筵上见司马光被吕惠卿一番讥刺而愤然离去后,他们无不为司马受辱担忧,担忧这位方直清名的司马如何承受得了?于是便凑到一处商量,约定这个休假日邀请司马君实到茶楼吃茶谈心,借此消除他的愤懑之气。
北宋是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朝代,尽管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但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文人雅士,甚或达官显贵,他们的生活节奏始终是不紧不慢,悠哉游哉,不仅过得恬适舒惬,更是在恬适舒惬中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求那些足可以使人感觉无比悠闲与高雅的情调。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吃茶。那时的吃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吃”字便可了结,更是在吃的过程中派生出五花八门的茶艺茶技,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选个僻静、典雅的茶楼阁子间去点茶斗茶,在点茶斗茶过程中,享受着他们需要寻求的那种由茶而自然生成的情趣与雅兴。
北山茶坊在繁华的潘楼东街,此茶楼有仙洞.仙桥,小桥流水,苍树翠竹,于喧嚣中隐含着幽静,繁华中充斥着典雅。大凡以点茶、斗茶取乐的文人雅士无不欢喜来这儿聊天品茶。这天,吕公著、韩维、吕诲、苏轼几人,各自带上最好的茶饼来到这里,选了一间窗临溪水、绿树拱绕的雅间,为博得好友司马公的高兴,又特意叫了几位歌妓。
韩维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茶博士不仅熟识,更是知道他们的喜好,于是先将雅间四角的香炉打开,燃起昂贵的龙涎香,顷刻,满雅间香云氤氲,使人顿觉一种清醇、淡雅之气缓缓沁入心脾,漫游五脏六腑,令人神清气爽,舒惬无比。
韩维、苏轼几人宾至如归,或坐榻,或靠床,边嗅着那袅袅的龙涎香,边静静地等候。
这时,就听 “笃、笃、笃”三下不紧不慢的敲门声,众人已知谁来了。
开了门,就见司马公温文尔雅地抱拳施礼进来:“让各位久等了。”
靠在罗汉床上的吕公著笑着说道:“君实好大架子,让我们如此等候。”
坐在榻上的韩维说道:“君实不会还在为那天在经筵上的事生气吧?”
斜靠在罗汉床上的苏轼早已站起,深深施了一礼,问候道:“司马公近日心情还好否?”
坐在司马光对面的吕诲挪动了一下屁股,说道:“司马公胸襟豁达,哪会把那些小人的话记在心头。”
司马光拱手还礼道:“生气当然免不了,但听说众位好友邀光前来小聚,那气自是消了大半。”
韩维已将候在外面的歌妓请进。
那歌妓一个个霓裳广袖,貌美若仙,各就各位后,有的抚琴,有的弹瑟,琴瑟和鸣,悠扬动听,令人陶醉。
弹唱的词儿是黄庭坚的《满庭芳.茶》:
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五里名动京宫。碎骨粉身,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棒,研膏浅乳,金缕鹧鸪斑。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为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
听着听着,司马光想起苏轼吕诲刚才的问话,他也如歌中唱的“搜搅起胸中万卷怨恨的波澜”,于是愤然说道:“那气焰嚣张的吕吉甫,老夫可以不与他计较,只是那场合中透露出的信息,着实让光堪忧啊。”
此言一出,苏轼、吕诲几乎同时问道:“司马大人是指吕惠卿那厮说的变与不变之事?”
司马光道,“吕惠卿所说的‘变’,倒不必担忧。担忧的是,当吕惠卿说出此话时,皇上与那经筵官王介甫不仅不反感,更是频频点头,面露赞许之色,这倒是光极其担忧的。”
吕公著立马从罗汉床上坐起,说道:“君实这种担忧,晦叔深有同感。”
不等吕公著说完,吕诲、苏轼急问道:“司马大人说的是那变法之事?”
吕公著提盏抿了一口茶水,说道:“通过吕惠卿和皇上及介甫的谈话及神色,老夫已观察到,皇上所以要安排这次讲筵,就是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他要像仁宗朝那样,再来一场‘庆历新政’!”
这一说,大家更是吃惊,纷纷放下手中茶盏,纷纷想道:“如果真再来一次‘庆历新政’,那不仅是毁掉祖宗之法,更是要将一个好端端的太平盛世的大宋给折腾得鸡飞狗跳,毫无安宁之日?那还了得?”
想着,众人一齐把目光投向司马光,想听听他的主张。
与苏轼同坐一张罗汉床的司马光捋了捋疏朗的胡须,闪了一下凤眼,慢吞吞地叹了气,说道:“唉,这次光算是看错人喽。”
众人问:“司马公何出此言?”
司马光道:“光本以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可事实恰恰相反,要是那王介甫真的实行变法,大宋朝可又要大乱一阵喽。”
吕诲不解,问道:“司马大人,你不是也说过,这大宋弊端甚多,不变不行。现在那王介甫有意变法,你如何又担心了?”
侧卧着的苏轼“骨碌”坐起,愤然说道:“司马大人说的‘不变不行’,和王介甫要搞的变法决不是一码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接着说道,“从吕惠卿那番讲话及王介甫的神色中,子瞻已清楚地预感到,王介甫此次变法不变则已,如变,掀起的风暴远比‘庆历新政’更为厉害,更加强劲。司马公说的‘看错人了’,此言丝毫不虚!”
韩维本是借请司马光来吃茶,消消他的怨气,没想到几句话一说,反倒增添了众人的愤怒,想了想,站起提议道:“我们今天来是为过个轻松的休假日,诸位将茶饼拿出,我们边听曲儿边斗茶,以博个雅兴。莫谈政事,莫谈政事。”
说着,让歌女换了词曲,接着弹唱……
一个休假日,荆公正在家为选拔不到理想的变法班子成员感到焦虑,都知蓝天震来了,说有宗杀人案定谳时,大理寺和审刑院与登州的知府各执一词,无法决断,皇上诏翰林学士院司马光、王安石两位政治最敏感的学士拿出处理意见,以供圣裁参考。
此案荆公早已听说。
登州有位孤苦伶仃的少女阿云,这年十三岁,正在家为母守孝,不料她的叔父贪图钱财,竟以几石麦子将其卖给一位叫韦大的光棍为妻。韦大不仅大阿云三十多岁,更是容貌丑陋,阿云对这门亲事死活不肯接受,可又拗不过叔父,于是阿云趁成婚之夜,拿柴刀对着熟睡的韦大一阵乱砍,被惊醒的阿韦大惊醒,但仍被砍掉一个指头。
韦大报了官。
知县接到报案,立即将阿云捉拿。阿云毫无隐瞒地将事情经过交待清楚。招供后,知县以谋杀亲夫罪判处阿云死刑。
宋朝律法规定,地方判处死刑,案件须逐级上达,先是报到登州知府那里,知府许遵觉得此判决过重。
他认为:阿云许配韦大时尚处于母亲守孝期间,按照大宋律法规定,守孝期间的婚约无效;再者,阿云是被叔父逼婚,自己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因此这门亲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合法,既然婚约不合法,阿云就不是韦大的妻子,也就没有谋杀亲夫之罪一说;还有,案情的后果也不严重,韦大只是被砍断一根指头,并无大碍,阿云罪不至死。于是许遵签署了意见,将案子报送到大理寺和审刑院。
大理寺与审刑院审核后认为,即便阿云不是韦大的妻子,但是其蓄意谋杀,并且造成了对方人身伤害;按照大宋律令,母亲丧葬期间出嫁,更应罪加一等。纵上两条,阿云已属十恶不赦,应判处立斩。
翰林学士本为皇上的智囊。荆公接到诏令,得知皇上要听听他与司马学士对此案的意见,机灵一动,便想借机去会会好友司马光,此一是为商谈此案的处理办法,二是借机向那次在经筵上被气走的好友作个解释,三要与好友司马光探讨组建变法班子一事。想妥后,荆公也不换装,仍是穿着那身灰袍,带着石子,乘着马车去了司马府上,一打听,说司马大人出门去了。
荆公问去了哪里?家人说老爷与几位好友去酒楼吃茶去了。
荆公问:“在哪吃茶?”
家人说:“在潘楼东街北山茶坊。”
荆公谢过,乘车赶了过去。
此时,吕公著、韩维、吕诲、苏轼等几位好友正在北山茶坊请司马学士品茶。
在几位好友的心目中,司马光简直就是他们道德文章中的一面大纛,那天在经筵上见司马光被吕惠卿一番讥刺而愤然离去后,他们无不为司马受辱担忧,担忧这位方直清名的司马如何承受得了?于是便凑到一处商量,约定这个休假日邀请司马君实到茶楼吃茶谈心,借此消除他的愤懑之气。
北宋是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朝代,尽管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但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文人雅士,甚或达官显贵,他们的生活节奏始终是不紧不慢,悠哉游哉,不仅过得恬适舒惬,更是在恬适舒惬中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求那些足可以使人感觉无比悠闲与高雅的情调。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吃茶。那时的吃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吃”字便可了结,更是在吃的过程中派生出五花八门的茶艺茶技,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选个僻静、典雅的茶楼阁子间去点茶斗茶,在点茶斗茶过程中,享受着他们需要寻求的那种由茶而自然生成的情趣与雅兴。
北山茶坊在繁华的潘楼东街,此茶楼有仙洞.仙桥,小桥流水,苍树翠竹,于喧嚣中隐含着幽静,繁华中充斥着典雅。大凡以点茶、斗茶取乐的文人雅士无不欢喜来这儿聊天品茶。这天,吕公著、韩维、吕诲、苏轼几人,各自带上最好的茶饼来到这里,选了一间窗临溪水、绿树拱绕的雅间,为博得好友司马公的高兴,又特意叫了几位歌妓。
韩维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茶博士不仅熟识,更是知道他们的喜好,于是先将雅间四角的香炉打开,燃起昂贵的龙涎香,顷刻,满雅间香云氤氲,使人顿觉一种清醇、淡雅之气缓缓沁入心脾,漫游五脏六腑,令人神清气爽,舒惬无比。
韩维、苏轼几人宾至如归,或坐榻,或靠床,边嗅着那袅袅的龙涎香,边静静地等候。
这时,就听 “笃、笃、笃”三下不紧不慢的敲门声,众人已知谁来了。
开了门,就见司马公温文尔雅地抱拳施礼进来:“让各位久等了。”
靠在罗汉床上的吕公著笑着说道:“君实好大架子,让我们如此等候。”
坐在榻上的韩维说道:“君实不会还在为那天在经筵上的事生气吧?”
斜靠在罗汉床上的苏轼早已站起,深深施了一礼,问候道:“司马公近日心情还好否?”
坐在司马光对面的吕诲挪动了一下屁股,说道:“司马公胸襟豁达,哪会把那些小人的话记在心头。”
司马光拱手还礼道:“生气当然免不了,但听说众位好友邀光前来小聚,那气自是消了大半。”
韩维已将候在外面的歌妓请进。
那歌妓一个个霓裳广袖,貌美若仙,各就各位后,有的抚琴,有的弹瑟,琴瑟和鸣,悠扬动听,令人陶醉。
弹唱的词儿是黄庭坚的《满庭芳.茶》:
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五里名动京宫。碎骨粉身,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棒,研膏浅乳,金缕鹧鸪斑。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为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
听着听着,司马光想起苏轼吕诲刚才的问话,他也如歌中唱的“搜搅起胸中万卷怨恨的波澜”,于是愤然说道:“那气焰嚣张的吕吉甫,老夫可以不与他计较,只是那场合中透露出的信息,着实让光堪忧啊。”
此言一出,苏轼、吕诲几乎同时问道:“司马大人是指吕惠卿那厮说的变与不变之事?”
司马光道,“吕惠卿所说的‘变’,倒不必担忧。担忧的是,当吕惠卿说出此话时,皇上与那经筵官王介甫不仅不反感,更是频频点头,面露赞许之色,这倒是光极其担忧的。”
吕公著立马从罗汉床上坐起,说道:“君实这种担忧,晦叔深有同感。”
不等吕公著说完,吕诲、苏轼急问道:“司马大人说的是那变法之事?”
吕公著提盏抿了一口茶水,说道:“通过吕惠卿和皇上及介甫的谈话及神色,老夫已观察到,皇上所以要安排这次讲筵,就是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他要像仁宗朝那样,再来一场‘庆历新政’!”
这一说,大家更是吃惊,纷纷放下手中茶盏,纷纷想道:“如果真再来一次‘庆历新政’,那不仅是毁掉祖宗之法,更是要将一个好端端的太平盛世的大宋给折腾得鸡飞狗跳,毫无安宁之日?那还了得?”
想着,众人一齐把目光投向司马光,想听听他的主张。
与苏轼同坐一张罗汉床的司马光捋了捋疏朗的胡须,闪了一下凤眼,慢吞吞地叹了气,说道:“唉,这次光算是看错人喽。”
众人问:“司马公何出此言?”
司马光道:“光本以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可事实恰恰相反,要是那王介甫真的实行变法,大宋朝可又要大乱一阵喽。”
吕诲不解,问道:“司马大人,你不是也说过,这大宋弊端甚多,不变不行。现在那王介甫有意变法,你如何又担心了?”
侧卧着的苏轼“骨碌”坐起,愤然说道:“司马大人说的‘不变不行’,和王介甫要搞的变法决不是一码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接着说道,“从吕惠卿那番讲话及王介甫的神色中,子瞻已清楚地预感到,王介甫此次变法不变则已,如变,掀起的风暴远比‘庆历新政’更为厉害,更加强劲。司马公说的‘看错人了’,此言丝毫不虚!”
韩维本是借请司马光来吃茶,消消他的怨气,没想到几句话一说,反倒增添了众人的愤怒,想了想,站起提议道:“我们今天来是为过个轻松的休假日,诸位将茶饼拿出,我们边听曲儿边斗茶,以博个雅兴。莫谈政事,莫谈政事。”
说着,让歌女换了词曲,接着弹唱……
上一章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