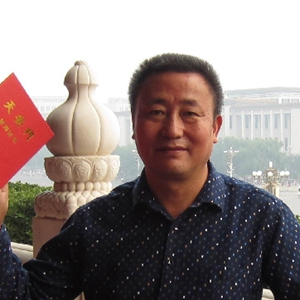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普通授权
字数:15012
阅读:5962
发表:2019/6/17
3章 历史 小说
《兵魂》第1章
0
1
2
3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第一部
第一章 你们还敢这样猖狂
4 鬼子走了
嗖嗖的风。白花花的太阳。冷湿的半化未化的霜。屋檐上吊着冰凌,明晃晃地,一滴刚化的水珠欲滴未滴、似滴非滴;树枝朝上的一面,冰凌像条镶嵌的翡翠,能透过它看见后面的枝或是更远更深更邃的太阳。
“鬼子这下全离开中国了。”
三棍子说完,伸手擤了下鼻涕,然后甩了甩,可那鼻涕粘在手上细长细长,甩了几甩也没能甩掉,他看了看,然后拎起一只鞋,张着拇指和食指,在鞋后跟上擦了擦。
“这有什么稀奇,早在白露后的一天(1945年9月9日)日本鬼子的大头头在南京就交出了他的随身佩刀。”
“就是,上次何大牛回来就说过了。”四棍子接过江启龙的话附和了声。
“那个时候只是投降,还没有走。”三棍子不屑地抬起手“嗤”了一声,“要是鬼子真的走了,他怎么还往外跑,不回来?”
“不是还有你们这些伪军没走么?”江启龙轻蔑地也挥了一下手。
“我们早不叫伪军了。”三棍子忙解释,“现在叫国民革命军。”
“就是国民党。”四棍子不知什么表情地笑着。
“你是共产党?”三棍子立即敛了脸,转向四棍子。
“不是,不是,”四棍子忙连连摇手,“我不是。”
“他是你兄弟,是不是共产党,你还不最清楚?”江启龙漫不经心地将袖着手的肘往四棍子肩上搭了搭。
虽然四棍子与他同年生,可江启龙显然要比他大一个块头。
三棍子就不再言语,将眼睛望向对面的远处。
远处,离这里足足有三四里远的稻堆山上的碉堡,在这花花的太阳下,似在颤动——他知道,这是因为化霜造成的。平日里,他就生活在那个碉堡里,自从两年前被征丁当了兵后,就一直住在那里。前半年一年里,到处打仗,所幸的是,小队长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叔,叫黄二。虽然黄二长得龅牙猴腮的,但对三棍子还算好,每次抽人,他都找各种借口将他留了下来,要不然,说不定三棍子不被共产党子弹打死,也要被日本鬼子炮弹开瓢。当然,这除了三棍子的父亲只要有一点好处都要送给他外,还有就是三棍子挺机灵,将他不仅是当表叔,而是当祖爷爷,什么事,只要他递个眼色歪着嘴巴动个指头,三棍子马上就替他办了。
稻堆山的南边是他们现在所在的横堆山,东边,是新河庄,北边隔着水阳江——水阳江上承新河庄,下分两支,一支注入水阳,一支,则流向东门渡,进入裘公河。
“你们尽偷懒,躲到这里晒太阳。”
“哎,兄弟,快过来——”随着声音,江启龙看到大罩子从屋后转了过来,“这里还真暖和。”
大罩子走到离他们还有五六米远的时候,停了下来,歪着身子笼着手用袖子擦了下脸(也不知是擦鼻涕还是擦痒),道:“这里当然暖和,三面靠墙,一面向太阳。”
“我们不是偷懒,这不,我哥回来了么。”四棍子笑着用肘指了指三棍子。
“唷,黄狗子回来了呀。”
“你说什么?”三棍子立即瞪起了眼。
“别,哎,你们别这样好不好。”江启龙靠墙的身子往起站了站,“都是一个村子上的,干吗呢,这是!”
“鬼子都走了,你还神气个什么劲儿?”大罩子一边走向江启龙侧面,一边说着。
“鬼子是走了,但这里,是我们国民革命军接管了。”
“哦喝,不叫伪军啦——哦,对了,几天前你们的汪主席的坟都被扒掉了……”②
一语戳到了三棍子的心尖上,临回来时,黄二确实与他一再地交待过,他们现在叫国民革命军,最高最高的头头是蒋总统,再也不要提汪主席;他立即变了脸色,瞪着眼睛,往前走上几步……
“瞪什么瞪,比眼珠大小啊?”大罩子也往前上了一步,“有本事,你去东门渡瞪去。”
“东门渡那里芦苇丛生,后面荒山野岭的,去那干吗?”江启龙揣着聪明装糊涂地“阴阳怪气”着,“难道那里藏着新四军?”
“新四军?早在5年前就被我们打光了,还新四军?有野猪还差不多。”三棍子转向江启龙。
“‘我’还‘们’?你穿这身黄皮才几年?”大罩子讥笑道,“还‘我们’!”
“有本事你穿身我看看?”
“我和四棍子还有江启龙不是比你们要小没赶上年纪么。”大罩子后仰了一下,但立即又俯过身来:“但人家何大牛就不穿。”
“他不穿?是,他不穿,所以他不是一直在外面打流浪吗,敢回来?”
“怎么不敢回来,日本鬼子不是走了吗?”四棍子不服地插了一句。
三棍子憋了憋气,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好。
但这一憋,倒是一下将三棍子憋醒了过来,转向大罩子:“你刚才说什么?
②1946年1月21日,也就是乙酉年腊月十九,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精卫坟墓炸毁。
前几天汪主席的坟被扒掉了?你怎么知道的?说!”
“我怎么知道的关你屁事?”
三棍子咬了咬牙,恶狠狠地指着大罩子道:“你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那你是不是?”大罩子伸手挡开三棍子的手,一边说着一边做着手势,“我整天与他们在一起,连横堆山都没离开过一步,还共产党?我要是共产党,‘砰’,我非一枪崩了你个……”
“好了好了,今天三棍子好不容易回来趟。”江启龙一看两人要动真,忙再次劝道,“都是一个村上……”
“是呀,要不是今天腊月二十四掸尘(也叫过小年),我哥还不得回来呢。”四棍子一见他们杠上了,也忙着站到中间。
大罩子一见三棍子动了真,忙缓了下来,笑着一边拉开四棍子一边说:“没事,谁叫他是我哥呢——是吧,三棍子,你比我大三岁呢;我们说着玩儿,伤言伤语不伤兄弟情嘛。”
三棍子见大罩子首先服软了,也就顺水推舟,伸手轻拍了下大罩子的肩膀,说:“我也是说着玩儿,一个村上的,谁还不知道谁。”
嘴上这样说着,但对大罩子是从哪得到汪主席被扒坟的消息,还是心存疑虑。
大罩子呢,当然不会掐指算命,打卦占卜,他的消息,自然是另有一番隐情……③
“喂,家家都忙得竹帚朝上了天,你们却在这躲着。”
循声望去,只见一胖胖的女孩,穿着一件花袄,原本生动而活泼的脸上,却被不知是锅灰还是泥灰抹得花里胡哨,看不出年龄也看不出表情。
“鬼子都走了,江启凤,你还抹着脸啊?”大罩子首先叫了起来。
四棍子也指着江启凤笑道:“抹了脸却穿着花袄,还不是花姑娘呀?”
江启凤就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花袄,望了一眼三棍子,没说话,转向江启龙:“老爷让你回去呢。”
“老爷叫你回去呢。”四棍子学着江启凤取笑着江启龙。
“谁叫你穿成这样就出来了?”江启龙皱了下眉头。
“不是鬼子都走了么?”
③确实是另有“隐情”——只不过,大罩子这个时候还没有“革命意识”,只是受人之反复叮嘱,不能说出去;出于义气,“隐”下了这“情”而已。
原来,鬼子侵占中国期间,江成富虽然被上面任命为一方保长,但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日本这小蛮夷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因此,尽管江启凤还小,不过金钗之年,但他还是十分小心,不让她穿花衣服,不让扎小辫子,不让露出真面容——不穿花衣服,不扎小辫子,这都好办,而不让露真容,女孩爱美的天性,却使江启凤挨了不知多少骂,因为前面母亲将她的脸涂上锅底灰,后面她便找块有水的地方就想洗干净。久而久之,她每天也就忘了有洗脸这一说,直到脸上的灰褪得差不多时,母亲提醒她要重抹了,这时她才洗净一次,自我还没欣赏上三分钟,就又被黑灰给遮上了。
“看看你那脸——”三棍子这时走了过来,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想摸一下江启凤的脸。
大罩子立即“啪”地打下了他伸了一半的手,说:“你想干吗?”
“什么想干吗?你看看她的脸。”三棍子甩了甩被大罩子突然的一巴掌打得有些疼的手。
江启凤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要不是脸上的灰,现在,肯定满脸飞霞;今年她15岁了,年一过,就是碧玉年华,正是羞涩的年龄。
“江启龙,鬼子都走了,让你姐把脸洗了呗。”四棍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着,“怎么,洗了还怕何大牛回来认不出来她呀!”
说起来好笑,一次何大牛回来,正好江启凤在水边洗净了脸,恁是没认出来,问她是哪个村的,怎么跑到这来了。江启凤也是一时顽性,说她是日本小妞,他爹就在村上。何大牛立即大惊失色,一把拧了她,差点没将她胳膊拧断。尽管她一再解释说她是江启凤,可何大牛就是不信,直到江启凤再次将脸涂得花里胡哨,何大牛这才笑了起来……
虽然这是两三年前的笑话了,但说起来,仍是让人忍俊不禁。
江启凤乜了一眼四棍子,转身走了。
“散了散了,回家掸尘去吧。”大罩子望着江启凤的背影,挥了挥手道。
三棍子则站在那有些发呆。
“哥,我们也回吧。”四棍子用肘碰了碰三棍子。
三棍子似才回过神,望了一眼四棍子,什么也没说,转过身,上前走了;四棍子忙撵上两步,兄弟俩一前一后转过了墙角。
大罩子见三棍子四棍子走了,跟上也正走开的江启龙,用肘撞了下他,道:“何大牛回来了。”
江启龙一下站住了,睁大着眼睛:“大牛回来了!”
“嘘,”大罩子故作神秘地嘘了一下,“他说他爹也要回来。”
“何老爷!”
大罩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5 何老爷回来了
何老爷是在江老爷的大太太被杀后离开横堆山的。
民国二十年何老爷带着何大流为江老爷家“引弟”,结果,不仅引来了“江启凤”,当然,也有“江启龙”,还引来了一场亘古的水灾。
在一片白浪浪的水还没退尽,何老爷便开始放粮,不知是为了同情乡邻们还是为了为何大流改过;在水退后,灾民们四散逃荒,吃过江老爷家江启龙的“满月酒”回来后,他决计为何大流改名。
改成什么?
横堆山惟一读过私墪的何老爷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突然灵光乍现,将“流”改成了“牛”,意思是,有“牛”,便有田;有田,便有种;有种,便有收;有收,便有饭吃。
果然,“何大流”改成“何大牛”后的第二年,庄稼长势竟奇迹般地丰茂,是个少有的丰年,尽管村上人在春荒中除了逃难在外的饿死的不下三分之二。没饿死的三分之一人家,活下来的,除了大人,小儿中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男孩——这也是村上现在与江启凤一般大的,只有江启凤一个女孩的缘由;当然,也是村上活下来的男孩们众星捧月般地呵护着江启凤的原因。
“何大流”成了“何大牛”后,水灾是没有了,可是,没过几年,比水灾更令人害怕的灾难,却来了——
虽然早就听说日本鬼子打来了,可那毕竟是“听说”,及至一天傍晚,何老爷正准备邀请江老爷过来一起一方面喝杯小酒,一方面谈谈明年怎么收租的事,不想,送信的下人刚走出门,却很快就又转了回来,慌慌张张,何老爷正准备责问让他去请江老爷,怎么又回来了,那个下人结结巴巴地说,村上人全都在跑反。
“跑反?”
“跑鬼子反。”
“鬼子在哪?”
“在——”
下人一下卡住了,在哪,他也只是听一村上的人在说,究竟在哪,他还真的没听清楚。
何老爷笑了一下:“鬼子,也是人吧?”
下人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何老爷不管他点头还是摇头,继续道:“只要不是鬼,有何怕?”
“可是鬼子……”下人有些不服地辩解。
“‘鬼’后面不是还有一个‘子’么。”何老爷再次轻蔑地笑了笑。“子者,人子。既为人子,焉惧矣?”
“何老爷,何老爷——”正说到这,门外闯进一个人来,一看,是江老爷家的雇农。“何老爷,我们家老爷说鬼子马上要来,问你作何打算?”
“作何打算?没打算。”何老爷笑了一下,“你们江老爷呢,他作何打算?”
“我们老爷准备捆扎捆扎,也跑反。”
“跑反?往哪跑?”何老爷顿了下,想想说:“你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往哪跑也不是个事,要是鬼子把整个中国都占了,他还能往哪跑?”
“那老爷的意思是——”
“不跑,哪也不去。”
“是,哪也不去。我这就回去禀报我们家老爷。”
江成富家的雇农离开后,何老爷突然莫名地烦躁起来,在家里转了两圈,静不下来,又来到院子里转。可转了两圈,还是不安。于是,他走出院子,往村头走,一直走出了村子,站在一块高地上,望着朦朦胧胧的稻堆山,想象着鬼子正从那里结着队往这边开来。
可是,待他定睛一看,鬼子倒是没看到,看到的,却是一些男男女女正往这边跑——这是那些刚跑反出去的。
跑出去了,怎么又往回?
何老爷这个聪明人一时竟也犯起了糊涂。
“啊呀,何老爷,你怎么跑这来了?”
“我没跑。”何老爷很不高兴地转向向他正张着嘴说着话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我为什么要跑?”
“都跑光了。”那个人自顾自地说着。
“你不是在?我不是在!怎么就都跑光了?”
“我也正准备跑呢。”
“准备跑?往哪跑?你看——”何老爷用手指了指正往回来的那些跑反的人。
花白头发就踮着脚地望了望那些正往回跑着的人群。
“回去。”
第一章 你们还敢这样猖狂
4 鬼子走了
嗖嗖的风。白花花的太阳。冷湿的半化未化的霜。屋檐上吊着冰凌,明晃晃地,一滴刚化的水珠欲滴未滴、似滴非滴;树枝朝上的一面,冰凌像条镶嵌的翡翠,能透过它看见后面的枝或是更远更深更邃的太阳。
“鬼子这下全离开中国了。”
三棍子说完,伸手擤了下鼻涕,然后甩了甩,可那鼻涕粘在手上细长细长,甩了几甩也没能甩掉,他看了看,然后拎起一只鞋,张着拇指和食指,在鞋后跟上擦了擦。
“这有什么稀奇,早在白露后的一天(1945年9月9日)日本鬼子的大头头在南京就交出了他的随身佩刀。”
“就是,上次何大牛回来就说过了。”四棍子接过江启龙的话附和了声。
“那个时候只是投降,还没有走。”三棍子不屑地抬起手“嗤”了一声,“要是鬼子真的走了,他怎么还往外跑,不回来?”
“不是还有你们这些伪军没走么?”江启龙轻蔑地也挥了一下手。
“我们早不叫伪军了。”三棍子忙解释,“现在叫国民革命军。”
“就是国民党。”四棍子不知什么表情地笑着。
“你是共产党?”三棍子立即敛了脸,转向四棍子。
“不是,不是,”四棍子忙连连摇手,“我不是。”
“他是你兄弟,是不是共产党,你还不最清楚?”江启龙漫不经心地将袖着手的肘往四棍子肩上搭了搭。
虽然四棍子与他同年生,可江启龙显然要比他大一个块头。
三棍子就不再言语,将眼睛望向对面的远处。
远处,离这里足足有三四里远的稻堆山上的碉堡,在这花花的太阳下,似在颤动——他知道,这是因为化霜造成的。平日里,他就生活在那个碉堡里,自从两年前被征丁当了兵后,就一直住在那里。前半年一年里,到处打仗,所幸的是,小队长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叔,叫黄二。虽然黄二长得龅牙猴腮的,但对三棍子还算好,每次抽人,他都找各种借口将他留了下来,要不然,说不定三棍子不被共产党子弹打死,也要被日本鬼子炮弹开瓢。当然,这除了三棍子的父亲只要有一点好处都要送给他外,还有就是三棍子挺机灵,将他不仅是当表叔,而是当祖爷爷,什么事,只要他递个眼色歪着嘴巴动个指头,三棍子马上就替他办了。
稻堆山的南边是他们现在所在的横堆山,东边,是新河庄,北边隔着水阳江——水阳江上承新河庄,下分两支,一支注入水阳,一支,则流向东门渡,进入裘公河。
“你们尽偷懒,躲到这里晒太阳。”
“哎,兄弟,快过来——”随着声音,江启龙看到大罩子从屋后转了过来,“这里还真暖和。”
大罩子走到离他们还有五六米远的时候,停了下来,歪着身子笼着手用袖子擦了下脸(也不知是擦鼻涕还是擦痒),道:“这里当然暖和,三面靠墙,一面向太阳。”
“我们不是偷懒,这不,我哥回来了么。”四棍子笑着用肘指了指三棍子。
“唷,黄狗子回来了呀。”
“你说什么?”三棍子立即瞪起了眼。
“别,哎,你们别这样好不好。”江启龙靠墙的身子往起站了站,“都是一个村子上的,干吗呢,这是!”
“鬼子都走了,你还神气个什么劲儿?”大罩子一边走向江启龙侧面,一边说着。
“鬼子是走了,但这里,是我们国民革命军接管了。”
“哦喝,不叫伪军啦——哦,对了,几天前你们的汪主席的坟都被扒掉了……”②
一语戳到了三棍子的心尖上,临回来时,黄二确实与他一再地交待过,他们现在叫国民革命军,最高最高的头头是蒋总统,再也不要提汪主席;他立即变了脸色,瞪着眼睛,往前走上几步……
“瞪什么瞪,比眼珠大小啊?”大罩子也往前上了一步,“有本事,你去东门渡瞪去。”
“东门渡那里芦苇丛生,后面荒山野岭的,去那干吗?”江启龙揣着聪明装糊涂地“阴阳怪气”着,“难道那里藏着新四军?”
“新四军?早在5年前就被我们打光了,还新四军?有野猪还差不多。”三棍子转向江启龙。
“‘我’还‘们’?你穿这身黄皮才几年?”大罩子讥笑道,“还‘我们’!”
“有本事你穿身我看看?”
“我和四棍子还有江启龙不是比你们要小没赶上年纪么。”大罩子后仰了一下,但立即又俯过身来:“但人家何大牛就不穿。”
“他不穿?是,他不穿,所以他不是一直在外面打流浪吗,敢回来?”
“怎么不敢回来,日本鬼子不是走了吗?”四棍子不服地插了一句。
三棍子憋了憋气,一时不知道怎么说好。
但这一憋,倒是一下将三棍子憋醒了过来,转向大罩子:“你刚才说什么?
②1946年1月21日,也就是乙酉年腊月十九,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精卫坟墓炸毁。
前几天汪主席的坟被扒掉了?你怎么知道的?说!”
“我怎么知道的关你屁事?”
三棍子咬了咬牙,恶狠狠地指着大罩子道:“你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那你是不是?”大罩子伸手挡开三棍子的手,一边说着一边做着手势,“我整天与他们在一起,连横堆山都没离开过一步,还共产党?我要是共产党,‘砰’,我非一枪崩了你个……”
“好了好了,今天三棍子好不容易回来趟。”江启龙一看两人要动真,忙再次劝道,“都是一个村上……”
“是呀,要不是今天腊月二十四掸尘(也叫过小年),我哥还不得回来呢。”四棍子一见他们杠上了,也忙着站到中间。
大罩子一见三棍子动了真,忙缓了下来,笑着一边拉开四棍子一边说:“没事,谁叫他是我哥呢——是吧,三棍子,你比我大三岁呢;我们说着玩儿,伤言伤语不伤兄弟情嘛。”
三棍子见大罩子首先服软了,也就顺水推舟,伸手轻拍了下大罩子的肩膀,说:“我也是说着玩儿,一个村上的,谁还不知道谁。”
嘴上这样说着,但对大罩子是从哪得到汪主席被扒坟的消息,还是心存疑虑。
大罩子呢,当然不会掐指算命,打卦占卜,他的消息,自然是另有一番隐情……③
“喂,家家都忙得竹帚朝上了天,你们却在这躲着。”
循声望去,只见一胖胖的女孩,穿着一件花袄,原本生动而活泼的脸上,却被不知是锅灰还是泥灰抹得花里胡哨,看不出年龄也看不出表情。
“鬼子都走了,江启凤,你还抹着脸啊?”大罩子首先叫了起来。
四棍子也指着江启凤笑道:“抹了脸却穿着花袄,还不是花姑娘呀?”
江启凤就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花袄,望了一眼三棍子,没说话,转向江启龙:“老爷让你回去呢。”
“老爷叫你回去呢。”四棍子学着江启凤取笑着江启龙。
“谁叫你穿成这样就出来了?”江启龙皱了下眉头。
“不是鬼子都走了么?”
③确实是另有“隐情”——只不过,大罩子这个时候还没有“革命意识”,只是受人之反复叮嘱,不能说出去;出于义气,“隐”下了这“情”而已。
原来,鬼子侵占中国期间,江成富虽然被上面任命为一方保长,但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日本这小蛮夷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因此,尽管江启凤还小,不过金钗之年,但他还是十分小心,不让她穿花衣服,不让扎小辫子,不让露出真面容——不穿花衣服,不扎小辫子,这都好办,而不让露真容,女孩爱美的天性,却使江启凤挨了不知多少骂,因为前面母亲将她的脸涂上锅底灰,后面她便找块有水的地方就想洗干净。久而久之,她每天也就忘了有洗脸这一说,直到脸上的灰褪得差不多时,母亲提醒她要重抹了,这时她才洗净一次,自我还没欣赏上三分钟,就又被黑灰给遮上了。
“看看你那脸——”三棍子这时走了过来,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想摸一下江启凤的脸。
大罩子立即“啪”地打下了他伸了一半的手,说:“你想干吗?”
“什么想干吗?你看看她的脸。”三棍子甩了甩被大罩子突然的一巴掌打得有些疼的手。
江启凤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要不是脸上的灰,现在,肯定满脸飞霞;今年她15岁了,年一过,就是碧玉年华,正是羞涩的年龄。
“江启龙,鬼子都走了,让你姐把脸洗了呗。”四棍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着,“怎么,洗了还怕何大牛回来认不出来她呀!”
说起来好笑,一次何大牛回来,正好江启凤在水边洗净了脸,恁是没认出来,问她是哪个村的,怎么跑到这来了。江启凤也是一时顽性,说她是日本小妞,他爹就在村上。何大牛立即大惊失色,一把拧了她,差点没将她胳膊拧断。尽管她一再解释说她是江启凤,可何大牛就是不信,直到江启凤再次将脸涂得花里胡哨,何大牛这才笑了起来……
虽然这是两三年前的笑话了,但说起来,仍是让人忍俊不禁。
江启凤乜了一眼四棍子,转身走了。
“散了散了,回家掸尘去吧。”大罩子望着江启凤的背影,挥了挥手道。
三棍子则站在那有些发呆。
“哥,我们也回吧。”四棍子用肘碰了碰三棍子。
三棍子似才回过神,望了一眼四棍子,什么也没说,转过身,上前走了;四棍子忙撵上两步,兄弟俩一前一后转过了墙角。
大罩子见三棍子四棍子走了,跟上也正走开的江启龙,用肘撞了下他,道:“何大牛回来了。”
江启龙一下站住了,睁大着眼睛:“大牛回来了!”
“嘘,”大罩子故作神秘地嘘了一下,“他说他爹也要回来。”
“何老爷!”
大罩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5 何老爷回来了
何老爷是在江老爷的大太太被杀后离开横堆山的。
民国二十年何老爷带着何大流为江老爷家“引弟”,结果,不仅引来了“江启凤”,当然,也有“江启龙”,还引来了一场亘古的水灾。
在一片白浪浪的水还没退尽,何老爷便开始放粮,不知是为了同情乡邻们还是为了为何大流改过;在水退后,灾民们四散逃荒,吃过江老爷家江启龙的“满月酒”回来后,他决计为何大流改名。
改成什么?
横堆山惟一读过私墪的何老爷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突然灵光乍现,将“流”改成了“牛”,意思是,有“牛”,便有田;有田,便有种;有种,便有收;有收,便有饭吃。
果然,“何大流”改成“何大牛”后的第二年,庄稼长势竟奇迹般地丰茂,是个少有的丰年,尽管村上人在春荒中除了逃难在外的饿死的不下三分之二。没饿死的三分之一人家,活下来的,除了大人,小儿中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男孩——这也是村上现在与江启凤一般大的,只有江启凤一个女孩的缘由;当然,也是村上活下来的男孩们众星捧月般地呵护着江启凤的原因。
“何大流”成了“何大牛”后,水灾是没有了,可是,没过几年,比水灾更令人害怕的灾难,却来了——
虽然早就听说日本鬼子打来了,可那毕竟是“听说”,及至一天傍晚,何老爷正准备邀请江老爷过来一起一方面喝杯小酒,一方面谈谈明年怎么收租的事,不想,送信的下人刚走出门,却很快就又转了回来,慌慌张张,何老爷正准备责问让他去请江老爷,怎么又回来了,那个下人结结巴巴地说,村上人全都在跑反。
“跑反?”
“跑鬼子反。”
“鬼子在哪?”
“在——”
下人一下卡住了,在哪,他也只是听一村上的人在说,究竟在哪,他还真的没听清楚。
何老爷笑了一下:“鬼子,也是人吧?”
下人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何老爷不管他点头还是摇头,继续道:“只要不是鬼,有何怕?”
“可是鬼子……”下人有些不服地辩解。
“‘鬼’后面不是还有一个‘子’么。”何老爷再次轻蔑地笑了笑。“子者,人子。既为人子,焉惧矣?”
“何老爷,何老爷——”正说到这,门外闯进一个人来,一看,是江老爷家的雇农。“何老爷,我们家老爷说鬼子马上要来,问你作何打算?”
“作何打算?没打算。”何老爷笑了一下,“你们江老爷呢,他作何打算?”
“我们老爷准备捆扎捆扎,也跑反。”
“跑反?往哪跑?”何老爷顿了下,想想说:“你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往哪跑也不是个事,要是鬼子把整个中国都占了,他还能往哪跑?”
“那老爷的意思是——”
“不跑,哪也不去。”
“是,哪也不去。我这就回去禀报我们家老爷。”
江成富家的雇农离开后,何老爷突然莫名地烦躁起来,在家里转了两圈,静不下来,又来到院子里转。可转了两圈,还是不安。于是,他走出院子,往村头走,一直走出了村子,站在一块高地上,望着朦朦胧胧的稻堆山,想象着鬼子正从那里结着队往这边开来。
可是,待他定睛一看,鬼子倒是没看到,看到的,却是一些男男女女正往这边跑——这是那些刚跑反出去的。
跑出去了,怎么又往回?
何老爷这个聪明人一时竟也犯起了糊涂。
“啊呀,何老爷,你怎么跑这来了?”
“我没跑。”何老爷很不高兴地转向向他正张着嘴说着话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我为什么要跑?”
“都跑光了。”那个人自顾自地说着。
“你不是在?我不是在!怎么就都跑光了?”
“我也正准备跑呢。”
“准备跑?往哪跑?你看——”何老爷用手指了指正往回来的那些跑反的人。
花白头发就踮着脚地望了望那些正往回跑着的人群。
“回去。”
上一章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