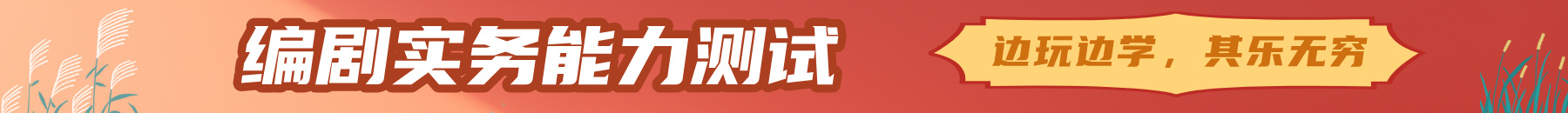权属:原创 · 独家授权
字数:32461
阅读:10106
发表:2015/9/21
20章 家庭 小说
《红肚兜》第1-5章
1-5
6-11
12-16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长篇小说正文
《红肚兜》
前 言
人的一生能够拥有梦想是幸福的,就像生命之舟标注了航线,又如漂泊之人灵魂有了家园。我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对于文学的执着向往,因为我本平庸,以为拿捏文字可以改变自己,证明我人生一世的实际意义。
然而我又不甘媚俗,不愿跟风那些流行元素,蛊撰一些玄幻灵异、时空穿越的魅惑来吸人眼球,也不想串烧那种颠倒阴阳、调侃爱情的闹剧来给这个本已滥情的文化市场添堵。因为我心里始终保持着一份初衷的宁静,总想以一种传统的、纯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自我意识,并以其点滴笔墨折射时代脉络,勾画人性本质,试图达到反思社会现实、启迪世人感悟的目的,如此而已。
但是我又摆脱不了男欢女爱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只是不想屈就那些鸡零狗碎的闲情逸事,也无意窠臼那种皆大欢欣、圆满结局的套路喜剧。有人说悲剧能够洞穿人的内心柔软神经,更能呼唤人性良知而产生震撼效应。因而,根据鲁迅先生对于悲剧的定义: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以此原理,本人凭借年近半百的所见所闻,并在捕捉生活原型的基础之上,经过耗时多年,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总算完成了这部悲情小说,旨在以故事贯穿历史取胜,以情节大喜大悲感人,聊以碎岁,以飨读者。
由于本文的笔调对于社会伦理的常规描写有所突破,可能会引起部份读者的不适或非议,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这也不失为对文学领域的一种大胆尝试,欢迎读者批判性的鉴赏,如果这粒试水之石能够击起文海一丝涟漪,也就不枉我常年青灯孤影、咬文嚼字地苦苦追逐文学之梦了。
作者(代序)
目 录
姊妹篇(上部)
一、 古城发生离奇事件 法制编辑追根溯源
二、 下乡知青前途无望 空虚迷茫坠入歧情
三、 不幸身孕诚惶诚恐 万般无奈遁入深山
四、 寄身猎户私生一子 高考中榜挥泪而去
五、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遗子失踪生死未卜
姊妹篇(下部)
六、 还原真相教授探监 女犯原是商界名流
七、 专职司机兼当随秘 孤男寡女暗相心仪
八、 误入骗局企业受损 急中生智共赴危难
九、 勇斗地虎化险为夷 两情相悦春风几度
十、 两好合一欲结连理 道破孽缘情何以堪
十一、惟恐毁誉避之不及 身陷迷情无以自拔
十二、寻机发财借鸡下蛋 闯下债祸溜之大吉
十三、有恃无恐三番要挟 反目成仇顿生邪念
十四、有心无胆顺流逆流 真相乍现急转直下
十五、蓄意谋杀走向不归 巧释迷雾欲盖弥彰
十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铁窗囹圄悔恨交加
尾 声
姊妹篇(上部)
一
古城发生离奇事件
法制编辑追根溯源
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相距之间,在我国西北方向那些山川、河流相互交融的沃土之上,有一座远近闻名、谓之“萌州”的内陆古城。由于千年历史文化的蕴润,这里的世俗民风一贯崇尚传统德化教育,即便是倍受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态度依然怀古守旧。就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在相交织、传统与现实相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惊世骇俗的离奇事件,其内幕不仅涉及命案,而且伤及到社会伦理的基本道德规范,事发时兀然引起舆论一派哗然,成为当地旷古至今的爆炸性新闻。
21世纪初页的一个清明节,在萌州郊区的公墓之中,随着四围烟雾缭绕、鞭炮炸鸣的祭祀氛围,一位简发素服、龄近半百的中年妇女,手持大束鲜花夹带着些许什物,穿过中路熙嚷的人群拾级而上,此人是本地一名中学教师,她就那是那起轰动性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由于那场变故使她一次失去了两个直系亲人,其后人们发现,但凡年终岁末或上坟时节,她都务必赶来亡者墓地凭吊祭奠,也许是寄托哀思,亦或是排遣负疚心理,就这样她重复演绎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苦情景。
只见她来到半坡深处并排的两座墓前站定,习惯的将花束分别向两墓摆开,然后只在一座坟前上香、焚纸。做完这些她从怀中取出了一条红色的、好似肚兜形状的布巾挂于坟头,盯着那物她两眼垂泪,伫立着久久不愿离去。正在此时,从她身后轻轻传出一句问话声来:“请问是夏雪老师吗?”
夏雪蓦然回首,发现身后已站着一男一女两个陌生的人。看那女的年轻、时尚,男的却是一位皓首童颜的长者,两人正朝她微微点头致意。瞧着两位不速之客,夏雪迟疑的回应:“是我,你们是……”
那女子首先开腔道:“夏老师,我是本市报社记者,我们打听到清明节你可能会来扫墓,想不到你果然在此。”她指了指身旁的长者说:“是这样,我今天陪这位前辈来找你,给你介绍一下,他是省法制报的主编,这次是专程从省城赶来见你的。”
长者慈眉善目,年纪约六十开外,一副学者模样。听到介绍自己,立刻取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夏雪接过认真看看,又仔细端详近前之人,半响竟然惊异地叫出声来:“哦!是丹阳教授,您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真是您来找我吗?”那语气似曾相识。
长者听她的话外有音,也打量起她来,并回问道:“你认识我?”
夏雪浅笑着说:“我早先见过你,只是时间太久,差点认不出了。”
长者十分兴致的又问:“噢,什么时候,在哪里?”
夏雪尽量回忆着说:“那还是文革过后刚恢复高考不久,我在华东师范学院上学时,院校曾经请你来给我们作过司法讲座,当时听说你在什么政法学院任高级讲师,曾经给我们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教授眼睛一亮,频频点头说:“喔,好象有这么回事,真是太巧了,你的记忆真好。”
夏雪直接问道:“你老现在可好,怎么不上讲台,改当主编了?”
教授解释说:“我已退休了,但身体还好,现在被聘为这家法制报社的责任编辑,同时做些法学研究。”说着他话锋一转“实不想瞒,我这次来萌州,就是为你们家的事想当面采访一下你,想不到我们还有师生之缘呢。”
“采访我什么?”夏雪诧意的问。
那名女记者接话说:“想必这墓地中埋的是你的亲人吧,丹阳老师就是为这墓中的人和事想了解一些情况,你看可以和他谈谈吗?”
闻此言夏雪黯然神伤,推辞说:“不,我不想谈过去,往事如烟,希望你们也不要再提那些事好吗,实在抱歉。”
一时塞语,良久,教授开始劝慰道:“夏雪,虽然你们家的事在法律上已经盖棺论定,但是对其事实由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也曾引起舆论界一些不实报道,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想对这起案件的因果关系进行明辩梳理,也就是说这个事件不仅是你们家的悲剧,也是时代变迁的产物,我们将以客观的、高度负责的态度还原事实真相,还舆论一个公正的说法。”
夏雪一脸戚惶的面朝着坟墓不再言语。此时教授才注意到眼前有两座紧捱的墓穴,一并摆放着同样的花束,其中一座墓碑上篆刻着“赵满强之墓”的简单字样,左下角只有一个称作“赵老爹”的人立碑署名。而另一座墓除了龛型具全外,却没有竖碑和片字铭文。他不禁试探着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叫赵满强的人就是你的亲生孩子吧。”
一听“亲生孩子”夏雪两眼涌动泪花,嘴唇嗫嚅着欲说还休,她的情绪变化证实了教授的说法。
女记者抬眼看见墓顶上挂着的那条红色小物件,不由好奇地走拢去捻开来看,只见那上面现出了几个残缺的“红卫兵”字样,虽然败了颜色,但依然明晰可辨,她问:“这是啥东西,它代表什么呀?”
夏雪缓缓地上前取下那物捏在手中摩挲着,半阵才说出话来:“这是墓中的娃出生时我给他缝的肚兜,是用我早先戴过的一只‘红卫兵’袖套改做的。”
女记者和教授相互对视了一下,觉得那肚兜一定有不少故事,但是此地不便追述,教授就朝近旁的那座无字墓移步过去问道:“喏,这座没有碑文的墓又是谁的呢?”
夏雪喃喃地说:“她是谁?她就是我的亲妹儿,夏霖。”言罢抑止不住大泪滂沱。
教授甚感愕然,十分不解的说:“我们都知道夏霖虽然被判了极刑,但并没有执行,后来是改判了的,为何一定要给她置下这块墓地呢?”
“按当时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我们还以为她会随强娃一起去了……”夏雪伤心地擦着眼泪说:“所以事先也在这里置了这块地……后来才知道她改了刑,但考虑到她很难生还出狱,监狱又不许探视,她就如已死而没埋的人,因此这地暂时还没退,就算是个念象吧。”
“这样呀!”教授释然的点点头,接着再次提出说:“为了给已死和未死之人一个公平的说法,为了消除舆论对你本人的误解,我建议你还是正式接受我们的采访。”
夏雪依然回绝教授的要求,她说:“算了吧,往事不堪回首,我想还是让那些事连同这墓一道深埋地下,随着时间慢慢消亡、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
场面有些尴尬,女记者插言道:“夏老师,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们也知道,就因为你们家的事让世人对你产生了许多偏见,连学校也迫于舆论压力暂停了你任教的资格,你还有什么可回避的,也许我们可以帮你澄清一些事实,消除别人的恶语中伤,换得社会对你的理解和同情。”
夏雪有所触动,她想是呀,自从遗失的亲生骨肉命归黄泉、自己的同胞妹子锒铛入狱,仿佛一夜之间她便从一名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沦为遭人唾弃的异类。一年多来她的内心一直陷入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而这场悲剧的起源又与自己年轻时那青涩蒙昧的少女情怀有关,所以面对世上的流言蜚语她有口难辩,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她两鬓斑白,容颜过早的衰老了,长此以往如何才是尽头。
教授接着说:“夏雪,希望你能勇敢面对现实,过去在你身上发生的事不一定就是你的错,所以你何不讲出实情,以正视听,这样或许有益于你的生活,有利于今后走好脚下的路。”
这番话似乎对夏雪很有效,经再三考虑,后来终于答应了教授的采访。于是三人一行出了公墓园陵,搭乘女记者的小车去到萌州城内一处僻静的茶庄,并由她招呼着定下了一个包间。但是待他们刚坐定,沏上茶饮,女记者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而后她歉意地对教授说:“丹阳老师,刚才我们社长通知说市里有个重要采访任务,必须得去,不好意思,这里我先不陪你了,等我那边一完事就来接你,你看行吗?”
教授随即点头道:“行、行,你去忙吧,我这里不要紧的。”
女记者起身说:“那好,一会儿再联系哈。”并对夏雪道了声:“夏老师,你们慢慢聊,放心,是啥就说啥,没关系的。”说着摆摆手匆匆走了。
这样就留下了教授和夏雪单独谈话,当两人调整好心态,在他的循循善诱之下,在开启的录音机面前,夏雪慢慢打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心扉,大胆地讲出了自己雪藏二十多年、鲜为人知的那段畸情悲悯的故事。
二
下乡知青前途无望
空虚迷茫坠入畸情
故事是从夏雪的名字开始讲起的,夏雪问教授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含义?教授惑然。她便解释说自己本是知识份子家庭出生,父亲是在旧社会上过“洋学堂”的文化人,解放后又好在报刊上发表点文章,由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被迫接受劳动改造。老爸熟知“窦娥”喊冤、六月下雪的历史悲剧,他说自己比窦娥还冤,刚好那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因为姓夏,又是女娃,他就给孩子取名为夏雪,象征夏天之雪,以此借谕自己的冤屈。
在生养子女的问题上,父亲一直想要个男孩。后来间隔多年,妈妈前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仍都是女娃,中间那个因病夭折了,剩下一个是在一九六九年降生的,因为那是在“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之年,父亲以为可以春风化雨,使自己的政治处境得到改善,因此就给这个迟来的女孩取了个名字叫夏霖。而存活的夏雪与夏霖两姊妹年龄相差竟有十一、二岁。
妹妹的出生并非天降甘霖,在政治上父亲依然受到旁人的偏见和歧视,他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长期的郁郁寡欢之中心劳成疾,未到中年便一病不起而撒手人寰。留下妈妈带着两女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直到夏雪高中毕业,随着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浪潮,被有关组织分配到边远的山区农村去插队落户。
与夏雪一道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学均是各个学校汇集而来的应届毕业生。接收他们下放的那个地方叫“水磨公社”,那是因为当地一条小河上有个很大的水碾石磨而得名。可能是考虑到女孩的生理条件,夏雪与另外一位女生被公社安排到大山脚下一个生产小队上,这个队距公社约十来里路,位于两座大山之间的狭长地带,由于这里遍布柿树,所以地名就叫“柿树垭”。
队里安置夏雪两人的住处是由粮食仓库隔搭的一角简易陋室,屋内的门窗四处透风,房顶上雨雪可以飘进,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她们跟着当地农民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动。由于每天干着机械而繁重的农活,另一位女生熬不住便经常借故跑回家去。夏雪比较坚强,她知道家里帮不了自己,以为只要好好表现就可以被公社推荐出去安排工作。但是事与愿违,一两年后消息纷纷传来,其它队上那些表现好或不好的知青被调走不少,就连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子也因家庭成份好而与她拜拜回城去了。
后来夏雪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有两次单位来招工都因“政审”条件而不能过关。由此她看到现实与理想有多么大的差异,以至陷入深深的困惑与迷茫之中。似乎是“看破红尘”,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起来,也开始借故赖工,常常蜗居在那泥巴墙内的斗室里恹恹的不肯下床。
有那么一天,雨过天晴,屋外有几只小鸟在啁啾啭啼,夏雪的童心被唤起,她打开房门慵慵的伸了个懒腰,就朝房前的一棵大柿树下去寻那些鸟儿,当那些鸟惊飞起来,她顺着飞往的方向看去,忽然发现那边有一个身着橄榄绿军装的青年正向这边健步走来,虽然没戴领章、帽徽,但看那人挺有精神。夏雪不觉眼睛一亮,因为在这穷乡僻壤的山窝里日常所见的都是与泥土一色的农民,乍眼见到如此衣着整洁、昂首走路的人不由令她刮目相看。那人经过房前,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在云隙透过的一缕阳光之下,她看到了一张五官端正、颇具英气的面孔,当他走过时竟也特意的回眸一瞥,仿佛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使夏雪盯着他的后背愣愣的好久未能将视线挪开。
恰好这时垓坎下一位相邻的张姓大妈打猪草回来,夏雪抑止不住好奇,便向她打听刚走过去的人是谁。大妈歇下脚瞅了瞅那个远去的背影说:“哦,那是垭口‘郝老拐’家的儿子从部队复员回来了,叫郝林,我们喊他林娃子,这下可好,他们家又添劳力啰。”
“郝老拐,就是那个瘸了腿杵着拐杖的老人吗?”在夏雪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性格古怪的残疾人,还知道他儿子是在当兵,有一个儿媳在家务农,那媳妇体壮腰圆,属于典型的农家妇女。她在心里嘀咕,那老头怎么会有一个如此像貌堂堂的儿子,并且也很难把那个五大三粗的悍妇与刚才的俊朗青年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听过张大妈讲出事情由来她才明白,原来“郝老拐”生有两女一儿,老伴死得早,他又在一次上山砍柴时摔断了腿,待女娃先后嫁人走了,本指望林娃子长大了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不料这娃死活要去当兵,头一年他爹没同意,这小子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同时达到出去参军的目的,挨到第二年征兵之前,他悄悄把邻队一个体力硕健的姑娘娶了过来,让她照顾家里,而后瞒天过海的硬是当兵去了。好在那媳妇能干活,里里外外一把手,老人再也没啥说道,而林娃与那女子的婚礼还是后来从部队请假回来补办的,现在他们的娃娃都有两三岁了。
听了大妈讲的闲话,夏雪有些理解,却也为那个林娃子的“壮举”有些惋惜,然而听过也就罢了,很快便忘了此事。后来夏雪在队里出工时还常常在田间地头看见过他,只是相对无语,并不在意,她又依然如故的打发起平淡无奇的日子。
但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某日,夏雪为买生活用品,也象往常一样到公社场镇上去赶集,那是夏秋雨季时节,在回来途中在趟过一道溪沟时,突遇山洪暴涨,她脚下一滑被卷入水中而冲出老远,险些淌入下游的洄水沱里,在同路乡民的齐声惊呼中,在紧要的危急关头,忽有一人跳下水奋力扑上前去一把将她抓住了,而且迅速将她带过了溪沟对面。夏雪惊魂失魄、落汤鸡似的站立不稳,加之又呛了好几口水,眼神迷散着未看清救她的是谁就晕了过去。
待她苏醒过来发现已躺在自家床上了。抬眼一看天色已晚,只见邻居张大妈正在煤油炉上熬着稀饭,床前的桌上放着一盘煎好的鸡蛋,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大妈见她有了动静急切的叫说:“娃呀,你终于醒啦,都几个时辰啰,怪吓人的!”说着她指了指煮好的饭道:“我看时候不早了,就帮你作了饭,快起来吃一点。”
夏雪吃力的撑起身子问:“张妈,我是咋回来的?”
“哎哟,你还不晓得呀,是垭口郝家的林娃子把你背回来的,”她拖着那特有的大嗓门道:“听说你滚到河沟里了,是他把你拉起来的,见你昏昏沉沉,浑身浇湿,就把我喊来给你换衣服、照看你,他看不方便,估摸你没啥事就走了。”
夏雪极力搜索记忆,半天才回想起落水的情景,并依稀觉得自己曾匍匐在一个宽厚地脊背之上……顿时觉得是郝林救了她,自己已欠下他好大一个人情。
事隔好几天,夏雪特意带了点自己舍不得吃的饼干到郝林家去,说是去看他们家的小孩,实际是想当面向他致谢。不巧林娃没在家,是他那敦厚朴实地媳妇接待了她,媳妇告诉说,队里通知林娃子有啥事到公社去了。夏雪不急,她想改天见面再道谢也不迟,但是一连好些日子在地里都没见到他的人影,禁不住一打听,才知道公社正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要搞引渠建坝的水利工程,抽调了一批青壮劳力和像郝林那样的退武军人到工地去了,末了,夏雪只好把感谢的事暂切放下不提。
而就在这段时间,生产队长的儿子把她盯上了。这小子俗称“孬(方言移音:pie)娃子”,是因为他娘生了好几个娃都没养成,有了他后就取了这个贱名指望好养活,果然这就留下了,由于是独苗队长很迁就他,所以这娃平时走东窜西、沾花惹草地十分霸道。而夏雪生得细皮嫩肉、模样俊俏,而且是有知识、又“洋气”的城里人,当他第一眼瞧见她来到队里时,就好似看到了仙女下凡,这与那些村姑对照起来如像是天鹅和野鸡,简直无法比拟,所以他垂涎夏雪很久了,一直有觊觎、非份之想。
近段时间他总想找机会接近夏雪,还假借他爹的名义,不是捧几个鸡蛋就是提一筐红苕上门来讨好,他那双山里人因柴烟熏得两睑猩红的眼眶,和那猥狎不敬的神态令夏雪十分反感,但又不好驳了队长的面子,只好勉强应承。就这样三番两回,有次他居然斗胆关上门一把将她抱住了,夏雪急呼救命,并顽抗了好一阵险些被他得逞,恰好这时房前的晒坝上来了几个玩童,听到呼声都跑了过来,一个个爬上窗户往里探望,他才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手。乘此时夏雪一把拿起了桌上的菜刀,怒指说再敢过来就砍他,这小子仍不死心,继续与她僵持着,直到夏雪叫嚷着要到公社去告他,他才一下软了,因为那时上面有政策,说是奸污女知青是与“破坏军婚”一样的大罪,是要下大狱的,无奈,他只得连声告饶的仓惶逃走了。
打那以后,夏雪的心里就滋生出一种强烈地需要被保护的意识,不由间会想起那个救过她命的郝林,她猜想一个复原军人必定是有正义感的,如果他在队上知道孬娃子来这里耍流氓,一定会像上次那样挺身而出来解救自己,就这样她时常幻入一种假设地冥想之中,渐渐地郝林的身影在她心目中变得明晰高大起来,乃至促发起急于想见他的一种愿望。然而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只有每天重复着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偶而还发现孬娃子躲在老远偷窥,使她心里总是发怵,有时她壮着胆子捡起石头朝他仍去,那狗东西也就识趣地赶快消失,时光就这样在担惊受怕和百无聊奈中慢慢流逝。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一次夏雪又到公社去逢场赶集,在场街上她碰见一个分在其它生产队,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女知青,就陪她在狭窄的街道上,在接踵交臂的人群中瞎逛了好长时间,后来又坐在街沿边怨天忧人地闲聊了许久,直到人稀场散才将她送到街的尽头走了。当她正准备起身回队时,忽有一人挡在前面冒失的喊了一声:“喂,这不是我们队上的知青吗,也来赶场哈。”
夏雪抬眼一看原来是郝林,偶然相逢使她一时有些拘促,倒是那林娃略显大方地问道:“好久不见,你还好吧?”
夏雪恍然回过神来,赶紧回应说:“谢谢你还能记得我,这么久你跑哪里去了?我还找过你哩。”
林娃说:“噢,我到公社水坝上去了,你说找我,有啥事吗?”
夏雪夸张的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哟,我当然应该感谢你嘛。”
林娃说:“你说那事呀,没啥,哪个遇见都会救你的,其实那天我很担心你,后来看你真的没事,我才放心走了。”说着他调侃地问:“你说应该感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夏雪当真的想想说:“这样,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林娃赶紧回绝:“不用,不用,我是开玩笑的。”
夏雪反倒坚决起来:“不行,这顿饭我一定要请你,不然总觉得欠你的,反正也快到吃饭时间了,干脆现在我们就去下馆子吃饭。”
林娃见她认真了转身欲走,却被她生生地拉住硬是带进了一家饭馆。
当坐下点好酒菜后,林娃像是真的饿了,就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打趣地说:“你也快吃呀,一顿饭换一条命值哟。”
夏雪见他性格豪爽、言语健谈,一时高兴也陪他喝起酒来。几杯下肚后两个年轻人就象久逢知己的朋友拉开了话匣。夏雪谈起自己的身世,述说心中的愁怨,林娃则大讲他在部队如何立功授奖,走过多少城市,见过多少世面。从讲述中夏雪知道他在部队是一名工程兵班长,曾参与过国家几项大型工程的爆破任务,这次公社筑坝修渠正好发挥他的特长,派他专门负责开山破石的放炮任务。
看他说到兴奋时两眼生辉,热了竟无所顾忌地脱了外套敞快起来,在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字样的背心映衬下,他那黝黑发亮地肌肤显得格外健康生动,不由令夏雪心头一悸,悄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怀。
吃罢晚饭林娃突然想起说:“今晚公社要演路天电影,说是‘平原游击队’,我们是从工地专程通知回来的,你也去看吧。”
夏雪说:“算了,看完都半夜了,我咋回去?”林娃考虑了一下问:“你究竟想不想看?”
《红肚兜》
前 言
人的一生能够拥有梦想是幸福的,就像生命之舟标注了航线,又如漂泊之人灵魂有了家园。我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对于文学的执着向往,因为我本平庸,以为拿捏文字可以改变自己,证明我人生一世的实际意义。
然而我又不甘媚俗,不愿跟风那些流行元素,蛊撰一些玄幻灵异、时空穿越的魅惑来吸人眼球,也不想串烧那种颠倒阴阳、调侃爱情的闹剧来给这个本已滥情的文化市场添堵。因为我心里始终保持着一份初衷的宁静,总想以一种传统的、纯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自我意识,并以其点滴笔墨折射时代脉络,勾画人性本质,试图达到反思社会现实、启迪世人感悟的目的,如此而已。
但是我又摆脱不了男欢女爱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只是不想屈就那些鸡零狗碎的闲情逸事,也无意窠臼那种皆大欢欣、圆满结局的套路喜剧。有人说悲剧能够洞穿人的内心柔软神经,更能呼唤人性良知而产生震撼效应。因而,根据鲁迅先生对于悲剧的定义: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以此原理,本人凭借年近半百的所见所闻,并在捕捉生活原型的基础之上,经过耗时多年,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总算完成了这部悲情小说,旨在以故事贯穿历史取胜,以情节大喜大悲感人,聊以碎岁,以飨读者。
由于本文的笔调对于社会伦理的常规描写有所突破,可能会引起部份读者的不适或非议,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这也不失为对文学领域的一种大胆尝试,欢迎读者批判性的鉴赏,如果这粒试水之石能够击起文海一丝涟漪,也就不枉我常年青灯孤影、咬文嚼字地苦苦追逐文学之梦了。
作者(代序)
目 录
姊妹篇(上部)
一、 古城发生离奇事件 法制编辑追根溯源
二、 下乡知青前途无望 空虚迷茫坠入歧情
三、 不幸身孕诚惶诚恐 万般无奈遁入深山
四、 寄身猎户私生一子 高考中榜挥泪而去
五、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遗子失踪生死未卜
姊妹篇(下部)
六、 还原真相教授探监 女犯原是商界名流
七、 专职司机兼当随秘 孤男寡女暗相心仪
八、 误入骗局企业受损 急中生智共赴危难
九、 勇斗地虎化险为夷 两情相悦春风几度
十、 两好合一欲结连理 道破孽缘情何以堪
十一、惟恐毁誉避之不及 身陷迷情无以自拔
十二、寻机发财借鸡下蛋 闯下债祸溜之大吉
十三、有恃无恐三番要挟 反目成仇顿生邪念
十四、有心无胆顺流逆流 真相乍现急转直下
十五、蓄意谋杀走向不归 巧释迷雾欲盖弥彰
十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铁窗囹圄悔恨交加
尾 声
姊妹篇(上部)
一
古城发生离奇事件
法制编辑追根溯源
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相距之间,在我国西北方向那些山川、河流相互交融的沃土之上,有一座远近闻名、谓之“萌州”的内陆古城。由于千年历史文化的蕴润,这里的世俗民风一贯崇尚传统德化教育,即便是倍受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的生活态度依然怀古守旧。就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在相交织、传统与现实相碰撞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惊世骇俗的离奇事件,其内幕不仅涉及命案,而且伤及到社会伦理的基本道德规范,事发时兀然引起舆论一派哗然,成为当地旷古至今的爆炸性新闻。
21世纪初页的一个清明节,在萌州郊区的公墓之中,随着四围烟雾缭绕、鞭炮炸鸣的祭祀氛围,一位简发素服、龄近半百的中年妇女,手持大束鲜花夹带着些许什物,穿过中路熙嚷的人群拾级而上,此人是本地一名中学教师,她就那是那起轰动性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由于那场变故使她一次失去了两个直系亲人,其后人们发现,但凡年终岁末或上坟时节,她都务必赶来亡者墓地凭吊祭奠,也许是寄托哀思,亦或是排遣负疚心理,就这样她重复演绎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苦情景。
只见她来到半坡深处并排的两座墓前站定,习惯的将花束分别向两墓摆开,然后只在一座坟前上香、焚纸。做完这些她从怀中取出了一条红色的、好似肚兜形状的布巾挂于坟头,盯着那物她两眼垂泪,伫立着久久不愿离去。正在此时,从她身后轻轻传出一句问话声来:“请问是夏雪老师吗?”
夏雪蓦然回首,发现身后已站着一男一女两个陌生的人。看那女的年轻、时尚,男的却是一位皓首童颜的长者,两人正朝她微微点头致意。瞧着两位不速之客,夏雪迟疑的回应:“是我,你们是……”
那女子首先开腔道:“夏老师,我是本市报社记者,我们打听到清明节你可能会来扫墓,想不到你果然在此。”她指了指身旁的长者说:“是这样,我今天陪这位前辈来找你,给你介绍一下,他是省法制报的主编,这次是专程从省城赶来见你的。”
长者慈眉善目,年纪约六十开外,一副学者模样。听到介绍自己,立刻取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夏雪接过认真看看,又仔细端详近前之人,半响竟然惊异地叫出声来:“哦!是丹阳教授,您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真是您来找我吗?”那语气似曾相识。
长者听她的话外有音,也打量起她来,并回问道:“你认识我?”
夏雪浅笑着说:“我早先见过你,只是时间太久,差点认不出了。”
长者十分兴致的又问:“噢,什么时候,在哪里?”
夏雪尽量回忆着说:“那还是文革过后刚恢复高考不久,我在华东师范学院上学时,院校曾经请你来给我们作过司法讲座,当时听说你在什么政法学院任高级讲师,曾经给我们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教授眼睛一亮,频频点头说:“喔,好象有这么回事,真是太巧了,你的记忆真好。”
夏雪直接问道:“你老现在可好,怎么不上讲台,改当主编了?”
教授解释说:“我已退休了,但身体还好,现在被聘为这家法制报社的责任编辑,同时做些法学研究。”说着他话锋一转“实不想瞒,我这次来萌州,就是为你们家的事想当面采访一下你,想不到我们还有师生之缘呢。”
“采访我什么?”夏雪诧意的问。
那名女记者接话说:“想必这墓地中埋的是你的亲人吧,丹阳老师就是为这墓中的人和事想了解一些情况,你看可以和他谈谈吗?”
闻此言夏雪黯然神伤,推辞说:“不,我不想谈过去,往事如烟,希望你们也不要再提那些事好吗,实在抱歉。”
一时塞语,良久,教授开始劝慰道:“夏雪,虽然你们家的事在法律上已经盖棺论定,但是对其事实由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也曾引起舆论界一些不实报道,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想对这起案件的因果关系进行明辩梳理,也就是说这个事件不仅是你们家的悲剧,也是时代变迁的产物,我们将以客观的、高度负责的态度还原事实真相,还舆论一个公正的说法。”
夏雪一脸戚惶的面朝着坟墓不再言语。此时教授才注意到眼前有两座紧捱的墓穴,一并摆放着同样的花束,其中一座墓碑上篆刻着“赵满强之墓”的简单字样,左下角只有一个称作“赵老爹”的人立碑署名。而另一座墓除了龛型具全外,却没有竖碑和片字铭文。他不禁试探着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叫赵满强的人就是你的亲生孩子吧。”
一听“亲生孩子”夏雪两眼涌动泪花,嘴唇嗫嚅着欲说还休,她的情绪变化证实了教授的说法。
女记者抬眼看见墓顶上挂着的那条红色小物件,不由好奇地走拢去捻开来看,只见那上面现出了几个残缺的“红卫兵”字样,虽然败了颜色,但依然明晰可辨,她问:“这是啥东西,它代表什么呀?”
夏雪缓缓地上前取下那物捏在手中摩挲着,半阵才说出话来:“这是墓中的娃出生时我给他缝的肚兜,是用我早先戴过的一只‘红卫兵’袖套改做的。”
女记者和教授相互对视了一下,觉得那肚兜一定有不少故事,但是此地不便追述,教授就朝近旁的那座无字墓移步过去问道:“喏,这座没有碑文的墓又是谁的呢?”
夏雪喃喃地说:“她是谁?她就是我的亲妹儿,夏霖。”言罢抑止不住大泪滂沱。
教授甚感愕然,十分不解的说:“我们都知道夏霖虽然被判了极刑,但并没有执行,后来是改判了的,为何一定要给她置下这块墓地呢?”
“按当时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我们还以为她会随强娃一起去了……”夏雪伤心地擦着眼泪说:“所以事先也在这里置了这块地……后来才知道她改了刑,但考虑到她很难生还出狱,监狱又不许探视,她就如已死而没埋的人,因此这地暂时还没退,就算是个念象吧。”
“这样呀!”教授释然的点点头,接着再次提出说:“为了给已死和未死之人一个公平的说法,为了消除舆论对你本人的误解,我建议你还是正式接受我们的采访。”
夏雪依然回绝教授的要求,她说:“算了吧,往事不堪回首,我想还是让那些事连同这墓一道深埋地下,随着时间慢慢消亡、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
场面有些尴尬,女记者插言道:“夏老师,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们也知道,就因为你们家的事让世人对你产生了许多偏见,连学校也迫于舆论压力暂停了你任教的资格,你还有什么可回避的,也许我们可以帮你澄清一些事实,消除别人的恶语中伤,换得社会对你的理解和同情。”
夏雪有所触动,她想是呀,自从遗失的亲生骨肉命归黄泉、自己的同胞妹子锒铛入狱,仿佛一夜之间她便从一名受人尊重的人民教师沦为遭人唾弃的异类。一年多来她的内心一直陷入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而这场悲剧的起源又与自己年轻时那青涩蒙昧的少女情怀有关,所以面对世上的流言蜚语她有口难辩,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她两鬓斑白,容颜过早的衰老了,长此以往如何才是尽头。
教授接着说:“夏雪,希望你能勇敢面对现实,过去在你身上发生的事不一定就是你的错,所以你何不讲出实情,以正视听,这样或许有益于你的生活,有利于今后走好脚下的路。”
这番话似乎对夏雪很有效,经再三考虑,后来终于答应了教授的采访。于是三人一行出了公墓园陵,搭乘女记者的小车去到萌州城内一处僻静的茶庄,并由她招呼着定下了一个包间。但是待他们刚坐定,沏上茶饮,女记者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而后她歉意地对教授说:“丹阳老师,刚才我们社长通知说市里有个重要采访任务,必须得去,不好意思,这里我先不陪你了,等我那边一完事就来接你,你看行吗?”
教授随即点头道:“行、行,你去忙吧,我这里不要紧的。”
女记者起身说:“那好,一会儿再联系哈。”并对夏雪道了声:“夏老师,你们慢慢聊,放心,是啥就说啥,没关系的。”说着摆摆手匆匆走了。
这样就留下了教授和夏雪单独谈话,当两人调整好心态,在他的循循善诱之下,在开启的录音机面前,夏雪慢慢打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心扉,大胆地讲出了自己雪藏二十多年、鲜为人知的那段畸情悲悯的故事。
二
下乡知青前途无望
空虚迷茫坠入畸情
故事是从夏雪的名字开始讲起的,夏雪问教授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含义?教授惑然。她便解释说自己本是知识份子家庭出生,父亲是在旧社会上过“洋学堂”的文化人,解放后又好在报刊上发表点文章,由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被迫接受劳动改造。老爸熟知“窦娥”喊冤、六月下雪的历史悲剧,他说自己比窦娥还冤,刚好那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因为姓夏,又是女娃,他就给孩子取名为夏雪,象征夏天之雪,以此借谕自己的冤屈。
在生养子女的问题上,父亲一直想要个男孩。后来间隔多年,妈妈前后又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仍都是女娃,中间那个因病夭折了,剩下一个是在一九六九年降生的,因为那是在“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之年,父亲以为可以春风化雨,使自己的政治处境得到改善,因此就给这个迟来的女孩取了个名字叫夏霖。而存活的夏雪与夏霖两姊妹年龄相差竟有十一、二岁。
妹妹的出生并非天降甘霖,在政治上父亲依然受到旁人的偏见和歧视,他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长期的郁郁寡欢之中心劳成疾,未到中年便一病不起而撒手人寰。留下妈妈带着两女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直到夏雪高中毕业,随着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浪潮,被有关组织分配到边远的山区农村去插队落户。
与夏雪一道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学均是各个学校汇集而来的应届毕业生。接收他们下放的那个地方叫“水磨公社”,那是因为当地一条小河上有个很大的水碾石磨而得名。可能是考虑到女孩的生理条件,夏雪与另外一位女生被公社安排到大山脚下一个生产小队上,这个队距公社约十来里路,位于两座大山之间的狭长地带,由于这里遍布柿树,所以地名就叫“柿树垭”。
队里安置夏雪两人的住处是由粮食仓库隔搭的一角简易陋室,屋内的门窗四处透风,房顶上雨雪可以飘进,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她们跟着当地农民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动。由于每天干着机械而繁重的农活,另一位女生熬不住便经常借故跑回家去。夏雪比较坚强,她知道家里帮不了自己,以为只要好好表现就可以被公社推荐出去安排工作。但是事与愿违,一两年后消息纷纷传来,其它队上那些表现好或不好的知青被调走不少,就连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子也因家庭成份好而与她拜拜回城去了。
后来夏雪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有两次单位来招工都因“政审”条件而不能过关。由此她看到现实与理想有多么大的差异,以至陷入深深的困惑与迷茫之中。似乎是“看破红尘”,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起来,也开始借故赖工,常常蜗居在那泥巴墙内的斗室里恹恹的不肯下床。
有那么一天,雨过天晴,屋外有几只小鸟在啁啾啭啼,夏雪的童心被唤起,她打开房门慵慵的伸了个懒腰,就朝房前的一棵大柿树下去寻那些鸟儿,当那些鸟惊飞起来,她顺着飞往的方向看去,忽然发现那边有一个身着橄榄绿军装的青年正向这边健步走来,虽然没戴领章、帽徽,但看那人挺有精神。夏雪不觉眼睛一亮,因为在这穷乡僻壤的山窝里日常所见的都是与泥土一色的农民,乍眼见到如此衣着整洁、昂首走路的人不由令她刮目相看。那人经过房前,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在云隙透过的一缕阳光之下,她看到了一张五官端正、颇具英气的面孔,当他走过时竟也特意的回眸一瞥,仿佛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使夏雪盯着他的后背愣愣的好久未能将视线挪开。
恰好这时垓坎下一位相邻的张姓大妈打猪草回来,夏雪抑止不住好奇,便向她打听刚走过去的人是谁。大妈歇下脚瞅了瞅那个远去的背影说:“哦,那是垭口‘郝老拐’家的儿子从部队复员回来了,叫郝林,我们喊他林娃子,这下可好,他们家又添劳力啰。”
“郝老拐,就是那个瘸了腿杵着拐杖的老人吗?”在夏雪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性格古怪的残疾人,还知道他儿子是在当兵,有一个儿媳在家务农,那媳妇体壮腰圆,属于典型的农家妇女。她在心里嘀咕,那老头怎么会有一个如此像貌堂堂的儿子,并且也很难把那个五大三粗的悍妇与刚才的俊朗青年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听过张大妈讲出事情由来她才明白,原来“郝老拐”生有两女一儿,老伴死得早,他又在一次上山砍柴时摔断了腿,待女娃先后嫁人走了,本指望林娃子长大了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不料这娃死活要去当兵,头一年他爹没同意,这小子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同时达到出去参军的目的,挨到第二年征兵之前,他悄悄把邻队一个体力硕健的姑娘娶了过来,让她照顾家里,而后瞒天过海的硬是当兵去了。好在那媳妇能干活,里里外外一把手,老人再也没啥说道,而林娃与那女子的婚礼还是后来从部队请假回来补办的,现在他们的娃娃都有两三岁了。
听了大妈讲的闲话,夏雪有些理解,却也为那个林娃子的“壮举”有些惋惜,然而听过也就罢了,很快便忘了此事。后来夏雪在队里出工时还常常在田间地头看见过他,只是相对无语,并不在意,她又依然如故的打发起平淡无奇的日子。
但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某日,夏雪为买生活用品,也象往常一样到公社场镇上去赶集,那是夏秋雨季时节,在回来途中在趟过一道溪沟时,突遇山洪暴涨,她脚下一滑被卷入水中而冲出老远,险些淌入下游的洄水沱里,在同路乡民的齐声惊呼中,在紧要的危急关头,忽有一人跳下水奋力扑上前去一把将她抓住了,而且迅速将她带过了溪沟对面。夏雪惊魂失魄、落汤鸡似的站立不稳,加之又呛了好几口水,眼神迷散着未看清救她的是谁就晕了过去。
待她苏醒过来发现已躺在自家床上了。抬眼一看天色已晚,只见邻居张大妈正在煤油炉上熬着稀饭,床前的桌上放着一盘煎好的鸡蛋,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大妈见她有了动静急切的叫说:“娃呀,你终于醒啦,都几个时辰啰,怪吓人的!”说着她指了指煮好的饭道:“我看时候不早了,就帮你作了饭,快起来吃一点。”
夏雪吃力的撑起身子问:“张妈,我是咋回来的?”
“哎哟,你还不晓得呀,是垭口郝家的林娃子把你背回来的,”她拖着那特有的大嗓门道:“听说你滚到河沟里了,是他把你拉起来的,见你昏昏沉沉,浑身浇湿,就把我喊来给你换衣服、照看你,他看不方便,估摸你没啥事就走了。”
夏雪极力搜索记忆,半天才回想起落水的情景,并依稀觉得自己曾匍匐在一个宽厚地脊背之上……顿时觉得是郝林救了她,自己已欠下他好大一个人情。
事隔好几天,夏雪特意带了点自己舍不得吃的饼干到郝林家去,说是去看他们家的小孩,实际是想当面向他致谢。不巧林娃没在家,是他那敦厚朴实地媳妇接待了她,媳妇告诉说,队里通知林娃子有啥事到公社去了。夏雪不急,她想改天见面再道谢也不迟,但是一连好些日子在地里都没见到他的人影,禁不住一打听,才知道公社正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要搞引渠建坝的水利工程,抽调了一批青壮劳力和像郝林那样的退武军人到工地去了,末了,夏雪只好把感谢的事暂切放下不提。
而就在这段时间,生产队长的儿子把她盯上了。这小子俗称“孬(方言移音:pie)娃子”,是因为他娘生了好几个娃都没养成,有了他后就取了这个贱名指望好养活,果然这就留下了,由于是独苗队长很迁就他,所以这娃平时走东窜西、沾花惹草地十分霸道。而夏雪生得细皮嫩肉、模样俊俏,而且是有知识、又“洋气”的城里人,当他第一眼瞧见她来到队里时,就好似看到了仙女下凡,这与那些村姑对照起来如像是天鹅和野鸡,简直无法比拟,所以他垂涎夏雪很久了,一直有觊觎、非份之想。
近段时间他总想找机会接近夏雪,还假借他爹的名义,不是捧几个鸡蛋就是提一筐红苕上门来讨好,他那双山里人因柴烟熏得两睑猩红的眼眶,和那猥狎不敬的神态令夏雪十分反感,但又不好驳了队长的面子,只好勉强应承。就这样三番两回,有次他居然斗胆关上门一把将她抱住了,夏雪急呼救命,并顽抗了好一阵险些被他得逞,恰好这时房前的晒坝上来了几个玩童,听到呼声都跑了过来,一个个爬上窗户往里探望,他才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手。乘此时夏雪一把拿起了桌上的菜刀,怒指说再敢过来就砍他,这小子仍不死心,继续与她僵持着,直到夏雪叫嚷着要到公社去告他,他才一下软了,因为那时上面有政策,说是奸污女知青是与“破坏军婚”一样的大罪,是要下大狱的,无奈,他只得连声告饶的仓惶逃走了。
打那以后,夏雪的心里就滋生出一种强烈地需要被保护的意识,不由间会想起那个救过她命的郝林,她猜想一个复原军人必定是有正义感的,如果他在队上知道孬娃子来这里耍流氓,一定会像上次那样挺身而出来解救自己,就这样她时常幻入一种假设地冥想之中,渐渐地郝林的身影在她心目中变得明晰高大起来,乃至促发起急于想见他的一种愿望。然而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只有每天重复着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偶而还发现孬娃子躲在老远偷窥,使她心里总是发怵,有时她壮着胆子捡起石头朝他仍去,那狗东西也就识趣地赶快消失,时光就这样在担惊受怕和百无聊奈中慢慢流逝。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一次夏雪又到公社去逢场赶集,在场街上她碰见一个分在其它生产队,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女知青,就陪她在狭窄的街道上,在接踵交臂的人群中瞎逛了好长时间,后来又坐在街沿边怨天忧人地闲聊了许久,直到人稀场散才将她送到街的尽头走了。当她正准备起身回队时,忽有一人挡在前面冒失的喊了一声:“喂,这不是我们队上的知青吗,也来赶场哈。”
夏雪抬眼一看原来是郝林,偶然相逢使她一时有些拘促,倒是那林娃略显大方地问道:“好久不见,你还好吧?”
夏雪恍然回过神来,赶紧回应说:“谢谢你还能记得我,这么久你跑哪里去了?我还找过你哩。”
林娃说:“噢,我到公社水坝上去了,你说找我,有啥事吗?”
夏雪夸张的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哟,我当然应该感谢你嘛。”
林娃说:“你说那事呀,没啥,哪个遇见都会救你的,其实那天我很担心你,后来看你真的没事,我才放心走了。”说着他调侃地问:“你说应该感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夏雪当真的想想说:“这样,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林娃赶紧回绝:“不用,不用,我是开玩笑的。”
夏雪反倒坚决起来:“不行,这顿饭我一定要请你,不然总觉得欠你的,反正也快到吃饭时间了,干脆现在我们就去下馆子吃饭。”
林娃见她认真了转身欲走,却被她生生地拉住硬是带进了一家饭馆。
当坐下点好酒菜后,林娃像是真的饿了,就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打趣地说:“你也快吃呀,一顿饭换一条命值哟。”
夏雪见他性格豪爽、言语健谈,一时高兴也陪他喝起酒来。几杯下肚后两个年轻人就象久逢知己的朋友拉开了话匣。夏雪谈起自己的身世,述说心中的愁怨,林娃则大讲他在部队如何立功授奖,走过多少城市,见过多少世面。从讲述中夏雪知道他在部队是一名工程兵班长,曾参与过国家几项大型工程的爆破任务,这次公社筑坝修渠正好发挥他的特长,派他专门负责开山破石的放炮任务。
看他说到兴奋时两眼生辉,热了竟无所顾忌地脱了外套敞快起来,在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字样的背心映衬下,他那黝黑发亮地肌肤显得格外健康生动,不由令夏雪心头一悸,悄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怀。
吃罢晚饭林娃突然想起说:“今晚公社要演路天电影,说是‘平原游击队’,我们是从工地专程通知回来的,你也去看吧。”
夏雪说:“算了,看完都半夜了,我咋回去?”林娃考虑了一下问:“你究竟想不想看?”
到头了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