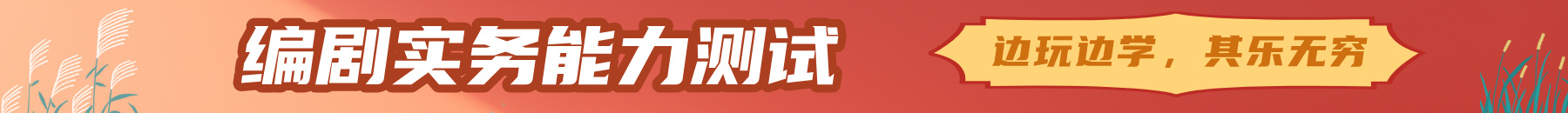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普通授权
字数:44306
阅读:2528
发表:2023/8/19
都市,农村
小说
三层口罩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本作品已在华语剧本网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版权登记,登记2023-B-03097】
“我这辈子是俺奶害的,你男姥太和你外姥爷想让我上学认俩字,俺奶——就是你女姥太是一直打坝子阻拦说,‘小闺女家上什么学?读什么书?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会点针线活、能洗衣会做饭就行了。’”母亲感慨的语气并无丝毫的怨意。
她看着书上一个个黑色的方块字,“现在成了睁眼瞎,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哎!那时的人真太憨了。”
母亲有幸上过一段时间的夜校,却因为家庭的状况、最后还是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但那段时间成了母亲最幸福、最美好快乐的回忆。
“临上轿扎耳眼,事先就要把第天的东西准备好。”看着我早上上学时急里慌张的找东忘西的样子,记得母亲总会这么嗔怪的说,“整天提着耳朵都教不好,东西要有收管,用时才好找。”
“我这辈子是俺奶害的,你男姥太和你外姥爷想让我上学认俩字,俺奶——就是你女姥太是一直打坝子阻拦说,‘小闺女家上什么学?读什么书?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会点针线活、能洗衣会做饭就行了。’”母亲感慨的语气并无丝毫的怨意。
她看着书上一个个黑色的方块字,“现在成了睁眼瞎,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哎!那时的人真太憨了。”
母亲有幸上过一段时间的夜校,却因为家庭的状况、最后还是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但那段时间成了母亲最幸福、最美好快乐的回忆。
我外姥爷早期的家境很好,有长工和大领,做的香火生意远销好几百里外的省县。
饱读诗书的外姥爷既聪明儒雅又俊朗风趣,上了十二年的私塾的外姥爷无论吟诗作对还是泼墨挥毫——他是信手拈来。
从学堂回家的一次路上,十多岁的外姥爷不小心的踩死了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黄鸡,他回到家在鸡圈里逮住一只老母鸡,抱着它回到了刚才踩死小黄鸡的地方,把怀中的老母鸡往地上一放,然后就宽心的转身向家里走去。
家道在动荡的年代中慢慢地衰退,最后被迫终止了祖传的香火生意,一肚文墨的外姥爷为了生计——自学并做起了贴大饼、做油馍、花卷小吃等糊口的小生意,也曾溜街挑担卖过香油。
做压面条生意时,因为母亲是老大,下面有六个年幼的弟妹,不足十二岁的母亲已像个大人样承担起一份家庭的责任。
“这么俊的孩子会被压成矬子的。”
“长不高了。”
“俊兰要变成小矮子,可惜呀!”
“……”
母亲遗传了外老爷的相貌,大眼睛,双眼皮,五官端正,比例协调,特得了个“俊兰”的称号。
母亲一手扶着顶在头上的装满了新鲜面条的大圆簸箕,另一只向外伸展的手在极力的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脸色涨红、神情紧张的母亲每天穿梭在狭窄的小街上,那瘦小赢弱的身体消失在两边此起彼伏的买卖的吆喝中,四邻跟路人对着母亲的背影每每都会不由得摇头叹息。
那些消逝的一幅幅生动淳朴、触人心弦的、生命力旺盛的——多视角的风景画绘会出了小街浓香醇厚的灵魂。
那时做小买卖的人都是步行,来回二百多里的步程对外姥爷来说是平常之事,夜行昼赶、奔波劳碌的外老爷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愁眉苦脸。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不为耻,也无不可。”外姥爷说。
“地位虽低下,人品却不低俗,健全、高尚的人格是小弟你的骄傲。”闲时与外姥爷谈古论今、对饮畅谈的好友回说。
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的外姥爷——脸上始终挂着恬淡的笑。儒雅的气质和骨子里的清高没因艰辛的生计而消退,重压下的生活好像让他在坚强的同时愈发的淡定自若了。
“他爷,今天吃什么?”
“他爷,多加件衣服,变天了。”
“他爷,茶泡好了。”
“太爷,吃饭吧!”
“他爷,合胃口吗?”
“……”
打小就过来的外姥姥应算是童养媳吧!善良软糯的外姥姥对外姥爷是即尊崇又敬重,低眉顺眼的百依百顺,生活上对外老爷倍是体贴,那极度呵护、关爱的神情如同慈母。
只要别人喜欢,自己再珍爱的东西——姥外爷总是眉头不皱,笑盈盈地执意相赠。姥外爷在他过世后,只留下一些别人挑剩的书跟几件简朴的衣服。
看书是外姥爷闲暇之余的一大嗜好和最大的乐趣,也是他生命中所有事项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茅屋外,红褐色的竹椅上坐着头戴灰色鸭舌帽的外姥爷。他的鼻子上卡着一副像掉下似的发黄的老花镜,他捧着书,微低着头,温暖的金色阳光斜洒在心神俱静的外老爷那端正的身姿上。
不远处,黑褐色的手压水井恬静的伸着长嘴巴,磨的黑亮的压水的铁把柄在阳光下白光闪晃。旁边那棵茂盛低矮的无花果树上——交错的冒出一个个喜人的青红果实。它时而又以光秃、粗糙、历练岁月的沧桑姿态——衬映在外老爷的身侧。这些静谧温馨的画面散发出文化所内蕴的圣洁之光。
这深深印在脑中的场景是我心中的圣地。
“能大多少?小又能小多少?”那时的鸡蛋论个卖,谁都想挑大的买。外老爷看不惯家人在鸡蛋筐里挑来拣去的样子,也不赞成家人讨价还价的习性。
其实买东西不问价不讲价的外姥爷——生活一点都不宽裕。他买东西的神情反似非常感激卖家对他的照顾和青睐,他也从不计较买回的东西不是量少就是质差。只能维持温饱的他在卖家没法找零时,会主动的不要并慌张的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转身走掉。
从来不怨命运之错
不怕旅途多坎坷
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
错了我也不悔过
人生本来苦恼已多
再多一次又如何
……
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由梁立人作词、何国杰作曲,翁素英演唱的歌曲。
耄耋之年的外老爷对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主题曲中的这几句词是尤为喜爱。
“写的好。”每次听到这首歌,他就会赞赏的说,“人生苦恼本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呢?”外姥爷的声音中透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故事和他内心深处的感慨。
虢国夫人承主恩
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
淡扫蛾眉朝至尊
这首唐代张祜的贬讽杨玉环三姐的诗,外姥爷分解出自己所赏析且提倡的——不擦脂粉、不特意修饰自己外貌的一种自然之美。
他的这种分解和理念对我影响至深。
临近年关,写春联是外老爷的一大盛事。深受外姥爷熏陶的哥哥从小就是外姥爷的小帮手,他的任务直至延续到外姥爷过世。被外老爷熏染的哥哥传承了他的喜书、爱书与写字。
屏息沉气的外姥爷手腕灵转、收放自如的在一张张裁好的红纸上挥毫泼墨,每每看呆了哥哥看傻了啥都不懂的我。
外姥爷一直起身,哥哥便小心地把刚写好的——墨迹淋漓的春联平捧着——然后再小心地放在平整的地上。
偶尔参与进来的我是激动又骄傲,从堂屋到小院——地上铺满了一溜溜、一排排墨迹已干或未干的大红春联。年的喜悦已扑面而来,一句句祝福吉祥的话语令人踏实、心安又快乐。
对子女在各自的家庭和他(她)们在外面等所发生矛盾的时候,外姥爷从不护短且主动搅过,一直是责骂儿子护媳妇,数落闺女偏女婿。
“我的过,我的不是,实在是对不起。”
“……”
外姥爷不住的用责己的话抚慰因对自己的子女或家人不满而产生怒气的任何人,直至对方平息怨气,错在对方他也是如此。
“做人不能拿‘不是’当理讲。”外姥爷说这话时的神情是很严肃的。
母亲同父亲成家后与外姥爷的家仅一路之隔,使我们有幸和外姥爷、外姥姥有朝夕相处的机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老爷的脾气在最后的岁月里变得有些乖张、暴躁,但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完美和对他的崇敬之情。
出嫁那天,外姥爷对我说的那句话会偶尔从心底泛出在耳边响起,“这是你的第二个娘家。”
“现在的人享着以前朝廷也没享上的福。”母亲羡慕的看着现在人的生活,“做梦也想不到的日子,干活时喝号子都想着有一天能过上有电灯、用电话的日子。”
张大妈,李大娘
幸福院里拉家常
自从来了共产党
一天到比一天强
一个老头九十九
睡在床上不能走
听说中国全解放
出门就把秧歌扭
唆啦唆,哆啦哆
说声大姐你不用愁
人民解放得自由
有高楼和大厦呀
有洋犁子和洋耙
电灯泡子碗口大
你要不信就看看吧
说着说着——深入母亲骨髓的号子会舒畅自然的一泻而出,押韵明快的词语直入心底,触拨原始本性的心魂。
母亲即兴即景的号子在生产队时是随口就来,它在激发社员们劳动热情的同时又明显的增强了热烈的生产气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融汇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一个大姐才十七
四年没取二十一
说个丈夫才十岁
算来算去大十一
有一天,夫妻二人去挑水
一头高来一头低
大姐在后面一使劲
捅的丈夫牙啃泥
丈夫起来很生气
上面拳打脚又踢
南面来了个拾粪的
走到面前笑嘻嘻
老头说
要管孩子回家管
不要在井沿立规距
丈夫听了心生气
骂声老头老东西‘
不要看她年龄大
我是她丈夫,她是我妻
老头耳背没听清
晚娘也该打你的
就是晚娘也该打你的
本地的一个老者向田间走来,他马上成为母亲即兴号子的题材,家境不错的老者在孩提的时候,父母就为他娶了一个大他好多岁的媳妇,惹出过不少让人学舌的笑话。
母亲不用担心她的号子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其他(她)的社员同样不用操心自己无所顾忌的笑会引发当事人的愤懑,开心的哄笑取闹反令大家消除了隔阂与不快,焕发的身心使人忘掉了疲累和愁闷,在它的影响下陡增的力量会从体内不断地再次迸发。
打起精神干呐
喝起号子缠呀
力气是福财呀
使了它就来
同志们呐
加油干呀
洋犁耕的深呐
每亩双千斤呀
小麦不种好
来年怎么吃饱呀
同志们呐
加油干呀
超产要奖励呐
她看着书上一个个黑色的方块字,“现在成了睁眼瞎,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哎!那时的人真太憨了。”
母亲有幸上过一段时间的夜校,却因为家庭的状况、最后还是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但那段时间成了母亲最幸福、最美好快乐的回忆。
“临上轿扎耳眼,事先就要把第天的东西准备好。”看着我早上上学时急里慌张的找东忘西的样子,记得母亲总会这么嗔怪的说,“整天提着耳朵都教不好,东西要有收管,用时才好找。”
“我这辈子是俺奶害的,你男姥太和你外姥爷想让我上学认俩字,俺奶——就是你女姥太是一直打坝子阻拦说,‘小闺女家上什么学?读什么书?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会点针线活、能洗衣会做饭就行了。’”母亲感慨的语气并无丝毫的怨意。
她看着书上一个个黑色的方块字,“现在成了睁眼瞎,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哎!那时的人真太憨了。”
母亲有幸上过一段时间的夜校,却因为家庭的状况、最后还是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但那段时间成了母亲最幸福、最美好快乐的回忆。
我外姥爷早期的家境很好,有长工和大领,做的香火生意远销好几百里外的省县。
饱读诗书的外姥爷既聪明儒雅又俊朗风趣,上了十二年的私塾的外姥爷无论吟诗作对还是泼墨挥毫——他是信手拈来。
从学堂回家的一次路上,十多岁的外姥爷不小心的踩死了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黄鸡,他回到家在鸡圈里逮住一只老母鸡,抱着它回到了刚才踩死小黄鸡的地方,把怀中的老母鸡往地上一放,然后就宽心的转身向家里走去。
家道在动荡的年代中慢慢地衰退,最后被迫终止了祖传的香火生意,一肚文墨的外姥爷为了生计——自学并做起了贴大饼、做油馍、花卷小吃等糊口的小生意,也曾溜街挑担卖过香油。
做压面条生意时,因为母亲是老大,下面有六个年幼的弟妹,不足十二岁的母亲已像个大人样承担起一份家庭的责任。
“这么俊的孩子会被压成矬子的。”
“长不高了。”
“俊兰要变成小矮子,可惜呀!”
“……”
母亲遗传了外老爷的相貌,大眼睛,双眼皮,五官端正,比例协调,特得了个“俊兰”的称号。
母亲一手扶着顶在头上的装满了新鲜面条的大圆簸箕,另一只向外伸展的手在极力的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脸色涨红、神情紧张的母亲每天穿梭在狭窄的小街上,那瘦小赢弱的身体消失在两边此起彼伏的买卖的吆喝中,四邻跟路人对着母亲的背影每每都会不由得摇头叹息。
那些消逝的一幅幅生动淳朴、触人心弦的、生命力旺盛的——多视角的风景画绘会出了小街浓香醇厚的灵魂。
那时做小买卖的人都是步行,来回二百多里的步程对外姥爷来说是平常之事,夜行昼赶、奔波劳碌的外老爷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愁眉苦脸。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不为耻,也无不可。”外姥爷说。
“地位虽低下,人品却不低俗,健全、高尚的人格是小弟你的骄傲。”闲时与外姥爷谈古论今、对饮畅谈的好友回说。
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的外姥爷——脸上始终挂着恬淡的笑。儒雅的气质和骨子里的清高没因艰辛的生计而消退,重压下的生活好像让他在坚强的同时愈发的淡定自若了。
“他爷,今天吃什么?”
“他爷,多加件衣服,变天了。”
“他爷,茶泡好了。”
“太爷,吃饭吧!”
“他爷,合胃口吗?”
“……”
打小就过来的外姥姥应算是童养媳吧!善良软糯的外姥姥对外姥爷是即尊崇又敬重,低眉顺眼的百依百顺,生活上对外老爷倍是体贴,那极度呵护、关爱的神情如同慈母。
只要别人喜欢,自己再珍爱的东西——姥外爷总是眉头不皱,笑盈盈地执意相赠。姥外爷在他过世后,只留下一些别人挑剩的书跟几件简朴的衣服。
看书是外姥爷闲暇之余的一大嗜好和最大的乐趣,也是他生命中所有事项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茅屋外,红褐色的竹椅上坐着头戴灰色鸭舌帽的外姥爷。他的鼻子上卡着一副像掉下似的发黄的老花镜,他捧着书,微低着头,温暖的金色阳光斜洒在心神俱静的外老爷那端正的身姿上。
不远处,黑褐色的手压水井恬静的伸着长嘴巴,磨的黑亮的压水的铁把柄在阳光下白光闪晃。旁边那棵茂盛低矮的无花果树上——交错的冒出一个个喜人的青红果实。它时而又以光秃、粗糙、历练岁月的沧桑姿态——衬映在外老爷的身侧。这些静谧温馨的画面散发出文化所内蕴的圣洁之光。
这深深印在脑中的场景是我心中的圣地。
“能大多少?小又能小多少?”那时的鸡蛋论个卖,谁都想挑大的买。外老爷看不惯家人在鸡蛋筐里挑来拣去的样子,也不赞成家人讨价还价的习性。
其实买东西不问价不讲价的外姥爷——生活一点都不宽裕。他买东西的神情反似非常感激卖家对他的照顾和青睐,他也从不计较买回的东西不是量少就是质差。只能维持温饱的他在卖家没法找零时,会主动的不要并慌张的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转身走掉。
从来不怨命运之错
不怕旅途多坎坷
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
错了我也不悔过
人生本来苦恼已多
再多一次又如何
……
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由梁立人作词、何国杰作曲,翁素英演唱的歌曲。
耄耋之年的外老爷对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主题曲中的这几句词是尤为喜爱。
“写的好。”每次听到这首歌,他就会赞赏的说,“人生苦恼本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呢?”外姥爷的声音中透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故事和他内心深处的感慨。
虢国夫人承主恩
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
淡扫蛾眉朝至尊
这首唐代张祜的贬讽杨玉环三姐的诗,外姥爷分解出自己所赏析且提倡的——不擦脂粉、不特意修饰自己外貌的一种自然之美。
他的这种分解和理念对我影响至深。
临近年关,写春联是外老爷的一大盛事。深受外姥爷熏陶的哥哥从小就是外姥爷的小帮手,他的任务直至延续到外姥爷过世。被外老爷熏染的哥哥传承了他的喜书、爱书与写字。
屏息沉气的外姥爷手腕灵转、收放自如的在一张张裁好的红纸上挥毫泼墨,每每看呆了哥哥看傻了啥都不懂的我。
外姥爷一直起身,哥哥便小心地把刚写好的——墨迹淋漓的春联平捧着——然后再小心地放在平整的地上。
偶尔参与进来的我是激动又骄傲,从堂屋到小院——地上铺满了一溜溜、一排排墨迹已干或未干的大红春联。年的喜悦已扑面而来,一句句祝福吉祥的话语令人踏实、心安又快乐。
对子女在各自的家庭和他(她)们在外面等所发生矛盾的时候,外姥爷从不护短且主动搅过,一直是责骂儿子护媳妇,数落闺女偏女婿。
“我的过,我的不是,实在是对不起。”
“……”
外姥爷不住的用责己的话抚慰因对自己的子女或家人不满而产生怒气的任何人,直至对方平息怨气,错在对方他也是如此。
“做人不能拿‘不是’当理讲。”外姥爷说这话时的神情是很严肃的。
母亲同父亲成家后与外姥爷的家仅一路之隔,使我们有幸和外姥爷、外姥姥有朝夕相处的机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老爷的脾气在最后的岁月里变得有些乖张、暴躁,但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完美和对他的崇敬之情。
出嫁那天,外姥爷对我说的那句话会偶尔从心底泛出在耳边响起,“这是你的第二个娘家。”
“现在的人享着以前朝廷也没享上的福。”母亲羡慕的看着现在人的生活,“做梦也想不到的日子,干活时喝号子都想着有一天能过上有电灯、用电话的日子。”
张大妈,李大娘
幸福院里拉家常
自从来了共产党
一天到比一天强
一个老头九十九
睡在床上不能走
听说中国全解放
出门就把秧歌扭
唆啦唆,哆啦哆
说声大姐你不用愁
人民解放得自由
有高楼和大厦呀
有洋犁子和洋耙
电灯泡子碗口大
你要不信就看看吧
说着说着——深入母亲骨髓的号子会舒畅自然的一泻而出,押韵明快的词语直入心底,触拨原始本性的心魂。
母亲即兴即景的号子在生产队时是随口就来,它在激发社员们劳动热情的同时又明显的增强了热烈的生产气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融汇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一个大姐才十七
四年没取二十一
说个丈夫才十岁
算来算去大十一
有一天,夫妻二人去挑水
一头高来一头低
大姐在后面一使劲
捅的丈夫牙啃泥
丈夫起来很生气
上面拳打脚又踢
南面来了个拾粪的
走到面前笑嘻嘻
老头说
要管孩子回家管
不要在井沿立规距
丈夫听了心生气
骂声老头老东西‘
不要看她年龄大
我是她丈夫,她是我妻
老头耳背没听清
晚娘也该打你的
就是晚娘也该打你的
本地的一个老者向田间走来,他马上成为母亲即兴号子的题材,家境不错的老者在孩提的时候,父母就为他娶了一个大他好多岁的媳妇,惹出过不少让人学舌的笑话。
母亲不用担心她的号子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其他(她)的社员同样不用操心自己无所顾忌的笑会引发当事人的愤懑,开心的哄笑取闹反令大家消除了隔阂与不快,焕发的身心使人忘掉了疲累和愁闷,在它的影响下陡增的力量会从体内不断地再次迸发。
打起精神干呐
喝起号子缠呀
力气是福财呀
使了它就来
同志们呐
加油干呀
洋犁耕的深呐
每亩双千斤呀
小麦不种好
来年怎么吃饱呀
同志们呐
加油干呀
超产要奖励呐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