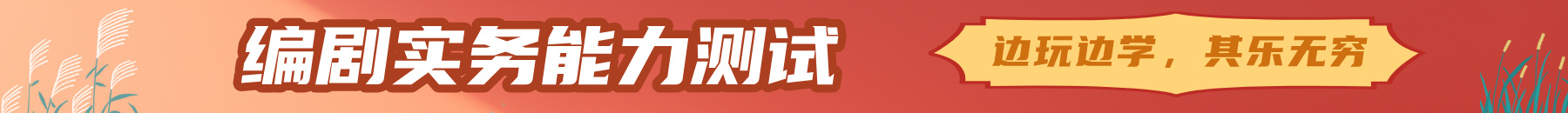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普通授权
字数:44306
阅读:2526
发表:2023/8/19
都市,农村
小说
三层口罩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本作品已在华语剧本网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版权登记,登记2023-B-03097】
减产要赔偿呀
庄稼要变成花
全靠人当家呀
母亲有时兴起——会不由得再次喝起往年的号子,她佝偻的身体迸出依旧洪亮、有劲又激昂的声音。
干劲十足的社员们在激奋、流畅的号子中如火如荼的于田间奋力的劳作,他(她)们充沛的精力、高涨的热情、质朴的精神同敦厚的面容——随着号子在脑中栩栩浮现。
“吃不饱,穿不暖,却有使不完的劲。不知愁,不知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现在的人什么都不缺,还……”
母亲经常感慨的想不通。
马铃薯产量高
五亩地收一蒲包
大的像铜钱
小的像胡椒
……
母亲的号子在诉说三年自然灾害失收的情景。
“孩子,行行好吧!给你大爷一口吃的吧!”快到家门口的母亲被自己的大爷我外姥爷的堂兄拦住,他枯竭的眼睛放出亮光,紧盯着母亲紧捂着的口袋。
“我的好孩子,揪一口也行,就一口。”看着躲闪的母亲,大外姥爷颤颤的上前一步。
“俊兰,好孩子,揪一口吧?就一口。”
母亲最终还是跑掉了,身后传来大外姥爷的声音,“孩子啊!俊兰,就给你大爷一口吧!”
大外姥爷微弱的声音和只剩一双眼睛的脸是母亲心中永远的伤痛。
“对不起他呀!有愧呀!怎么弄,没办法。”
口袋里半个杂粮窝头是母亲用血泪换来的,自己没舍得用牙硌一下。那天她从队里抽个空子偷跑了出来,是把这半个浸泡眼泪的窝头送给不赞成母亲上学的女姥太吃的。
生产队扒河改道,半劳力的母亲作为长女已能挣全劳力的公分了。健康结实、浑身是劲的母亲在哪都受欢迎,童年的劳累并没抑制她的身高,在女性中反被人称为了‘大个子’。
不偷奸耍滑的母亲会把最脏最累的活主动揽下,抬土兜时,她还要让同性搭档一个杠头,把轻的留给前面的姐妹,自己在后面还尽量的把挑绳往身边拉,拉到土兜不碰腿为止。
同志们呐
加油干呀
千年铁树开了花
农民土地回了老家,
种地的人有了地
男女老少笑哈哈了
……
失去上学机会的母亲遗传了外老爷的聪明才智,看什么会什么,张口即来的现编号子是社员们乏力时的加油器,沮丧时的强心针,在异常艰苦的状态下——人人却保持高昂向上的乐观的精神,劳动的乐趣与集体的团结力量是他(她)们活下来、走下去的强大支柱。
“啃树皮,喝菜汤,没吃没穿的还那么大的劲、那么足的精神,现在的人呐……”
回想以往,对比现在,母亲总是不解。
“喝个号子吧!”快收工了。力疲的社员们有些焉,队长这时会看看同样疲力的母亲。
墙头跑马不能算路
阴沟里使船不能算河呀
快板一打向前游
一对青丝挂门头
里边挂个荡刀布
必定是个剃头铺呀
前边扭后边扭
看看哪边好下手
剃了一个东洋头
再剃两个西洋头
不高不矮是平头
两面梳是分头
一根不留是光头
往上梳是飞机头
飞机头真好看
就是不能装炸弹呀
……
母亲对着挑担而过的剃头匠——那脱口而出的号子引来了一片起哄的喝彩与附和声。
小贵姥真难找
到处把扒人死人袄
弄到家里来粘好
打个鞋靠卖两毛喽
……
母亲对一个开她玩笑的同伴用自己独特的编撰把艰辛的年代用号子徘谐的表达了出来,特殊年代下的特殊时期已使人忘却了号子中辛酸故事的酸辛,一代代不变不改的是坚韧的赤忱之心和顽强不屈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天的劳顿在诙谐激情的号子中得到缓释和未尽的欢乐中收场。
为了犒劳社员,那天破天荒的每人发了一个杂粮窝头。欣喜若狂的社员们在还没享受到沁人的面香时——窝头就已下了肚。
母亲却把窝头一分为二,分别用纸包好,一份藏在枕头下的稻草垫下,另一份装进口袋随身携带,准备下工时抽空溜回家。
“啊……”母亲傍晚下工回来,发现草垫下空空的,半个窝头不见了。
开朗、坚强的母亲毕竟是个刚成年的孩子,她放声大哭——越哭越伤心——愈哭声越大。
“别哭了,俊兰。”
“再哭窝头也回不来了,快别哭了。”
“哪个吃屎狗,缺德鬼干的事?”
“不地道,太不地道了。”
“以后生孩子没屁眼。”
“……”
母亲怎么也止不住哭声。
“俊兰,累一天了,都想早点休息呀!”
什么都没吃的母亲跑到离她们听不见的空地继续大哭。一想到草垫下不见得半个窝头和破灭的心愿,渐停的哭泣又开始泛滥、爆发,越想越难受的母亲在外面哭了近一夜,大大的眼睛只剩一条缝了。
新一天的劳作还在等着她。
第二天下午眼睛消肿了,母亲才把仅剩的半个窝头送回家的,心里是硬逼着自己不去想那份丢失的给外姥姥的半个窝头。
“对不起大爷呀!对不起他。”每想到此,母亲的心还是会滴溜溜的疼。
分产到户后,家里半屋子的红薯是全家的生活保障。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不足也不够维持家用,干完农活的母亲会烀上一大锅红薯,放入铁皮桶内,上面再用棉纱被盖住——保温又防尘。
“热红白芋,才出锅的热红白芋。”
“又香又甜的热红白芋,快来买啦!”
“……”
我们这边把红薯称为白芋,母亲响亮清脆的叫卖声响遍大街小巷,清晰的留在我懵懂的记忆中。桶中最后剩下的一两个香甜稀软的白芋总是留给我的,桶底上粘稠的糖液,戳着戳着就想把头伸入桶底——觉得这样才能让我彻底的解馋。
白芋淌着红褐色的糖水顺着指缝流下来,吮着,吸着,舔着,我是绝不会浪费每一滴渗出来的糖水。
时至今日它那独特的香甜美味——没有一种美食能超过我对它的期盼和它在我心中的地位。
“该回来了。”外姥姥总站在路口,望着姐姐回家的必经之路。
“孩儿,是孩吗?前面可是孩儿?”
一次,天已经黑的只能看见人影了,一大早就出去、还没带干粮的姐姐还没回来,让外姥姥耽心极了,她替母亲站在路口,看见对面来个人影,她就要问几声。
‘孩’是她对孙辈的统称。
为了多拾些麦穗,瘦弱的姐姐跟比她大的成年人会跑到很远的地头。回来时背上的一大捆凌乱的麦穗遮住了她纤细、单薄的身体,斜挎的军用水壶里还装着给我带来的甘甜的泉水。
记得为了我和哥哥早上上学不迟到,早起的姐姐总是嫌炉火不旺,手中拿着母亲用布条沿上的蒲扇——对着炉口起劲的扇,累了就换手,两手都累了,就双手抱着扇柄不停地对着炉口扇。
憨淳的哥哥放学后就背起他专用的小粪箕,拿上木柄小撅头,四处转悠着寻找所有动物的粪便。我会在晚上拿起手电筒,在前面蹦蹦跳跳地帮助搜寻。
“一分钱尽喝,又甜又凉。”
“一分钱管够啊!”
……
家乡的集会上我和哥哥吆喝着新打上来的冰凉的井水,它是那时时兴的用糖精和食用色素勾兑的解暑水。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要穷。”母亲看着现在年轻人自如随性的生活,“挣一个花两个还行吗?有撒网时就有晒网时。”
母亲偶然上夜校的那段经历成了母亲自豪又骄傲的历程和美好的回忆。
多造林
多栽树
造林栽树有好处
绿树成林多好看
树大成材做木料
工业建设都需要
防风防水又防旱
“说错了,顺序又说错了,最后一句是在第二句后面的。”母亲对孙辈们纠正说,“脑子不好使了。”
棉花在工业上用处很大
政府提倡种棉花
一亩棉
三亩田
我们爱国家
好好种棉花
……
母亲像孩子一样字正腔圆,朗朗的背诵夜校所学的知识,神态是异常的认真,唯恐出错。
“毛主席号召提倡的。”母亲激动神圣的说。
她有时还能认得些我们不常用的陌生的繁体字,并说出字体结构。
“什么叫一亩田,三亩棉呢?”我忍不住问。
“是一亩棉,三亩田。”母亲更正。“棉花在那时很重要,种一亩棉花像种三亩粮食一样,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说的。”
母亲像外姥爷一样无师自通的会做些手底下经常使用的简易的木柜、桌子、凳子等。虽不精湛,却件件光滑、结实且耐用。
闲暇时她会找出孙辈们用过的小笔头——画小狗、小猫或茶壶等消遣作乐,尽管不形态逼真,然也像模像样的是那么回事。
“左眼闭,右眼睁,缺口对准星,准星对目标,目标正前方,三点线一条”。
民兵连时母亲打了五百多发子弹,次次优秀,无一良好。电影跟电视里激烈的战争场面与斗志昂扬的部队训练——会触及母亲尘封心底的另一种自豪与难忘的追忆。
母亲干农活的同时又包了两个打扫单位厕所的活。还好农具厂和塑料厂相隔不远,母亲的鼻子失去嗅觉是与这份工作有很大关系的,应该说是完全因为它才造成的嗅觉失灵。
好多年以后,她的嗅觉才稍稍恢复。
庄稼要变成花
全靠人当家呀
母亲有时兴起——会不由得再次喝起往年的号子,她佝偻的身体迸出依旧洪亮、有劲又激昂的声音。
干劲十足的社员们在激奋、流畅的号子中如火如荼的于田间奋力的劳作,他(她)们充沛的精力、高涨的热情、质朴的精神同敦厚的面容——随着号子在脑中栩栩浮现。
“吃不饱,穿不暖,却有使不完的劲。不知愁,不知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现在的人什么都不缺,还……”
母亲经常感慨的想不通。
马铃薯产量高
五亩地收一蒲包
大的像铜钱
小的像胡椒
……
母亲的号子在诉说三年自然灾害失收的情景。
“孩子,行行好吧!给你大爷一口吃的吧!”快到家门口的母亲被自己的大爷我外姥爷的堂兄拦住,他枯竭的眼睛放出亮光,紧盯着母亲紧捂着的口袋。
“我的好孩子,揪一口也行,就一口。”看着躲闪的母亲,大外姥爷颤颤的上前一步。
“俊兰,好孩子,揪一口吧?就一口。”
母亲最终还是跑掉了,身后传来大外姥爷的声音,“孩子啊!俊兰,就给你大爷一口吧!”
大外姥爷微弱的声音和只剩一双眼睛的脸是母亲心中永远的伤痛。
“对不起他呀!有愧呀!怎么弄,没办法。”
口袋里半个杂粮窝头是母亲用血泪换来的,自己没舍得用牙硌一下。那天她从队里抽个空子偷跑了出来,是把这半个浸泡眼泪的窝头送给不赞成母亲上学的女姥太吃的。
生产队扒河改道,半劳力的母亲作为长女已能挣全劳力的公分了。健康结实、浑身是劲的母亲在哪都受欢迎,童年的劳累并没抑制她的身高,在女性中反被人称为了‘大个子’。
不偷奸耍滑的母亲会把最脏最累的活主动揽下,抬土兜时,她还要让同性搭档一个杠头,把轻的留给前面的姐妹,自己在后面还尽量的把挑绳往身边拉,拉到土兜不碰腿为止。
同志们呐
加油干呀
千年铁树开了花
农民土地回了老家,
种地的人有了地
男女老少笑哈哈了
……
失去上学机会的母亲遗传了外老爷的聪明才智,看什么会什么,张口即来的现编号子是社员们乏力时的加油器,沮丧时的强心针,在异常艰苦的状态下——人人却保持高昂向上的乐观的精神,劳动的乐趣与集体的团结力量是他(她)们活下来、走下去的强大支柱。
“啃树皮,喝菜汤,没吃没穿的还那么大的劲、那么足的精神,现在的人呐……”
回想以往,对比现在,母亲总是不解。
“喝个号子吧!”快收工了。力疲的社员们有些焉,队长这时会看看同样疲力的母亲。
墙头跑马不能算路
阴沟里使船不能算河呀
快板一打向前游
一对青丝挂门头
里边挂个荡刀布
必定是个剃头铺呀
前边扭后边扭
看看哪边好下手
剃了一个东洋头
再剃两个西洋头
不高不矮是平头
两面梳是分头
一根不留是光头
往上梳是飞机头
飞机头真好看
就是不能装炸弹呀
……
母亲对着挑担而过的剃头匠——那脱口而出的号子引来了一片起哄的喝彩与附和声。
小贵姥真难找
到处把扒人死人袄
弄到家里来粘好
打个鞋靠卖两毛喽
……
母亲对一个开她玩笑的同伴用自己独特的编撰把艰辛的年代用号子徘谐的表达了出来,特殊年代下的特殊时期已使人忘却了号子中辛酸故事的酸辛,一代代不变不改的是坚韧的赤忱之心和顽强不屈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天的劳顿在诙谐激情的号子中得到缓释和未尽的欢乐中收场。
为了犒劳社员,那天破天荒的每人发了一个杂粮窝头。欣喜若狂的社员们在还没享受到沁人的面香时——窝头就已下了肚。
母亲却把窝头一分为二,分别用纸包好,一份藏在枕头下的稻草垫下,另一份装进口袋随身携带,准备下工时抽空溜回家。
“啊……”母亲傍晚下工回来,发现草垫下空空的,半个窝头不见了。
开朗、坚强的母亲毕竟是个刚成年的孩子,她放声大哭——越哭越伤心——愈哭声越大。
“别哭了,俊兰。”
“再哭窝头也回不来了,快别哭了。”
“哪个吃屎狗,缺德鬼干的事?”
“不地道,太不地道了。”
“以后生孩子没屁眼。”
“……”
母亲怎么也止不住哭声。
“俊兰,累一天了,都想早点休息呀!”
什么都没吃的母亲跑到离她们听不见的空地继续大哭。一想到草垫下不见得半个窝头和破灭的心愿,渐停的哭泣又开始泛滥、爆发,越想越难受的母亲在外面哭了近一夜,大大的眼睛只剩一条缝了。
新一天的劳作还在等着她。
第二天下午眼睛消肿了,母亲才把仅剩的半个窝头送回家的,心里是硬逼着自己不去想那份丢失的给外姥姥的半个窝头。
“对不起大爷呀!对不起他。”每想到此,母亲的心还是会滴溜溜的疼。
分产到户后,家里半屋子的红薯是全家的生活保障。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不足也不够维持家用,干完农活的母亲会烀上一大锅红薯,放入铁皮桶内,上面再用棉纱被盖住——保温又防尘。
“热红白芋,才出锅的热红白芋。”
“又香又甜的热红白芋,快来买啦!”
“……”
我们这边把红薯称为白芋,母亲响亮清脆的叫卖声响遍大街小巷,清晰的留在我懵懂的记忆中。桶中最后剩下的一两个香甜稀软的白芋总是留给我的,桶底上粘稠的糖液,戳着戳着就想把头伸入桶底——觉得这样才能让我彻底的解馋。
白芋淌着红褐色的糖水顺着指缝流下来,吮着,吸着,舔着,我是绝不会浪费每一滴渗出来的糖水。
时至今日它那独特的香甜美味——没有一种美食能超过我对它的期盼和它在我心中的地位。
“该回来了。”外姥姥总站在路口,望着姐姐回家的必经之路。
“孩儿,是孩吗?前面可是孩儿?”
一次,天已经黑的只能看见人影了,一大早就出去、还没带干粮的姐姐还没回来,让外姥姥耽心极了,她替母亲站在路口,看见对面来个人影,她就要问几声。
‘孩’是她对孙辈的统称。
为了多拾些麦穗,瘦弱的姐姐跟比她大的成年人会跑到很远的地头。回来时背上的一大捆凌乱的麦穗遮住了她纤细、单薄的身体,斜挎的军用水壶里还装着给我带来的甘甜的泉水。
记得为了我和哥哥早上上学不迟到,早起的姐姐总是嫌炉火不旺,手中拿着母亲用布条沿上的蒲扇——对着炉口起劲的扇,累了就换手,两手都累了,就双手抱着扇柄不停地对着炉口扇。
憨淳的哥哥放学后就背起他专用的小粪箕,拿上木柄小撅头,四处转悠着寻找所有动物的粪便。我会在晚上拿起手电筒,在前面蹦蹦跳跳地帮助搜寻。
“一分钱尽喝,又甜又凉。”
“一分钱管够啊!”
……
家乡的集会上我和哥哥吆喝着新打上来的冰凉的井水,它是那时时兴的用糖精和食用色素勾兑的解暑水。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要穷。”母亲看着现在年轻人自如随性的生活,“挣一个花两个还行吗?有撒网时就有晒网时。”
母亲偶然上夜校的那段经历成了母亲自豪又骄傲的历程和美好的回忆。
多造林
多栽树
造林栽树有好处
绿树成林多好看
树大成材做木料
工业建设都需要
防风防水又防旱
“说错了,顺序又说错了,最后一句是在第二句后面的。”母亲对孙辈们纠正说,“脑子不好使了。”
棉花在工业上用处很大
政府提倡种棉花
一亩棉
三亩田
我们爱国家
好好种棉花
……
母亲像孩子一样字正腔圆,朗朗的背诵夜校所学的知识,神态是异常的认真,唯恐出错。
“毛主席号召提倡的。”母亲激动神圣的说。
她有时还能认得些我们不常用的陌生的繁体字,并说出字体结构。
“什么叫一亩田,三亩棉呢?”我忍不住问。
“是一亩棉,三亩田。”母亲更正。“棉花在那时很重要,种一亩棉花像种三亩粮食一样,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说的。”
母亲像外姥爷一样无师自通的会做些手底下经常使用的简易的木柜、桌子、凳子等。虽不精湛,却件件光滑、结实且耐用。
闲暇时她会找出孙辈们用过的小笔头——画小狗、小猫或茶壶等消遣作乐,尽管不形态逼真,然也像模像样的是那么回事。
“左眼闭,右眼睁,缺口对准星,准星对目标,目标正前方,三点线一条”。
民兵连时母亲打了五百多发子弹,次次优秀,无一良好。电影跟电视里激烈的战争场面与斗志昂扬的部队训练——会触及母亲尘封心底的另一种自豪与难忘的追忆。
母亲干农活的同时又包了两个打扫单位厕所的活。还好农具厂和塑料厂相隔不远,母亲的鼻子失去嗅觉是与这份工作有很大关系的,应该说是完全因为它才造成的嗅觉失灵。
好多年以后,她的嗅觉才稍稍恢复。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