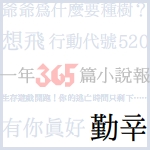■第七天.善良的
“咸柠檬红茶……味道有点奇怪。”
“跟梅子绿茶一样奇怪?”
“要这么说,也奇怪。为什么不是柠檬绿茶、梅子红茶?第一次喝梅子绿茶也怪怪的,不是梅子汤也不是绿茶。”
“不过,喝惯了也就惯了吧?”
“可是,咸柠檬红茶还是奇怪。”
“黄金比例到底在哪?明明是照黄金比调的……”
探视的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大概都在谈这个吧,咸柠檬红茶的黄金比例。一个话题能谈上三天,简博约果然不是不会说话的人,听说小学时还喜欢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是个像小老头的小孩,直到父母车祸后才开始有点沉默。
第七天,要有点不同了,虽然依旧带了一束满天星,还有咸柠檬红茶,但多了一点二分之一小馆的氛围──二分之一小馆的杯子,二分之一小馆的桌布。此外,还有一点不同。
“又送花了,还是满天星。想要她送别的吗?有喜欢什么样的花?……豆──花!呵呵。偶尔老套、俗套的答案也不错吧?反正生命没有标准答案。还是你比较喜欢这样的回答──什么花都好,因为花是奇迹,生命的奇迹,鼓舞自己的生命也努力开出花来?”
简博约这天似乎沉默了些。察觉到她的“有一点不同”?努力吧,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没什么不同,张舒怀。她勉励自己。
“冬天开出春天的花,是奇迹,还是有违天理?该说这样的花很努力,还是太犯规?”
简博约开口了,问的却也有一点不同。该怎么回应?她想起有一个家伙曾说:“依照现行的潮流说法,说要顺从自然、顺从自然,说要吃当时的、当地的食物。那么冬天不吃春菜,该吃什么?泡菜?酸菜?咸菜?腌菜?榨菜?酱菜?那些泡的、腌的、酱的菜又是从什么时候泡的、腌的、酱的?自然吗?孩子肚子饿了,要吃什么?吃潮流?呵呵,有没有想过,人站着,基本上就是不顺从自然的开始?”所以,即使有违一点天理,基本上还是可以认同?
“难说。”她只能这么说了。
“法律呢?法律会怎么说?认同?还是不认同?”
法律呀。“我们现行的法律在确保自然人社会化,也想确保大自然不被社会化。矛盾?是矛盾。只能说法律跟生命一样,都在寻找更好的答案。”她又想起那个家伙曾如此高谈阔论。
“对法律有兴趣?”
“应该是法律对我有兴趣。如果我想做有关法律的工作,有可能?”
“想从事法律工作,有什么问题?”
“没有法律问题?”
难说。“会有什么法律问题?”
“虽然说各种经验都很重要,但也都不见得必要。生过病的医师大概更能体会病人的苦吧?不是有些问题学生会反问老师说:你们,从小乖乖牌,从来就是资优生,哪里能了解我们的问题?如果这个老师也曾是问题学生,大概就没问题了吧?”
──所以,你为当法律人,累积犯案经验?
“满口烂牙的牙医,躁郁症缠身的心理医师,或许还没问题,可是杀人嫌犯,当法官?”
杀人嫌犯?他还知道警方当他是杀人嫌犯?“洗清嫌疑,不就好了?”
“洗得清吗?”
难说。想洗清吗?
“那些只想相信我有罪的人,会相信我真的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得能读法律、当法官?干干净净得能判人有罪、判人无罪?能肯相信,我也是被害人?──真是倒楣,竟然遇上这种事。”
倒楣?那个死了的不更倒楣?“不过,幸运的是,你不还有满天星?还有人相信你。”
不知真假,只见简博约微微苦笑:“她是相信我无罪,还是相信我有罪?”
“所以,你那时候都不肯开口,是因为委屈?没人相信你?”
“说话费力气了。希望别人相信,然后换来一个个的失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信也好,不信也好,怎样都好。”简博约认真看了看她:“舒怀姊呢?相信我吗?”
简博约开始怀疑她不相信他了吧?相信?不相信?到底怎样不知道。
她微微笑了笑:“我学天空。”像打禅谜。
简博约略带点警戒的眼神看着她。
“要是我说相信,你就相信了?要是我说不相信,你不就更不相信了?所以我只能说相信了?不,我只能学天空,不说话。‘天空不说话。四季变化,万物生化,天空不说话。’还记得吗,这一首最美丽的诗?”
简博约眨了一下眼睛:“有点印象。”
那是简博约的父亲在编辑教科书时写的,翻自孔夫子的一句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并注记说:这是世上最美丽的诗。简博约家里的书,从书架上的到流在地上的都翻出了毛边,他对这首诗能“有点印象”也算不错了。“请注意,‘都翻出了毛边’。妳看看这本,都写了什么?”那个爱高谈阔论的家伙曾说着说着,将一本书翻到她眼前。──她摇了摇头。
“拿来当满天星的花语如何,‘天空不说话’?”
直截了当:“不好。”
“为什么?最美丽的诗当最特别、最唯一的花语,不好?”
一脸严肃:“是最美丽的诗,也是最无情的。”
“怎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怎么,是感觉被父母、被代理监护人遗弃了?被命运遗弃了,被天地遗弃了?还有,同学?她问过那些同学,就是蔚沛然他们。他们似乎有意疏远了简博约,在三个月前?四个月前?总之,直到去年暑假前,简博约加蔚沛然加王仁哲加林守震加周思维这几人还是无敌好朋友。因为被无敌好朋友遗弃了,所以行为偏差,所以杀人?……果然,只要一心把简博约推当主谋,许多问题可以很简单就想通了。也难怪警方……不,是那家伙强力推荐简博约就是主谋。
她吁了口气,告诉自己:这次没要那么相信简博约没错,但也没要那么不相信。
“所以,你最推荐的花语会是……”
“‘这世界,即使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反对,我也要勇敢活下去!’这才是最……最……最‘最’的。”
简博约似乎有点激动了,连一句话都说不清。就像嵌在大北河畔堤防上的那块红砖,砖面上的两行文字同样模糊不清。
“还有人知道那是巴纳巴岛纪念碑吗?‘谨以一砖之地献给巴纳巴岛上容身不得的巴纳巴人。’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又最大的纪念碑了。最小,是因为只有一块砖;最大,是因为这样的砖遍布全世界。”这是那个家伙以前说的,接着还说:“听过巴纳巴岛吗?在太平洋上,二战时被轴心国军队强行占领……”这是那家伙极少数让她还听得下去的高谈阔论。
“所以,你还是会读法律吧,即使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反对;即使是冬天,你也要开出春天的花;即使有人不相信你,你也只管做自己的?”因为你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是吧,即使杀人的就是你?
“不行吗?”
简博约的眼神突然锐利无比,像只饿虎扑了过来,狠狠地吓得她忘了心跳,呆了。
***
时间同空间安静无声,简博约同她喝了一口咸柠檬红茶,冰的。冰的才更好麻痹那不适快的滋味。
“你想成为怎样的法官?律师?”玩法弄法的?儿戏人命官司的?高兴判生、不高兴判死的?可以把人玩得死死的、可以合法玩死人命的?
“跟舒怀姊一样,相信法律保护人。”
乒乒乓乓地,猛然一阵心跳,乱如骤雨。不,他根本不相信法律能保护人。
“还是,妳根本不相信法律能保护人?”
她只能略略稳住心跳,控制呼吸,无法回答什么。
“法律与人命,妳会选择哪个?如果必须违法、犯法才能保住人命,妳会宁可牺牲法律也要保护人吗?”
简博约的眼神极度热切,她只能再喝一口咸柠檬红茶。
这问题乍听下像是废死、反废死,也像是高墙与鸡蛋的选择,但坦白说,不同的状况会有不同的答案。简单一点,是法律对,还是人对?法律的本意在保护人,这一点绝对没错。至少保护多数人。她把问题在心底回答了一遍,突然──“真的?妳要保护法律?”那家伙闯进她脑里:“妳真的相信法律至少在保护多数人?〈逃亡奴隶法〉规定某些人种是长了两只脚、会走、会跑、会逃亡的私人财产,妳要保护这样的法律,好保护某些人的‘私人财产’不会出逃?张舒怀呀,没想到妳要当这种法律人呀!妳要反驳吗?那就是要保护人了?电车难题来了。失控的电车就要辗压绑在铁轨上的人,一条铁轨绑了五个人,另一条绑了一个人,妳要怎么选择?很简单的算术问题,小学一年级扳手指都扳得出来,就牺牲那一个……不,是救那五个人。那么,如果问题是:如果救一个人的结果是得死一千个人呢?反过来,如果杀一个人能救这一千个人呢?好了,小学一年级算不出来的,妳算了出来,要杀了那一个人吗?真的?那么,妳就杀了巴纳巴岛上最后一个巴纳巴人了。只要那个巴纳巴人活着,那一千个二战轴心国士兵就一千个该死了。所以妳说,妳的法律要保护那一千个该死的‘多数人’?张舒怀呀,真没想到妳是这种人耶!”她在心底大声呐喊:“所以我说要看状况!”
“看状况。看真相。法律跟生命一样,都没有标准答案,都在寻找更好的答案。”啧!竟用了那家伙的答案。“所以,问题是,你问题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你会问这问题,难道,法律要你死?真相反对你活下去?
简博约老僧入定:“真相那么重要?那么会有一千个真相跑出来要妳相信。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法律。”
“那你想要怎样的法律?”
“先矫正一点。法律老在考虑加害人是否有教化之可能,而没去想被害人是否有救治之可能。我们的法律还真是善良,还是天真?想矫正魔鬼?神了!”
说的真的假的?真想问他:那你如何看待犯法的未满十四岁免费优待?“你主张严惩不贷?”
“不行吗?”
故作姿态?对加害人深恶痛绝?所以绝对不是加害人?不论真假,都在吃法律豆腐。法律又不会因为一个人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就改变什么。他只是在表态自己和加害人什么的了无一点、半点关系吧?“有人说:‘我们现行的法律是性善说的信徒,相信人会犯错是社会出了错,之所以要罚加害人,是为了矫正那个错误的影响。判死刑是因为已无法矫正,判重刑是因为得很努力矫正,未成年减刑是因为有努力就能矫正,未满十四岁完全免受刑是因为不必努力也能完全矫正。’你怎么看?”
“即使是希特勒?”
“希特勒?怎么了?”
“即使希特勒犯了大屠杀的重罪,只要未满十四岁,就是免罪?”
“你这个充满假设性的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未满十四岁的人不会希特勒。”
“那么我们该在什么时候杀死希特勒?在他未杀人之前?还是杀人之后?不可能在杀人之前吧?因为他还没杀人。杀人之后呢?他已经改过了,努力或者不努力,反正已经矫正了,不会再杀人了,是不是也是免罪?”
──所以你即使是希特勒,也得等你犯下罪,才能惩治你?而等你犯下了罪,你又“不会再杀人了”,也不能惩治你?
“法效天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法律也待人如狗。一只狗咬死了另一只狗没关系,只要别再咬死别的狗就好了,停损才是最重要的。被咬死的狗不值钱,值钱的只有活着的狗,所有的狗都是彼此的替代品。这是我对法律的粗浅认识。”
才怪。那些“粗浅认识”来自他父亲编辑时写的笔记。这是她对他父亲写的笔记的粗浅认识。“所以你主张严刑峻法?”
“严刑峻法……也没错,更容易使人不犯法。不犯法的人才享有法律保护。”
当一个人剥夺了别人的生存权,他的生存权也就消灭了,因为不犯法的人才享有法律保护。──这是他父亲的笔记没错。“法律保护人,不是保护人不犯错,也不是保护人可以犯错,而是保护人有机会改过。因为法律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好人’或者‘坏人’。只要是人都可能犯错。”
“不需要。”
“不需要?”
“我不需要这样的法律。”
──你可是受保护的耶!如果你是主谋的话。所以“不需要”是因为你没犯法?还是因为有法律保护才害你犯法?
“给人改过的机会,给一、两次,他不改过;给三次、五次,他不改过;给九、十次,他还是不改过。那么就不给第十一次了?能说他第十一次肯定不会改过?那么他执迷不悟一百次,依然要给他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机会?那到底是谁执迷了?执迷的人执迷得想当神了!却拿被害人当牺牲品?还是,一开始就不许他犯错,一犯错就没机会了?这样至少没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被害人,而第一个被害人……第一个被害人……”
简博约说得激动了,俨然法官?不,是被害人。但他说的东西多少来自他父亲的笔记,背这些有用的、没用的正好用来暗示自己纯是事件被害人?“法律还是希望能给人改错的机会,机会当然不会太多,但肯定有。因为人会犯错,尤其是孩子,孩子不懂,所以会犯下自己也不知道的错,法律想做的不是别的,就是希望能平复那个错。”──这就是你说东说西,说到最后想要我亲口说的吧?
简博约微微点头:“嗯,没错,妳说的没错,孩子不懂,所以犯错。”头一抬,“但大人往往犯下比孩子更离谱的错,不是吗?”
简博约那险如深渊的黑眼圈直逼而来,像在逼问:是妳犯了错,还以为我犯了错?
她心跳不已。──真的?他没犯了错?我犯了错?……谁犯了错?
■第十三天.说故事吧
不,他犯了错。那一天是她第一次没那么相信他的黑眼睛,结果,果然,他值得她的“没那么相信”。接着几天,一天用无罪的眼睛看他,一天用有罪的眼睛看他,他就一天看起来无辜,一天看起来死有余辜。真像装进了薛丁格盒子里的猫。猫肯定是无辜的,但是他呢?肯定的是,管他二分之一不二分之一,他会百分之百拚尽全力活下去。
来了。那少年带着两眼黑洞进来了。
例行一阵寒暄后:“我们来说故事吧。你一定记得‘物理学家’教过的,英文的过去式就是说故事,故事说的是过去的事、虚构的事、譬喻的事。我们就来虚构、假设,假设你就是‘物理学家’,我们试着扮演这样的故事,如何?……好,那么当你再一次走进来、坐下去,我们就开始吧。”
喀地一声,门开了;碰地一声,门关了。
开始了。
“你就是凶手。”
***
“妳的那个,就是凶手喔。”
在结束第六天的探视后,她又踏进了二分之一小馆,还没走到柜枱,身后就传来了莫名其妙的这么一句。一股足以令她全身起粟的不好预感爬上了脊背。声音很熟,记忆中和大学课堂、食堂的气味纠缠成一团,是一个老爱高谈阔论的家伙。
“而妳就是凶手的法律保护人?”
那声音依旧不肯饶她。她慌里慌张地收拾情绪,喔,还有表情,告诉自己:张舒怀呀,千万别惊讶、惊慌、惊恐,要是看似教他看穿了,就真要教他看穿了。然后缓缓地、缓缓地回头,看见那个家伙,像个戴了眼镜、梳了油头、穿了西装的格斗家,脸上一抹胜利者的微笑,一如大学初见那天。
“妳是猫派还是狗派?”
一如大学初见那天,那家伙又用这一句打招呼。初入大学时她和几个初初认识的同学聊聊谈谈,聊养猫好还是养狗好,一句“妳是猫派还是狗派?”就从耳后突然窜出,是个初次见面的家伙。“有人说:‘猫派的偏向现代自由,狗派的偏向传统伦理。’妳怎么说?”她忘了当时怎么说的,只记得──
“保护人该当人派唷!”
没错,就是这句。当时那家伙说:“法律人该当人派唷!”然后脸上一抹胜利者的微笑。
那家伙才不是什么人派的法律人!
她最记得后来在大学课堂和同学讨论婚姻法时,那家伙又突然冒出,说:“为维护孩子的权利,我们应该支持传统伦理派的婚姻关系。婚姻法就是生育孩子法,我要和你结婚,就是我要和你建立生育孩子的关系。在这种定义下,为保障孩子的权利,我们现行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才会排除血缘关系、复数关系。”到了下一节,他又冒出来,握着拳头说:“为维护人的权利,我们应该现代自由派,解放传统婚姻关系!”
“耶,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那孩子的权利呢?”
“哦,有人的权利受损了?要打官司吗?那么,”大手一伸:“请先准备好律师费。──看看,我替你们制造了多少就业机会,感谢我吧!”说完脸上一抹胜利者的微笑。
这就是那家伙!
还有一次,她和同学在大学食堂吃饭,兼讨论昨晚〈脑人神探〉播的毒咖哩杀人事件──
“无罪唷,如果找我辩护的话。”
又是那家伙!
“真的?好,让我们先整理一下案情──社区运动会上有人中毒了。中毒的都吃了会上凶嫌煮的咖哩。凶嫌煮的咖哩里验出了砒霜。凶嫌住的房间里也找出了砒霜,同一成分的砒霜。虽然被害人和凶嫌素无往来,了无关系,但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些中毒死的、没中毒死的,有不少人身上都投保了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巨额意外险。当然,受益人毫不意外的就是凶嫌,而且保费也毫不意外的就是凶嫌缴的。试问,有谁会没头没脑替无缘无故的人缴保费?所以,凶嫌有唯一的杀人凶器,有绝对的杀人动机。而你,还能辩护什么?还能辩护到无罪?”
那家伙依然一派胜利者的微笑:“如果找我辩护的话。”
真的?“那你怎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