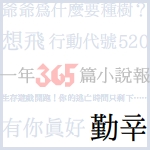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授权发表
字数:44446
阅读:6862
发表:2020/3/20
悬疑推理,犯罪
小说
恶魔游戏──十三岁少年杀人事件(下)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本作品已在华语剧本网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版权登记,登记2020-B-01368】
总是在记得自己的名字后才安心下来。随即却又紧张不安──是不是忘了什么才会那么不安?
咬咬唇。不想醒来,不想下床,是为什么?
“如如,舒怀姊来了。”
门外传来爸爸的声音。蒙上棉被,装睡。
***
舒怀姊进来了,就站在眼前。怎么进来了?没印象。
“早啊!今天觉得怎样?”张舒怀问。
她嘴巴绷着,像缝了一百零八条线。还不能说、还不能说。还是可以说?可以说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好像忘了不少东西。舒怀姊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关系那么亲密,叫舒怀姊?还有,今天早上真的有下雨?对了,有日记。幸好有日记。她警戒着跳下了床,偷偷翻了翻书桌上的日记。日记却整整齐齐的满篇课业笔记。她忘了,她很久不写日记了。日记会泄露秘密。
仿佛未曾察觉她的紧张,张舒怀眼睛看向摆放在书柜里的熊猫娃娃。一只只彩色的、斑点的、花布的熊猫娃娃就三三两两藏在书间,像玩躲猫猫,也像在说悄悄话──读书之余,也别忘了熊猫呀!
“妳喜欢哪一只?浅粉红的?彩叶纹的?青花布的?还是……呀,这只受伤了?”
张舒怀说的是一只最单纯的、纯然黑色白色的熊猫娃娃。牠右手打石膏般地绑了绷带,绷带上写了方方圆圆的蓝字。
“‘心……唯……庆……仍然守约’?这什么?”
这能不能不说?能不说就不说。但能不说?活下去。要活下去。这是约定。这不能说。“好好地。跟自己约定,好好地。”
“好好地?”
“就是好好地。”
话说出口了,她后悔了。应该说是给未来的自己十个约定。约定好十八岁的约会,要回校开同学会,约定好十八岁的微笑,要像十岁、八岁一样,约定好十八岁……忘了,忘了有什么样的约定。没错,应该说“忘了”。竟然忘了可以说忘了。现在再说就晚了。可是,舒怀姊会再问一遍吧?到时候还能说出一样的答案?她忘了她刚刚回答了什么。对,忘了,就说忘了……
“要不要见队长?”张舒怀突然发问。
队长?蔚沛然?对,她都叫蔚沛然队长。因为蔚沛然家里开健身房,还组了一支棒球队,店外就贴了一张蔚沛然拍的宣传照──手执球棒,头戴头盔,头盔下两眼凝视看不见的对手;雄姿英发,蔚然如棒球队队长。但是……舒怀姊怎么知道?
她呆呆地看着张舒怀,突然忘了张舒怀问了什么。──对,“要不要见队长?”好奇怪的问题,难怪会忘了。
队长曾要找她,被她爸爸轰出去:“你是打死人的,还是搬尸体的?”爸爸急要保护她,就要和那些沾上案子的划个一清二白,当下一棒子啵地一声打破了队长的头。横飞的血花溅满地面,那鲜红色的……不对,爸爸没打死人,她得瞒着……不对,爸爸真没打死人。她眨着眼睛看着张舒怀。
──爸爸没打死人,那是梦……爸爸没打死人,那是梦……那是爸爸在梦里没打死人?那在现实里呢?伪装成梦?
“爸爸没……”
“妳爸爸同意了。但还需要妳同意。”
她胸口怦怦怦地仿佛定时炸弹要炸了。那么爸爸是瞒过了张舒怀?张舒怀还不知道爸爸打死了人?不对,张舒怀是要她去见队长的……尸体?爸爸怎会同意?
“不,不可能。”糟了,这么说不可能,会不会反证了爸爸打死了人?
张舒怀缓缓地说:“妳回答问题似乎都想了一段时间?不觉得奇怪?”
她张着口,呐呐地发不出声。──为什么?我不是做得很好?我不是一直很听话?不是都教我要小心说话?为什么还要责备我?
“不觉得自己没必要受这种罪?我也是这么对妳爸爸说的。你们隔离得再远、再澈底,检方依然会怀疑你们早串通好了,所以刻意断绝往来也就没有意义了,只会让你们活得更神经紧张。或者,你们要一辈子不见面?不奇怪?为什么要变成这样?”
她还是张着口。队长没死?那爸爸是打死了谁?无论是谁,她都要保守这个秘密。不对,爸爸真有打死人?她摸摸脸,烫得。
“见吧,那就见吧。”
没错。说不见队长,反而奇怪吧?“请不要做奇怪的事,这就是妳的任务。”这是“物理学家”说的。
■中.好久不见半半
好久不见半半。半半似乎又可爱了点,坐在椅子上,等着她要半半握手、转圈、站起、坐下。手指挠挠半半的下巴,半半的喉咙就舒服地咕噜咕噜响。她想学半半咕噜咕噜,只是怕有人看见,队长,还有爸爸。
队长就同她坐在二分之一小馆的二楼窗前,爸爸则隔了一张桌子,像个业余侦探,藏在报纸后。是在跟踪女儿约会?如果是就好了。爸爸同意让队长见她,不表示同意让队长单独见她,直一路隔了两、三步的距离,直到现在。
窗外下着毛毛雨,堤防外几个小孩撑着伞、跺着小碎步,坚持要玩红绿灯。是该坚持呀!再坚持也坚持不了多久,不久后你们的世界会全面亮起红灯,禁玩这种游戏。
她想起他们好久没玩红绿灯了。
她的生日礼物每每都是他们抓娃娃抓来的、各色各别的熊猫娃娃。“送妳一只替身娃娃,祝妳生日很快乐!”“这不是一般的娃娃喔!妳要是被鬼抓了,只要用这只娃娃,我们就会替妳当鬼喔!”“哇!我也好想要呀!真羡慕死妳了!”“真的?下次我们也送你一只。”“耶?”“哈哈哈!”……
“没事吧?”队长开口问。
她回过了神,脱口一句:“没事。”这才惊觉仿佛这些天的纷纷扰扰都是梦境,和死党在一起都忘了什么叫提心吊胆。
“没事就好。事情要结束了。”队长喝一口刚来的热可可说:“没事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律师证明了我们没事,我们都是被人害的被害人,所以,没事的。如果妳可以的话,我想向舒怀姊说一件事。”
“什么事?”
“先约舒怀姊来吧,当面说比较好。没问题吧?”
她不知道,但不说不知道,只是拿一块饼干,点点头。队长就打了手机。舒怀姊好像有事,要晚一点来。
“最近如何?”
“最近如何?”她下意识撇头,看一眼那个藏在报纸后的“业余侦探”,“不好说。你呢?”
队长搔搔头:“都在家看电视,看棒球比赛。”
她喔地一声,没要接话。
“妳还是不看棒球?”
“看啊,只是看不懂。”
队长笑了。“看不懂还要看?还不要我教妳?还是,现在想学了?”
她嗯地一长声,摇头:“要是女孩子比你更懂棒球,很扫兴吧?所以……”撇头再看看“业余侦探”,不说了。怎能说“这种东西还是交给男朋友来教比较好”?
“还没学就会说大话?等妳懂棒球再说吧!”
“等我懂棒球,就不会觉得你有多厉害了。”说着装作手执球棒、两眼凝视,队长在宣传照上的模样。
队长只能苦笑。
“你没拿铁棒打人真是万幸……”
她话一溜出口,就后悔了。看得出来,队长脸色变了。勃喇勃喇地,隔桌再隔桌的翻报纸声适时响了一阵。真感谢爸爸跟来。她低头啜了一口热可可,再拿块饼干,递给队长,以示歉意。
队长接了饼干,正要往嘴巴送,停下了。“我先说律师说的事好了。”
队长说的律师就是到处走走串串的高强律师了。
高强律师说,现在一般的认知是王老师装在袋子里被人打死了,而打袋子的是三名学生。这样的认知对不对?很可能是错的。因为这很可能就是主谋想要人认知的。其实光想一想就会奇怪:为什么打死一个人得装上四只麻袋?是要让人忙得没空想东想西,譬如打开袋子看看?或是想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譬如吊上滑轮装置的那只麻袋其实装的只是等重的沾水绵花?这不无可能。那么王老师是谁打死的?算一算就知道,第一只麻袋吊给三名学生打,这期间推车从河滨公园推回学校后门口,运第二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再来到河滨公园,经历的时间就等同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一趟来回。接下来的三只麻袋只算比第一只麻袋多逗留在学校的时间。那么第二只麻袋就是多了从学校后门口运第一只麻袋到河滨公园,再从河滨公园推推车回学校后门口的时间,约等同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半趟来回。第三只麻袋则比第二只麻袋多了从学校后门口运第二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再回河滨公园运第一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最后回学校后门口要运第三只麻袋,就约等同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一趟半来回,比第一只麻袋多了两趟来回时间。第四只麻袋则比第三只麻袋多了从学校后门口运第三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再回学校后门口要运第四只麻袋,就是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一趟来回,比第一只麻袋多了三趟来回时间。如此,答案就显而易见了。王老师是有可能装在第一只麻袋,由三名学生打,打满一趟来回时间,但不也有可能装在第四只麻袋,由一名学生打,打满三趟来回时间?
“也就是三人连打十分钟造成的棍棒伤,只要努力点,一人连打三十分钟也做得到。”队长如此总结了高强律师的说法。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王老师装在袋子里被人打死了这一点肯定没错,而有三名学生吊打麻袋这一点也肯定没错,但要是以为打死王老师的就是这三名学生,那恐怕就有问题。是有人有意要我们产生这样的错误联想。”
她喃喃地又问了一句:“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有一个人躲在学校里、花了三倍时间打死了王老师。”
这什么意思?这“有一个人”是谁?将王老师装进麻袋的不就是简博约?难道是简博约?她不敢置信:“这……真的?真的?”
队长低下眼睛:“这样更好说明为什么要那么明目张胆地将麻袋吊上滑轮装置,众目睽睽下狠打、狠狠打。这也是律师说的。”
听起来像是这么回事。她叹了叹气。但还是不想相信。
队长说,律师还调查了麻袋的摆放位置,果然,没人记得是怎么摆放的。第一只麻袋和第三只、第四只麻袋调换了位置都有可能。
她挠挠半半的下巴,不知该说什么。王老师还是由王仁哲他们打死比较好,至少打死人的最后一下不知道是谁打的,对吧?半半只是眯着眼睛咕噜咕噜。
“舒怀姊来了。”
队长眼睛指向窗外,窗外可见张舒怀撑了伞,走着堤防来了。雨似乎大了。从天井望去,张舒怀进门的时候,门口已摆出了爱心伞,张舒怀差点把自己的伞收进爱心伞里。在想什么呢?她在二楼座上不觉紧张了一下,半半便翻了身,警戒地左右张望。
张舒怀上楼入座后,队长再将刚刚说的重说一遍。张舒怀看来并不意外,早猜到了这些事?她看看队长,不知队长意不意外。
“我相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否则无法说明为什么要用上四只麻袋。更何况──”队长两眼直视张舒怀:“简博约就是‘物理学家’。”
张舒怀眼睛睁了一下下。看来吓到了。
高强律师推论说,表面看来是三名学生打死了王老师,这太直接了,也显得另三只麻袋太多余了,所以恐怕是掩盖了一部分的真相。而这部分的真相有谁看得见?是谁将王老师装进袋子?是谁决定了王老师装进的袋子是第几只、决定了王老师是死是活、决定了这案子最终如何呈现、决定了这案子是成是败?能决定这一切的,会是简博约?还是“物理学家”?
因为律师的这番推论,也就让队长想起了一件事──
“简博约说过自己就是‘物理学家’。”
队长说着看了她一眼,再回看张舒怀,说那时候教室只有她,江心如,还有他在,而简博约走进教室突然说了自己就是“物理学家”,然后他们两人愣了一会,都没接话,简博约只能一脸尴尬离开了教室。事发突然,事后也没有后续,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现在回想,或许,简博约真的就是“物理学家”。
听错了吧?她愣了一会,没能接话。张舒怀眼睛看向她时,她只能一脸尴尬,摇摇头──别问我,我不记得这件事。
队长眉头皱了皱,又展平了,说:“妳可能忘了,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那是期中考后的体育课,妳身体不舒服,我当值日生。还不记得?……也好,至少证明了我们不是说好的。至少我们诚实面对了各自的记忆,也不必去猜有谁想骗谁说什么假话。”
她神经微微紧绷。队长……难道期待她配合说什么假话?
“假设真如简博约所说,他就是‘物理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张舒怀问。
队长想了一下:“我必须诚实地说,我确实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也以为听错了。”
“还记得叶沁吗?你们的伙伴,至少以前。”
这个……她还记得,微微点头。看向队长,队长却没什么反应。她也不敢微微点头了。
“叶沁,你们从小玩红绿灯的伙伴,她刚开学就没来上学了。你们却没有人去看她。不,是有一个人去看,就是简博约。”
“叶沁……她怎么了?”她现在问出口,反而作贼心虚,但又不敢像队长那样强作镇定。
“妳为什么不去她家探问?”张舒怀反问。
她低了低头。不,不能低头,低头就心虚了。抬头看了队长一眼,还是队长镇定。
队长微微皱眉:“我们是没去看她,但她也没来看我们,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沁,和简博约一样,学业成绩在你们当中数一数二。也就是,她和简博约一直分占你们当中的一、二名。叶沁拒学之后,简博约去看她了。然后,简博约肩膀严重磨伤,说是从堤防摔下来。再然后,就再也不见你们一起出现在这里,二分之一小馆。你要说说怎么了吗?”
“坦白说,不知道。忙吧。”
“是什么原因,叶沁拒学?是什么原因,简博约受伤?是什么原因,你们集体漠视了叶沁和简博约?”
“……课业繁重?大家都只顾得了自己,顾不了别人。”
“课业繁重?如果有人说是霸凌呢?”
“霸凌?谁说的?”队长一反方才漠然不惊的反应,声音急了起来:“简博约说的?简博约说的就是对的?不过成绩好了点,就什么都对?那我说的呢?就是妄想?哼!要我说,是简博约在妄想!被害妄想!”
妄想?是谁在妄想?是简博约妄想自己被霸凌,还是队长在妄想简博约妄想自己被霸凌?张舒怀眼睛看向了她,她赶紧摇摇头──别问我,我不知道这件事。
张舒怀转说刚才队长手机打来时,她就在叶沁家里。叶沁生病了,看来是压力过大,只想在家自学,也不请家教,甚至不太说话,学了手语,还有,理了光头,现在才慢慢长了些短短的头发。
“她的头发是之前遭人乱剪一通,东秃一块、西秃一块,才只好剪光了。将女孩子的头发剪得不得不剃光干净,这是逃避学业压力?还是霸凌?”
队长两眼凝视着张舒怀,仿佛面对那个看不见的投手。球来了吗?要挥棒了吗?
“她逃避上学,但不逃避学业,甚至花时间自学手语,怎么说都不像是课业压力造成的吧?”
“那么,像霸凌吗?”队长反问。
张舒怀点点头:“语言暴力会让人逃避暴力当下的语言。她恐怕在校的时候受了语言暴力,而且……”
“她也说是霸凌?”
直球对决?
“你觉得呢?”
曲球?
“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课业压力。所以忙着用功,可能疏忽了什么。”
“包括忽视叶沁为什么没来上学,还有简博约为什么受伤?”
“因为我们眼前有一件无法忽视的事:林守震的成绩掉下来了。”
“叶沁没来上学是在林守震考试之前吧?”
“那么就是:在林守震成绩掉下来之前,大家都不自觉地意识到课业压力。”
“真的?”
“当然……”
队长还是没挥棒。球来了,避开了。还是挥了棒?在挥棒?别问她,她对棒球一知半解,只是感觉队长的神情一如宣传照上的专注。大腿有东西碰了碰。低头看看,是半半用脚掌轻轻地抓了抓。半半也感到人类语言之间透出的压力了?看着半半无辜的大眼睛,她突然感到害怕。想起了一件事:半半抓伤过她。
***
“恐怖谷理论:越像人,越有亲近感,但太像人,却有恐怖感,像是看见了怪人,有怪病的人。人会远离有怪病的人,以防传染,这是天性。动物就是这样。有点像人有点不像人才会讨人喜欢。譬如猫,譬如狗。要是猫狗长得像脸上长了猫毛、狗毛的人那就恐怖了。但毕竟动物还是动物,有野性,人们接近牠们的时候都忘了牠们不懂人际关系、生活礼仪……”“呀呀呀!不过教半半不小心抓伤了一下,也值得你讲那么多?”是呀!很痛的,大概。几人七手八脚乱包乱扎,将教半半抓伤的手指绑得像打了石膏。“不过教半半不小心抓伤了一下,也值得包扎得那么夸张?”“哈哈哈!这是反恐怖谷理论。要是包扎得太认真,就把半半抓伤人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这样会产生心理障碍。所以,不妨转移注意力。再夸张点,我们都绑上绷带吧!”“对!再签名、签字!”“当然!有饭分着吃,有苦也分着吃!”“感情好得像手上的手指,脚上的脚趾!”“脸上的眼屎、耳屎、鼻屎!”“你少恶心了!”“再恶心,我也是沾在你脸上的!哈哈哈!”……
哈哈哈!当时好得真像手上的手指,脚上的脚趾,就是分开了也分不开。几个人说说笑笑,就把半半抓伤手指这件事玩笑了过去。那时候简博约、叶沁都在。都忘了是什么时候把这样的感情分得一干二净。好像有一场暴雨……
咬咬唇。不想醒来,不想下床,是为什么?
“如如,舒怀姊来了。”
门外传来爸爸的声音。蒙上棉被,装睡。
***
舒怀姊进来了,就站在眼前。怎么进来了?没印象。
“早啊!今天觉得怎样?”张舒怀问。
她嘴巴绷着,像缝了一百零八条线。还不能说、还不能说。还是可以说?可以说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好像忘了不少东西。舒怀姊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关系那么亲密,叫舒怀姊?还有,今天早上真的有下雨?对了,有日记。幸好有日记。她警戒着跳下了床,偷偷翻了翻书桌上的日记。日记却整整齐齐的满篇课业笔记。她忘了,她很久不写日记了。日记会泄露秘密。
仿佛未曾察觉她的紧张,张舒怀眼睛看向摆放在书柜里的熊猫娃娃。一只只彩色的、斑点的、花布的熊猫娃娃就三三两两藏在书间,像玩躲猫猫,也像在说悄悄话──读书之余,也别忘了熊猫呀!
“妳喜欢哪一只?浅粉红的?彩叶纹的?青花布的?还是……呀,这只受伤了?”
张舒怀说的是一只最单纯的、纯然黑色白色的熊猫娃娃。牠右手打石膏般地绑了绷带,绷带上写了方方圆圆的蓝字。
“‘心……唯……庆……仍然守约’?这什么?”
这能不能不说?能不说就不说。但能不说?活下去。要活下去。这是约定。这不能说。“好好地。跟自己约定,好好地。”
“好好地?”
“就是好好地。”
话说出口了,她后悔了。应该说是给未来的自己十个约定。约定好十八岁的约会,要回校开同学会,约定好十八岁的微笑,要像十岁、八岁一样,约定好十八岁……忘了,忘了有什么样的约定。没错,应该说“忘了”。竟然忘了可以说忘了。现在再说就晚了。可是,舒怀姊会再问一遍吧?到时候还能说出一样的答案?她忘了她刚刚回答了什么。对,忘了,就说忘了……
“要不要见队长?”张舒怀突然发问。
队长?蔚沛然?对,她都叫蔚沛然队长。因为蔚沛然家里开健身房,还组了一支棒球队,店外就贴了一张蔚沛然拍的宣传照──手执球棒,头戴头盔,头盔下两眼凝视看不见的对手;雄姿英发,蔚然如棒球队队长。但是……舒怀姊怎么知道?
她呆呆地看着张舒怀,突然忘了张舒怀问了什么。──对,“要不要见队长?”好奇怪的问题,难怪会忘了。
队长曾要找她,被她爸爸轰出去:“你是打死人的,还是搬尸体的?”爸爸急要保护她,就要和那些沾上案子的划个一清二白,当下一棒子啵地一声打破了队长的头。横飞的血花溅满地面,那鲜红色的……不对,爸爸没打死人,她得瞒着……不对,爸爸真没打死人。她眨着眼睛看着张舒怀。
──爸爸没打死人,那是梦……爸爸没打死人,那是梦……那是爸爸在梦里没打死人?那在现实里呢?伪装成梦?
“爸爸没……”
“妳爸爸同意了。但还需要妳同意。”
她胸口怦怦怦地仿佛定时炸弹要炸了。那么爸爸是瞒过了张舒怀?张舒怀还不知道爸爸打死了人?不对,张舒怀是要她去见队长的……尸体?爸爸怎会同意?
“不,不可能。”糟了,这么说不可能,会不会反证了爸爸打死了人?
张舒怀缓缓地说:“妳回答问题似乎都想了一段时间?不觉得奇怪?”
她张着口,呐呐地发不出声。──为什么?我不是做得很好?我不是一直很听话?不是都教我要小心说话?为什么还要责备我?
“不觉得自己没必要受这种罪?我也是这么对妳爸爸说的。你们隔离得再远、再澈底,检方依然会怀疑你们早串通好了,所以刻意断绝往来也就没有意义了,只会让你们活得更神经紧张。或者,你们要一辈子不见面?不奇怪?为什么要变成这样?”
她还是张着口。队长没死?那爸爸是打死了谁?无论是谁,她都要保守这个秘密。不对,爸爸真有打死人?她摸摸脸,烫得。
“见吧,那就见吧。”
没错。说不见队长,反而奇怪吧?“请不要做奇怪的事,这就是妳的任务。”这是“物理学家”说的。
■中.好久不见半半
好久不见半半。半半似乎又可爱了点,坐在椅子上,等着她要半半握手、转圈、站起、坐下。手指挠挠半半的下巴,半半的喉咙就舒服地咕噜咕噜响。她想学半半咕噜咕噜,只是怕有人看见,队长,还有爸爸。
队长就同她坐在二分之一小馆的二楼窗前,爸爸则隔了一张桌子,像个业余侦探,藏在报纸后。是在跟踪女儿约会?如果是就好了。爸爸同意让队长见她,不表示同意让队长单独见她,直一路隔了两、三步的距离,直到现在。
窗外下着毛毛雨,堤防外几个小孩撑着伞、跺着小碎步,坚持要玩红绿灯。是该坚持呀!再坚持也坚持不了多久,不久后你们的世界会全面亮起红灯,禁玩这种游戏。
她想起他们好久没玩红绿灯了。
她的生日礼物每每都是他们抓娃娃抓来的、各色各别的熊猫娃娃。“送妳一只替身娃娃,祝妳生日很快乐!”“这不是一般的娃娃喔!妳要是被鬼抓了,只要用这只娃娃,我们就会替妳当鬼喔!”“哇!我也好想要呀!真羡慕死妳了!”“真的?下次我们也送你一只。”“耶?”“哈哈哈!”……
“没事吧?”队长开口问。
她回过了神,脱口一句:“没事。”这才惊觉仿佛这些天的纷纷扰扰都是梦境,和死党在一起都忘了什么叫提心吊胆。
“没事就好。事情要结束了。”队长喝一口刚来的热可可说:“没事的,有一个很厉害的律师证明了我们没事,我们都是被人害的被害人,所以,没事的。如果妳可以的话,我想向舒怀姊说一件事。”
“什么事?”
“先约舒怀姊来吧,当面说比较好。没问题吧?”
她不知道,但不说不知道,只是拿一块饼干,点点头。队长就打了手机。舒怀姊好像有事,要晚一点来。
“最近如何?”
“最近如何?”她下意识撇头,看一眼那个藏在报纸后的“业余侦探”,“不好说。你呢?”
队长搔搔头:“都在家看电视,看棒球比赛。”
她喔地一声,没要接话。
“妳还是不看棒球?”
“看啊,只是看不懂。”
队长笑了。“看不懂还要看?还不要我教妳?还是,现在想学了?”
她嗯地一长声,摇头:“要是女孩子比你更懂棒球,很扫兴吧?所以……”撇头再看看“业余侦探”,不说了。怎能说“这种东西还是交给男朋友来教比较好”?
“还没学就会说大话?等妳懂棒球再说吧!”
“等我懂棒球,就不会觉得你有多厉害了。”说着装作手执球棒、两眼凝视,队长在宣传照上的模样。
队长只能苦笑。
“你没拿铁棒打人真是万幸……”
她话一溜出口,就后悔了。看得出来,队长脸色变了。勃喇勃喇地,隔桌再隔桌的翻报纸声适时响了一阵。真感谢爸爸跟来。她低头啜了一口热可可,再拿块饼干,递给队长,以示歉意。
队长接了饼干,正要往嘴巴送,停下了。“我先说律师说的事好了。”
队长说的律师就是到处走走串串的高强律师了。
高强律师说,现在一般的认知是王老师装在袋子里被人打死了,而打袋子的是三名学生。这样的认知对不对?很可能是错的。因为这很可能就是主谋想要人认知的。其实光想一想就会奇怪:为什么打死一个人得装上四只麻袋?是要让人忙得没空想东想西,譬如打开袋子看看?或是想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譬如吊上滑轮装置的那只麻袋其实装的只是等重的沾水绵花?这不无可能。那么王老师是谁打死的?算一算就知道,第一只麻袋吊给三名学生打,这期间推车从河滨公园推回学校后门口,运第二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再来到河滨公园,经历的时间就等同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一趟来回。接下来的三只麻袋只算比第一只麻袋多逗留在学校的时间。那么第二只麻袋就是多了从学校后门口运第一只麻袋到河滨公园,再从河滨公园推推车回学校后门口的时间,约等同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半趟来回。第三只麻袋则比第二只麻袋多了从学校后门口运第二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再回河滨公园运第一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最后回学校后门口要运第三只麻袋,就约等同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一趟半来回,比第一只麻袋多了两趟来回时间。第四只麻袋则比第三只麻袋多了从学校后门口运第三只麻袋到校外垃圾场,再回学校后门口要运第四只麻袋,就是从学校后门口到校外垃圾场跑一趟来回,比第一只麻袋多了三趟来回时间。如此,答案就显而易见了。王老师是有可能装在第一只麻袋,由三名学生打,打满一趟来回时间,但不也有可能装在第四只麻袋,由一名学生打,打满三趟来回时间?
“也就是三人连打十分钟造成的棍棒伤,只要努力点,一人连打三十分钟也做得到。”队长如此总结了高强律师的说法。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王老师装在袋子里被人打死了这一点肯定没错,而有三名学生吊打麻袋这一点也肯定没错,但要是以为打死王老师的就是这三名学生,那恐怕就有问题。是有人有意要我们产生这样的错误联想。”
她喃喃地又问了一句:“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有一个人躲在学校里、花了三倍时间打死了王老师。”
这什么意思?这“有一个人”是谁?将王老师装进麻袋的不就是简博约?难道是简博约?她不敢置信:“这……真的?真的?”
队长低下眼睛:“这样更好说明为什么要那么明目张胆地将麻袋吊上滑轮装置,众目睽睽下狠打、狠狠打。这也是律师说的。”
听起来像是这么回事。她叹了叹气。但还是不想相信。
队长说,律师还调查了麻袋的摆放位置,果然,没人记得是怎么摆放的。第一只麻袋和第三只、第四只麻袋调换了位置都有可能。
她挠挠半半的下巴,不知该说什么。王老师还是由王仁哲他们打死比较好,至少打死人的最后一下不知道是谁打的,对吧?半半只是眯着眼睛咕噜咕噜。
“舒怀姊来了。”
队长眼睛指向窗外,窗外可见张舒怀撑了伞,走着堤防来了。雨似乎大了。从天井望去,张舒怀进门的时候,门口已摆出了爱心伞,张舒怀差点把自己的伞收进爱心伞里。在想什么呢?她在二楼座上不觉紧张了一下,半半便翻了身,警戒地左右张望。
张舒怀上楼入座后,队长再将刚刚说的重说一遍。张舒怀看来并不意外,早猜到了这些事?她看看队长,不知队长意不意外。
“我相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否则无法说明为什么要用上四只麻袋。更何况──”队长两眼直视张舒怀:“简博约就是‘物理学家’。”
张舒怀眼睛睁了一下下。看来吓到了。
高强律师推论说,表面看来是三名学生打死了王老师,这太直接了,也显得另三只麻袋太多余了,所以恐怕是掩盖了一部分的真相。而这部分的真相有谁看得见?是谁将王老师装进袋子?是谁决定了王老师装进的袋子是第几只、决定了王老师是死是活、决定了这案子最终如何呈现、决定了这案子是成是败?能决定这一切的,会是简博约?还是“物理学家”?
因为律师的这番推论,也就让队长想起了一件事──
“简博约说过自己就是‘物理学家’。”
队长说着看了她一眼,再回看张舒怀,说那时候教室只有她,江心如,还有他在,而简博约走进教室突然说了自己就是“物理学家”,然后他们两人愣了一会,都没接话,简博约只能一脸尴尬离开了教室。事发突然,事后也没有后续,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现在回想,或许,简博约真的就是“物理学家”。
听错了吧?她愣了一会,没能接话。张舒怀眼睛看向她时,她只能一脸尴尬,摇摇头──别问我,我不记得这件事。
队长眉头皱了皱,又展平了,说:“妳可能忘了,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那是期中考后的体育课,妳身体不舒服,我当值日生。还不记得?……也好,至少证明了我们不是说好的。至少我们诚实面对了各自的记忆,也不必去猜有谁想骗谁说什么假话。”
她神经微微紧绷。队长……难道期待她配合说什么假话?
“假设真如简博约所说,他就是‘物理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张舒怀问。
队长想了一下:“我必须诚实地说,我确实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也以为听错了。”
“还记得叶沁吗?你们的伙伴,至少以前。”
这个……她还记得,微微点头。看向队长,队长却没什么反应。她也不敢微微点头了。
“叶沁,你们从小玩红绿灯的伙伴,她刚开学就没来上学了。你们却没有人去看她。不,是有一个人去看,就是简博约。”
“叶沁……她怎么了?”她现在问出口,反而作贼心虚,但又不敢像队长那样强作镇定。
“妳为什么不去她家探问?”张舒怀反问。
她低了低头。不,不能低头,低头就心虚了。抬头看了队长一眼,还是队长镇定。
队长微微皱眉:“我们是没去看她,但她也没来看我们,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沁,和简博约一样,学业成绩在你们当中数一数二。也就是,她和简博约一直分占你们当中的一、二名。叶沁拒学之后,简博约去看她了。然后,简博约肩膀严重磨伤,说是从堤防摔下来。再然后,就再也不见你们一起出现在这里,二分之一小馆。你要说说怎么了吗?”
“坦白说,不知道。忙吧。”
“是什么原因,叶沁拒学?是什么原因,简博约受伤?是什么原因,你们集体漠视了叶沁和简博约?”
“……课业繁重?大家都只顾得了自己,顾不了别人。”
“课业繁重?如果有人说是霸凌呢?”
“霸凌?谁说的?”队长一反方才漠然不惊的反应,声音急了起来:“简博约说的?简博约说的就是对的?不过成绩好了点,就什么都对?那我说的呢?就是妄想?哼!要我说,是简博约在妄想!被害妄想!”
妄想?是谁在妄想?是简博约妄想自己被霸凌,还是队长在妄想简博约妄想自己被霸凌?张舒怀眼睛看向了她,她赶紧摇摇头──别问我,我不知道这件事。
张舒怀转说刚才队长手机打来时,她就在叶沁家里。叶沁生病了,看来是压力过大,只想在家自学,也不请家教,甚至不太说话,学了手语,还有,理了光头,现在才慢慢长了些短短的头发。
“她的头发是之前遭人乱剪一通,东秃一块、西秃一块,才只好剪光了。将女孩子的头发剪得不得不剃光干净,这是逃避学业压力?还是霸凌?”
队长两眼凝视着张舒怀,仿佛面对那个看不见的投手。球来了吗?要挥棒了吗?
“她逃避上学,但不逃避学业,甚至花时间自学手语,怎么说都不像是课业压力造成的吧?”
“那么,像霸凌吗?”队长反问。
张舒怀点点头:“语言暴力会让人逃避暴力当下的语言。她恐怕在校的时候受了语言暴力,而且……”
“她也说是霸凌?”
直球对决?
“你觉得呢?”
曲球?
“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课业压力。所以忙着用功,可能疏忽了什么。”
“包括忽视叶沁为什么没来上学,还有简博约为什么受伤?”
“因为我们眼前有一件无法忽视的事:林守震的成绩掉下来了。”
“叶沁没来上学是在林守震考试之前吧?”
“那么就是:在林守震成绩掉下来之前,大家都不自觉地意识到课业压力。”
“真的?”
“当然……”
队长还是没挥棒。球来了,避开了。还是挥了棒?在挥棒?别问她,她对棒球一知半解,只是感觉队长的神情一如宣传照上的专注。大腿有东西碰了碰。低头看看,是半半用脚掌轻轻地抓了抓。半半也感到人类语言之间透出的压力了?看着半半无辜的大眼睛,她突然感到害怕。想起了一件事:半半抓伤过她。
***
“恐怖谷理论:越像人,越有亲近感,但太像人,却有恐怖感,像是看见了怪人,有怪病的人。人会远离有怪病的人,以防传染,这是天性。动物就是这样。有点像人有点不像人才会讨人喜欢。譬如猫,譬如狗。要是猫狗长得像脸上长了猫毛、狗毛的人那就恐怖了。但毕竟动物还是动物,有野性,人们接近牠们的时候都忘了牠们不懂人际关系、生活礼仪……”“呀呀呀!不过教半半不小心抓伤了一下,也值得你讲那么多?”是呀!很痛的,大概。几人七手八脚乱包乱扎,将教半半抓伤的手指绑得像打了石膏。“不过教半半不小心抓伤了一下,也值得包扎得那么夸张?”“哈哈哈!这是反恐怖谷理论。要是包扎得太认真,就把半半抓伤人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这样会产生心理障碍。所以,不妨转移注意力。再夸张点,我们都绑上绷带吧!”“对!再签名、签字!”“当然!有饭分着吃,有苦也分着吃!”“感情好得像手上的手指,脚上的脚趾!”“脸上的眼屎、耳屎、鼻屎!”“你少恶心了!”“再恶心,我也是沾在你脸上的!哈哈哈!”……
哈哈哈!当时好得真像手上的手指,脚上的脚趾,就是分开了也分不开。几个人说说笑笑,就把半半抓伤手指这件事玩笑了过去。那时候简博约、叶沁都在。都忘了是什么时候把这样的感情分得一干二净。好像有一场暴雨……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