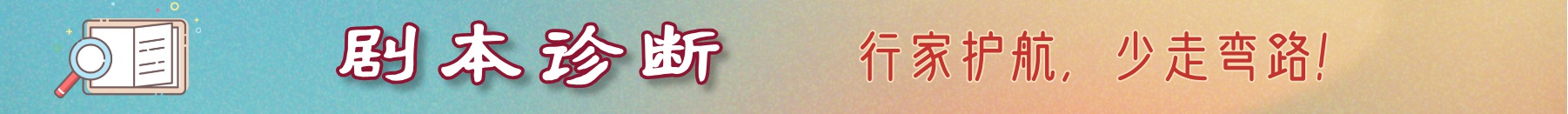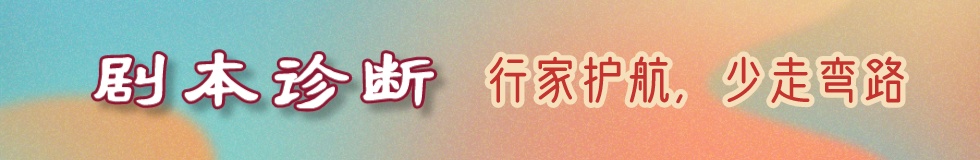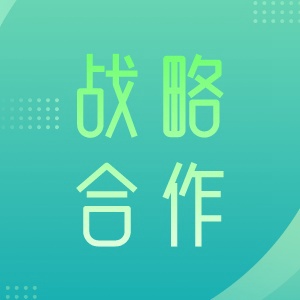权属:原创
字数:37503
阅读:1133
发表:2025/2/20
14章 家庭,军事,历史 小说
《史家绝唱》第1-2章
推荐
1-2
3
…
14
全部
-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新房屋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建成了,那是两栋南北相向,东西并列的房屋, 每栋房屋又分为上屋和下屋,上屋和下屋中间有一长方形的天井,天井的光 线照下来,使上下厅堂特别明亮。上下屋的外墙都有高高的马头墙耸立着, 远远的看去气势非凡,东西两屋相距九尺,有过道相连,房子的两边还建了偏房,西边的作厨房用,东边的则放置粮食和各种杂物等。新房屋比老宅面 积大了许多,一直盖到了史忠方填埋财宝的地方,后来有人猜测史老太爷急 着修建房屋,可能是对那些财宝埋在院子里不放心,他要将那些财宝置于自 己的脚下才能踏实。确实,史老太爷安排自己和已被称为老祖宗的母亲住在 东屋,两个儿子则住在西屋,而东屋正是他填埋财宝的地方。吴瑞芳对老太 爷这样的安排有些不满意,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史老太爷不但重建了房屋, 还将整个史家大院都重新整理了一下,只有那院内那棵传说有几百年的樟树, 依然保留着,史家人已经将这棵树看作是神树,是保佑史家兴旺发达的祥瑞 之树。那樟树一直是史家的象征,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这棵大树, 看见这棵大树,就能想起史家。现在它和史家两栋新房屋一起,显示着史家 在史镇的威严、财富和地位。史家的房屋建成了, 但里面窗户和梁柱上的雕刻, 却用了三个雕刻师雕了三年才完成。房屋建成后,史老太爷,便为自己的小 儿子成了亲,对方是不远处李家村李老爷的女儿。
四
史老太爷的回来,为史家带来了不少的热闹。但有一个人却感受不到兴 奋和热闹。他就是大儿子史世清。史世清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相当短暂, 他始终感觉到父亲的威严和压抑,他记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短暂的日子里都 是沉重而又不快乐的。据说,史世清出生前一天,有一只乌鸦在院中老樟树 不停地鸣叫了一整天,人们怎么驱赶,它也不飞走,第二天,史世清出生时 是脚先落地,史忠方先生心中非常的不愉快,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此从小 对史世清就另眼相看,总认为他随时会给家庭带来灾祸。再加上史世清童年 的时候特别贪玩,不喜欢读那些枯燥无味的圣贤书籍,在史忠方面前总是为 背不出那些拗口的、艰涩难懂的经书而受到呵斥,有时甚至是痛打。幸好有 爷爷和奶奶的宠爱和庇护,才逃过许多的打骂,爷爷奶奶是疼爱这个长孙的。 他从小就惧怕父亲,不敢和父亲多说话,更不敢和他说笑了。他小的时候却 喜欢到鄱阳湖旁去游玩,他常常一人对着那浩瀚的神秘的鄱阳湖望着,似乎 那里有自己熟悉的东西,他似乎能隐约地听见漫无边际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在 呼唤着自己。他喜欢和那些给自己家放牛的孩子一起玩耍,他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在荒山野外游玩,欣赏他们掏鸟蛋抓鱼虾的本事。这正是史忠方所 失望的,史家一直是长子继承家业,一代一代地为走上仕途而用心攻读诗书, 从而为史家光宗耀祖,成就功名。可自己的这个儿子,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 天赋,读那些圣贤经书时简直是愚蠢至极。
在史世清七岁的时候,史忠方考上了进士,步入了仕途,到外地当县官 去了。史世清没有随父母一同前去,一是史忠方对他极不满意,另外爷爷和 奶奶也舍不得让他离开,他们要自己的这个长孙留在自己身边,陪伴自己。 史家虽然是大户人家,但一直人丁不旺,到史忠方这一代已是三代单传,而 且史忠方是自己父亲四十岁上得的儿子,因此,他留下史世清也是为了让父 母不太孤单,史忠方是个孝子。
自此以后,史世清自由了许多,再也没有人严厉地管教他了。他虽然被 送进学堂,但他开始逃学,和那些放牛娃们上山掏鸟窝追野兔,有时到湖边 学人家抓鱼虾扒黄鳝,但他总是抓不着,有时鱼到了他的手中也滑跑了,他 非常懊恼,于是更加用力,也更加着急,自然也就更加抓不着鱼儿。同伴们 都被他的不规范的近似滑稽的动作逗乐了,说这些事不是他这样的少爷公子 干的,他不信,但最后他只能认输。再大一些后,他有时还跟渔船一起到湖 中间去看渔民撒网打鱼,每当看到网上一网鱼时,他便高兴得手舞足蹈。渔 民有时送些小鱼小虾和小乌龟之类的东西给他,他更是爱不释手。他喜欢听 渔民及老人们讲那些关于鄱阳湖里的妖精鬼怪和神仙的故事,来到湖中时, 他觉得这漫无边际的深邃的鄱阳湖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神秘,他总是问那 些打鱼的,这个湖到底有多宽,为什么看不到边际,那个对面有岸吗?那个 岸边有人吗?那些人和我们一样吗?那些渔民觉得这些问题太可笑了,也太 莫名其妙了,因为他们从来不去想这些事,因此也不知道这些事,他们只是 祖祖辈辈在这一带打鱼,没有必要知道那些事。他慢慢地长大了,也越来越 放纵了。这时的爷爷觉得问题严重了,他也觉得史世清作为史家的长孙和继 承人,必须传承史家的传统,读圣贤的经书求取功名。史世清小时候的淘气 他认为没有什么,长大了自然会好起来的。但现在他看不出史世清有收性的 苗头,而自己又年事已高,很难管得住史世清,因此爷爷修了一封家书,派 了一个能干的家仆将他送到为官的史忠方那儿去。那一年他已经十四岁了。
那时的父亲还是个县官。七年不见,他觉得父亲变得有些陌生了,也更威严了,因此他也显得更加拘束了。过了几年自由自在生活的他,对新的生 活新的环境显然有些无所适从。而且父亲还给他定下了许多的规矩,什么写 字的姿势要端正,不能东倒西歪;读书的声音要洪亮,不能有气无力;吃饭 时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不能吃出响声,更不能说话;早上起来要向 父母请安,一般不能出去,出去要向父母报告;走路要稳重端庄,不能急匆 匆的;客人和长辈来了,要鞠躬行礼,不能问这问那,不能抢着说话,不该 自己说话不能插嘴等等。他听了头皮发麻,他很难按照这些规矩去做,即使 做了也不能令父亲满意,因此免不了要挨父亲的训斥。你以为这是史镇的山 野之地,这是官府,就要有官府子弟的样子,你看看你写的那些字,写的那 些文章,那像我史家的子弟,你再看看你弟弟写的文章,读的诗书,那才叫 读书,你该好好向你的弟弟学学。
父亲为了使他能尽快地走上正轨,特地请来了一位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 每天教他学习经书。主要讲的是《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他硬着头皮学, 却越学越没劲,越没劲却越要学。他感觉在这里是度日如年,觉得比坐牢还 要难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先异常活跃的一个人,变得非常忧郁孤独, 从此他的眼神中永远游荡着迷离的孤独的神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 学这些他认为毫无用处的东西,父亲告诉他学好这些东西就能像父亲一样, 出人头地,成就功名,就能做大官,光宗耀祖。可他并不认为做官有什么好的, 就那些规矩就使他觉得做官没什么乐趣,他不愿意做官,因此就更没有必要 学这些“子曰诗云”了。然而他只能在心中想着,他不敢向父亲说出自己的 想法,他知道如果自己说出来会招来更狠的训斥。
史忠方原以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并不笨拙,只是从小没有严格的管教,被 爷爷奶奶惯坏了而已,只要给他施加压力,严格要求,他自然会走上正轨的, 也自然能为史家争取功名的,他对儿子还是抱有信心的。但现两年过去了, 史世清依然不开窍,气得史忠方大骂其真乃朽木不可雕,竖子不可教也。慢 慢地,史忠方放松了对大儿子的管教,这也表明他对史世清彻底失望了,他 只能寄望于天资聪慧的小儿子史世源了。这对史世清来说,却是好事。因为 从此以后,虽然书还在读,但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没有再来了,他也因此 有机会到外面去溜达。虽然不如在史镇那样自由,但总有机会能到官府外面 去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那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啊。
这是一个靠近长江的县城,和自己的家乡一样,有很多的湖泊,自然也 有很多的船只,只是这里的江面没有鄱阳湖那样宽广,但这些船只却比鄱阳 湖边的渔船大多了。他看见那些船只就思念起自己的家乡来。由于人生地不 熟,开始他只是远远地站着观望,慢慢地他抑制不住靠近船只,看看是否有 从家乡来的船只,江右省的船倒是不少,但没有双阳县的。他不知道江右省 有多大,也不知道这里离家乡有多远,再加上他对这个地方的方言有些听不 懂,因此他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然而,只要一有空,他还是会到江边去的, 渐渐地,他和那些船主和船工都混熟了,他慢慢地了解了这些船都是行商的, 不像自己家乡的那些小船只是打鱼撒网。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船和这些人, 他特别羡慕这些在船上生活的人,他们行走于江湖之上,天地之间,无拘无束, 是多么自在逍遥啊。这比待在官府衙门有意思多了。他梦想着,要是有一天 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那该是多么洒脱。然而他每天一回到官府,就知道这 种事永远只能是梦想,父亲是不可能让自己去做这种事的。不但不能做,连 看的机会也慢慢地少了。由于他对江边的船只越来越入迷,因此出来的次数 就越来越多,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终于被父亲知道了,在被痛骂一顿后, 又恢复了以前的管教,他的自由度又被缩小了。
他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近五年的时间,终因爷爷的去世而结束。那一年 他十九岁。爷爷病故后, 父亲带着家人回乡奔丧。爷爷的丧事办得隆重庄严, 父亲的哭声惊天动地,感动了史镇的人们。史世清没想到古板而又严肃的父亲, 竟然是如此的多情,这和他所认识的父亲是完全不同的。就在这一刻他有些 自责,是自己不好好地读书,以至于让父亲失望而生气。父亲的这种印象只 是那么短的展现在他的面前,没多久又恢复了以往的严厉,从那以后,他再 也没有感到过父亲的亲切。按清朝官吏丁忧制度,史忠方要在家丁忧三年, 这期间他为史世清订下了终身大事,对方便是双阳县另一大家族,吴镇的吴 家千金小姐吴瑞芳。吴家虽然不如史家那么历史久远,但近几十年来,吴家 的势头有超过史家的趋势,吴家家产丰厚,人丁旺盛,在吴镇已经没人能比了。 吴镇又是双阳县乃至整个右江水道的门户之地,四面八方的商贾云集于此, 是双阳县最繁荣的集镇。吴家自然与这些商贾有来有往,吴家的名声也因此 传播得很远。开始, 史家人还有些看不起吴家,因为吴家出的官没有史家的多, 也没有史家出的官品级高。但近些年,吴家出的官是越来越多了。史忠方想还是应该和吴家联姻,也许能从吴家带来些人气来,让史家也能人丁旺盛。 吴家的吴老爷,早就对史镇的史家仰慕已久,两镇虽然相距不远,但来往不 是很亲密,现在史忠方亲自托人前来说媒联姻,哪有不应之理,就这样史世 清与吴瑞玉的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史忠方丁忧期满,便要为史世清和吴瑞玉完婚了,并亲自为他们操办婚 事的。史世清在此之前虽然和吴瑞玉见过几次面,按那时的乡俗,未婚男女 是不能随便说话的,他们的见面都是史世清逢年过节时前去吴家参拜老丈人 之时相见的。吴瑞芳对史世清并不热情,史世清以为这是她害羞或要保持大 户人家小姐派头的原因。其实吴瑞芳对这门婚事是不情愿的,她是吴老爷的 独生女,而且是最小的,吴家又是吴镇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庭,因此她的 成长环境使她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表现出一种很强支配的欲望,伺候她的 丫环稍不如意就要受到责骂。她天资聪慧,学什么东西都特别快。她有过绚 丽的花一样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跟哥哥们一样走出吴镇,走出双阳, 到更远的地方去见更大的世面。她的大哥吴浩淼是她的榜样,因为他还去过 日本留学,回来后总是给她讲外面的新生事情,她听得都入迷了,她要哥哥 带她出去,她要成为一个女中豪杰,哥哥爽快地答应了。然而哥哥吴浩淼参 加了革命党,常常东躲西藏,要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回来一次,因此哥哥没有 实现带她出去的承诺。然而吴老爷怎么都不想让自己唯一的女儿走出去,他 虽然生活在吴镇,见过南来北往的各种各样的人,思想也没有史老太爷那么 正统,但他依然以为女孩子还是应该在家的好,也不能嫁得太远。史忠方派 人来提亲,他很是高兴, 一来,这个双阳县有名的富贵之家终于愿意和吴家 这样的后起大户联姻了,这是对吴家的认可,他知道吴家不论是财富还是家 族人员都超过了史家,但双阳人似乎还是认可史家的地位。而吴瑞芳却十分 的不情愿,她不想留在双阳这个偏僻的地方,可史镇是一个比吴镇更偏僻的 地方。再者, 她听人说史家这个大公子是一个不成器的人,不会有多大出息, 自己的一生和这个人联系在一起,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悲哀的结局。然而父亲 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平时他虽然也很娇惯这个女儿,但在婚姻这样的大事 情上,他必须表现一个大家族族长的威严,吴瑞芳只能恨自己命苦,恨那个 向自己提亲的史忠方。婚事操办完毕,史忠方就得到朝廷的任命绍书,并得 到升迁任职知府。他便要重返湖北就任新职。这一次,他不准备将史世清带在身边,而是把史世清留在家中, 一来史忠方是个独子,无兄无弟,必须让 自己的儿子留下来照顾自己的母亲,另外家里这么大的家业也应让人看守, 二来史忠方很清楚知道这个儿子是没有希望成就功名的,只希望他能经营好 自家的祖业就足矣。
史镇人都夸史世清有福气,娶了一个天仙般的美女。然而史世清却没有 表现出应有的欢乐和幸福,因为从结婚的那天晚上起,他就感受到了吴瑞芳 的冷漠和高傲,这种冷漠和高傲完全不是姑娘小姐们初嫁时的害羞和故作清 高的表现,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内心深处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轻蔑和漠然,其 中似乎夹杂着憎恨和厌恶。对史世清来说,自己娶的最多是一个冷美人。开 始史世清还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等到吴瑞芳熟悉了这个家,也许会改变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冷漠和隔膜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地增长。 夫妻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情感交流,他们的对话总是在一种陌生的,将对方 推开的语境中进行的,史世清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这个妻子为什么会如此,更 不了解她需要什么。她总是说你们史家什么的,我们吴家什么的,似乎她永 远都不想将自己融入这个家庭中来,弄得史世清心灰意冷。他没有想到自己 躲开了父亲的威严,却又要面对这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讥讽和嘲弄。他 陷入了一种更失望郁闷的情绪之中。
然而,吴瑞芳却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寄托, 因为她发现这个史家管理太混 乱了,许多事情都没有了规矩,根本不像外面人传说的那样,史家是一个有 几百来年根基的上等人家。那是她嫁来后的一个月后,她回娘家住了几天, 又回到了这个埋葬她梦想的陌生的家庭,她回来的第一个早晨既然没有人给 她端洗脸水,她按捺住自己的不满,等了好一会,后来她确信不会有人端水 来了,她自己走出了房门,来到了老太太房间,问奶奶史家是否有佣人,史 家的佣人是否给主人端洗脸水,我吴瑞芳是史家的主人吗?当奶奶明白了吴 瑞芳为什么不满后,叹息了一声说,都是清儿惯坏了这些下人们,很多规矩 这些下人们都不讲了,我又老了,很多事管不了。吴瑞芳说不是还有管家吗? 他也不管事吗?他不管事当什么管家。这件事以那位伺候少奶奶的女佣被辞 退而得以平息。从此吴少奶奶便开始过问史家的事了, 她征得老太太的同意, 决定将史家进行一番大的整治。首先,她为家里定下了许多的规矩:家里人 的开支要统一管理,管家不能随意支配,必须经过自己的同意,每笔支出要都记清楚,每月要向她报账。家里人的零用钱要统一按规定支取,任何人不 得超支,有特殊情况要经过老太太的同意。每人每年的衣服添置也要定数量 和钱数,柴米油盐要由专人管理,制定标准,平时用多少,一般节日用多少, 大年大节用多少等要精打细算,不能随意乱用。另外,吃饭时主人和下人要 分开进行,下人吃饭在规定的地方,不能端着碗在院子里到处走。家仆和佣 人的工钱,要重新制定,按干活的多少、轻重来增减, 同时对那些不听主人话, 不服从管家安排,或做事不卖力的要克扣工钱。下人每天早起要向主人请安, 对主人说话要恭敬低首,不能大声大气,到外面不能乱传史家内部的事,家 仆们也不能在背后对主人说三道四,更不能掺和主人家的家事。她还制定了 对史家家仆们的惩罚办法,谁违背了她定下的规矩就要按规定克扣工钱,严重的要进行体罚。自从爷爷死了以后,史世清管理了史家三年,可这三年他 将史家的规矩乱了差不多,史家的家业被弄得乱七八糟,可吴瑞芳用了不到 三个月,史家被整治得有条有理,焕然一新。也正在此时,她要求下人称她 为吴少奶奶,她要显示自己吴家的尊姓,而不是依附于史家的荣耀。老太太 天性仁厚,没有计较这称呼,默许了吴瑞芳的一切行为。史家的上上下下以 及史镇的人都对史家的这个新媳妇投来敬佩和畏惧的目光。吴瑞芳管家的才 能让所有的人都折服了,史世清自然自叹不如,这更加大了他和吴瑞芳的距离。 老太太倒是十分的高兴,她不清楚孙子和孙媳妇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发现了 孙媳妇的泼辣和干练,史家正需要这样的能干媳妇,这是史家的幸事。
五
史世清在家成了多余之人,他没有什么事可管,也说不上什么话,原来 他就厌烦家里那些琐碎之事,现在突然空闲下来,他又有点不适应。因此他 就常常到镇上去,和一些朋友打打牌喝喝酒,吴瑞芳并不怎么管他,由着他去, 因为她看着他在家就有些心烦。但如果他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她就会斥责, 并将他赶到别的房间去睡觉。后来镇上有人组织业余戏班唱戏曲,本来人家 是想要他帮着筹点款,但他不但出了钱还积极参加,成了一名打鼓的先生。 他学得特别努力,接受得也特别快,他对那些曲谱和唱词记得特别牢,几乎 可以脱离戏本,全不像他背那些圣贤经书那么笨拙。很快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打鼓手。打鼓手是整个戏曲乐队的指挥,随着他的鼓起板落,锣声琴声唢 呐声或激昂或低沉地演奏起来,他感到特别的舒畅。此时的他总是微闭着眼睛, 随着乐队的旋律和演员的唱腔晃动着双手和上身,他完全沉浸在其中,感受 着戏曲中的悲欢离合和人物的喜怒哀乐,外部世界的、不愉快的事情全部离 开了他。
就这样,他度过了婚姻的最初几年,和妻子的关系依然是不冷不热,两 人的心灵之间依然存在一条长长的、深深的鸿沟。两人都十分清楚,这条鸿 沟是无法填平的,虽然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史成杰、二儿 子取名为史成仁,都是父亲给取的。现在父亲回家了,而且再也不离开了,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打发日子的方式,又要被打破了。他除了要面对冷漠的妻 子,又要应付威严的父亲。他清楚地知道, 父亲回家后绝不允许自己出去打鼓, 虽然只是业余的,但还是与戏子有关,这种下九流的行为,怎么能是史家这 样的书香门第的人干的事,做这种事有辱史家的声誉。
郁闷的史世清又像小时候一样经常到湖边徘徊,长久地望着茫茫的湖面 排解胸中的郁闷。他对这湖依然有一种说不清的迷恋,鄱阳湖虽然不像小时 候那样神秘,但仍然在诱惑着他。这一天他又无所事事地来到湖边,眺望着 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湖面,突然他被那两只官船吸引住了。这时已是春天了, 湖面的水已经上涨了不少,那两艘搁浅的船已经被上涨的水浮起来了,在那 里摇晃着。由于已有半年多无人过问,那船已经有些陈旧了,全不像刚来时 那样威武漂亮了。他的脑海顿时出现了一个令他自己都激动不已的大胆的想 法,他完全可以将这两只船改造成商船,他可以像他在湖北看到的那些商人 一样,行走于江湖之上,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他就 无法抹去,虽然他知道父亲很难同意他这样做,但他必须试一试,他要尽力 去争取。他马上回到家里,鼓足十分的勇气找到父亲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亲在书房里看书,同时在教两个孙子史成杰和史成仁读书,他在门口 叫了一声:“爹。”
史老太爷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在他的记忆中,这个儿子是从来没有主动 找自己说过话的,今天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向自己说。他等了一会,不冷 不热地问道:“有什么事吗?”
史世清在和父亲的目光对视的那一瞬间,开始犹豫了,父亲的目光像闪电一般直刺向自己的心脏,父亲似乎知道了自己要说什么似的,似乎已经看 穿了自己的一切想法。而且父亲的目光中充满了不信任感,他预感到父亲会 否决自己的任何建议和想法,他就这么愣愣地站在那儿,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父亲等了一会,又冷冷地说: “有什么事快说,我还要教孩子读书呢。没事 就玩你的去,不要影响你的两个儿子。”
史世清涨红着脸,用他平生最大的勇气开始说了,因为他知道他不说就 会失去机会,就永远不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干。他说: “我有一个想法, 想和爹商量一下。”
史忠方将书放下,看了一眼两个孙子,又看了一眼史世清。然后起身对 两个孙子说: “你们在这里好好背书, 我和你们的爹有话说,一会就回来。”
史忠方估计儿子和自己商量的事很重要,但他知道这个儿子不会有什么 好事,因此他必须避开两个孙子,免得让儿子在孙子面前难堪。史忠方在前 面走,来到他会见重要客人的房间,然后叫史世清把房门关上。“你现在可 以说你的事了。”史忠方依然面无表情地说。
史世清清了清嗓子,极力使自己能平静下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开始说: “爹现在回家了,没有了俸禄,我们史家不能坐吃山空。我想自 己也这么大了,从来没为爹分过忧,也没为家里出过力。因此我想为家里做 些事情。正好爹带来的那两只官船在那里闲着,我可以利用它,将他们改造 成商船,到外去跑跑生意,总能为家里补充财物。爹觉得如何?”
史忠方就知道这个不中用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史家乃世代官绅 门第,书香世家,怎么着也没沦落到成为商贾之流。商贾之人乃唯利者是也,
怎么能保住史家的仁义之名?但史忠方还是克制了自己,他尽量保持平静地 说:“你可以为史家做许多事情,史家这么一个大的家业还没有你干的事吗?”
史世清说: “家里的事有瑞芳她管着,我哪插得上手。那两只船如果没 有人管,就会烂在水里的。”
“烂在水里你也别想去碰它。它本来就不是我们家的船,你操那么多心 干吗? ”史老太爷提高了声音,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你还好意思说,如果 不是你不务正业,史家会轮到一个女流之辈、一个外来人管家吗?你说得好听, 想为家里争点财富,其实是你的野性未灭,史镇装不下你了,你还想到外面 去疯。我告诉你,只要我没死,史家人就别想经商。我不想让史家的名声和、家业败在你的手中。史家虽然没有我的俸禄,但还有几百亩良田,足够我史 家的子孙们吃穿,你就给我死了这条心吧。”史老太爷说完站起来打开房门, 走出去了。留下史世清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四
史老太爷的回来,为史家带来了不少的热闹。但有一个人却感受不到兴 奋和热闹。他就是大儿子史世清。史世清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相当短暂, 他始终感觉到父亲的威严和压抑,他记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短暂的日子里都 是沉重而又不快乐的。据说,史世清出生前一天,有一只乌鸦在院中老樟树 不停地鸣叫了一整天,人们怎么驱赶,它也不飞走,第二天,史世清出生时 是脚先落地,史忠方先生心中非常的不愉快,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此从小 对史世清就另眼相看,总认为他随时会给家庭带来灾祸。再加上史世清童年 的时候特别贪玩,不喜欢读那些枯燥无味的圣贤书籍,在史忠方面前总是为 背不出那些拗口的、艰涩难懂的经书而受到呵斥,有时甚至是痛打。幸好有 爷爷和奶奶的宠爱和庇护,才逃过许多的打骂,爷爷奶奶是疼爱这个长孙的。 他从小就惧怕父亲,不敢和父亲多说话,更不敢和他说笑了。他小的时候却 喜欢到鄱阳湖旁去游玩,他常常一人对着那浩瀚的神秘的鄱阳湖望着,似乎 那里有自己熟悉的东西,他似乎能隐约地听见漫无边际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在 呼唤着自己。他喜欢和那些给自己家放牛的孩子一起玩耍,他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在荒山野外游玩,欣赏他们掏鸟蛋抓鱼虾的本事。这正是史忠方所 失望的,史家一直是长子继承家业,一代一代地为走上仕途而用心攻读诗书, 从而为史家光宗耀祖,成就功名。可自己的这个儿子,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 天赋,读那些圣贤经书时简直是愚蠢至极。
在史世清七岁的时候,史忠方考上了进士,步入了仕途,到外地当县官 去了。史世清没有随父母一同前去,一是史忠方对他极不满意,另外爷爷和 奶奶也舍不得让他离开,他们要自己的这个长孙留在自己身边,陪伴自己。 史家虽然是大户人家,但一直人丁不旺,到史忠方这一代已是三代单传,而 且史忠方是自己父亲四十岁上得的儿子,因此,他留下史世清也是为了让父 母不太孤单,史忠方是个孝子。
自此以后,史世清自由了许多,再也没有人严厉地管教他了。他虽然被 送进学堂,但他开始逃学,和那些放牛娃们上山掏鸟窝追野兔,有时到湖边 学人家抓鱼虾扒黄鳝,但他总是抓不着,有时鱼到了他的手中也滑跑了,他 非常懊恼,于是更加用力,也更加着急,自然也就更加抓不着鱼儿。同伴们 都被他的不规范的近似滑稽的动作逗乐了,说这些事不是他这样的少爷公子 干的,他不信,但最后他只能认输。再大一些后,他有时还跟渔船一起到湖 中间去看渔民撒网打鱼,每当看到网上一网鱼时,他便高兴得手舞足蹈。渔 民有时送些小鱼小虾和小乌龟之类的东西给他,他更是爱不释手。他喜欢听 渔民及老人们讲那些关于鄱阳湖里的妖精鬼怪和神仙的故事,来到湖中时, 他觉得这漫无边际的深邃的鄱阳湖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神秘,他总是问那 些打鱼的,这个湖到底有多宽,为什么看不到边际,那个对面有岸吗?那个 岸边有人吗?那些人和我们一样吗?那些渔民觉得这些问题太可笑了,也太 莫名其妙了,因为他们从来不去想这些事,因此也不知道这些事,他们只是 祖祖辈辈在这一带打鱼,没有必要知道那些事。他慢慢地长大了,也越来越 放纵了。这时的爷爷觉得问题严重了,他也觉得史世清作为史家的长孙和继 承人,必须传承史家的传统,读圣贤的经书求取功名。史世清小时候的淘气 他认为没有什么,长大了自然会好起来的。但现在他看不出史世清有收性的 苗头,而自己又年事已高,很难管得住史世清,因此爷爷修了一封家书,派 了一个能干的家仆将他送到为官的史忠方那儿去。那一年他已经十四岁了。
那时的父亲还是个县官。七年不见,他觉得父亲变得有些陌生了,也更威严了,因此他也显得更加拘束了。过了几年自由自在生活的他,对新的生 活新的环境显然有些无所适从。而且父亲还给他定下了许多的规矩,什么写 字的姿势要端正,不能东倒西歪;读书的声音要洪亮,不能有气无力;吃饭 时要细嚼慢咽,不能狼吞虎咽,不能吃出响声,更不能说话;早上起来要向 父母请安,一般不能出去,出去要向父母报告;走路要稳重端庄,不能急匆 匆的;客人和长辈来了,要鞠躬行礼,不能问这问那,不能抢着说话,不该 自己说话不能插嘴等等。他听了头皮发麻,他很难按照这些规矩去做,即使 做了也不能令父亲满意,因此免不了要挨父亲的训斥。你以为这是史镇的山 野之地,这是官府,就要有官府子弟的样子,你看看你写的那些字,写的那 些文章,那像我史家的子弟,你再看看你弟弟写的文章,读的诗书,那才叫 读书,你该好好向你的弟弟学学。
父亲为了使他能尽快地走上正轨,特地请来了一位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 每天教他学习经书。主要讲的是《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他硬着头皮学, 却越学越没劲,越没劲却越要学。他感觉在这里是度日如年,觉得比坐牢还 要难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先异常活跃的一个人,变得非常忧郁孤独, 从此他的眼神中永远游荡着迷离的孤独的神色。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 学这些他认为毫无用处的东西,父亲告诉他学好这些东西就能像父亲一样, 出人头地,成就功名,就能做大官,光宗耀祖。可他并不认为做官有什么好的, 就那些规矩就使他觉得做官没什么乐趣,他不愿意做官,因此就更没有必要 学这些“子曰诗云”了。然而他只能在心中想着,他不敢向父亲说出自己的 想法,他知道如果自己说出来会招来更狠的训斥。
史忠方原以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并不笨拙,只是从小没有严格的管教,被 爷爷奶奶惯坏了而已,只要给他施加压力,严格要求,他自然会走上正轨的, 也自然能为史家争取功名的,他对儿子还是抱有信心的。但现两年过去了, 史世清依然不开窍,气得史忠方大骂其真乃朽木不可雕,竖子不可教也。慢 慢地,史忠方放松了对大儿子的管教,这也表明他对史世清彻底失望了,他 只能寄望于天资聪慧的小儿子史世源了。这对史世清来说,却是好事。因为 从此以后,虽然书还在读,但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没有再来了,他也因此 有机会到外面去溜达。虽然不如在史镇那样自由,但总有机会能到官府外面 去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那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啊。
这是一个靠近长江的县城,和自己的家乡一样,有很多的湖泊,自然也 有很多的船只,只是这里的江面没有鄱阳湖那样宽广,但这些船只却比鄱阳 湖边的渔船大多了。他看见那些船只就思念起自己的家乡来。由于人生地不 熟,开始他只是远远地站着观望,慢慢地他抑制不住靠近船只,看看是否有 从家乡来的船只,江右省的船倒是不少,但没有双阳县的。他不知道江右省 有多大,也不知道这里离家乡有多远,再加上他对这个地方的方言有些听不 懂,因此他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然而,只要一有空,他还是会到江边去的, 渐渐地,他和那些船主和船工都混熟了,他慢慢地了解了这些船都是行商的, 不像自己家乡的那些小船只是打鱼撒网。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船和这些人, 他特别羡慕这些在船上生活的人,他们行走于江湖之上,天地之间,无拘无束, 是多么自在逍遥啊。这比待在官府衙门有意思多了。他梦想着,要是有一天 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那该是多么洒脱。然而他每天一回到官府,就知道这 种事永远只能是梦想,父亲是不可能让自己去做这种事的。不但不能做,连 看的机会也慢慢地少了。由于他对江边的船只越来越入迷,因此出来的次数 就越来越多,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终于被父亲知道了,在被痛骂一顿后, 又恢复了以前的管教,他的自由度又被缩小了。
他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近五年的时间,终因爷爷的去世而结束。那一年 他十九岁。爷爷病故后, 父亲带着家人回乡奔丧。爷爷的丧事办得隆重庄严, 父亲的哭声惊天动地,感动了史镇的人们。史世清没想到古板而又严肃的父亲, 竟然是如此的多情,这和他所认识的父亲是完全不同的。就在这一刻他有些 自责,是自己不好好地读书,以至于让父亲失望而生气。父亲的这种印象只 是那么短的展现在他的面前,没多久又恢复了以往的严厉,从那以后,他再 也没有感到过父亲的亲切。按清朝官吏丁忧制度,史忠方要在家丁忧三年, 这期间他为史世清订下了终身大事,对方便是双阳县另一大家族,吴镇的吴 家千金小姐吴瑞芳。吴家虽然不如史家那么历史久远,但近几十年来,吴家 的势头有超过史家的趋势,吴家家产丰厚,人丁旺盛,在吴镇已经没人能比了。 吴镇又是双阳县乃至整个右江水道的门户之地,四面八方的商贾云集于此, 是双阳县最繁荣的集镇。吴家自然与这些商贾有来有往,吴家的名声也因此 传播得很远。开始, 史家人还有些看不起吴家,因为吴家出的官没有史家的多, 也没有史家出的官品级高。但近些年,吴家出的官是越来越多了。史忠方想还是应该和吴家联姻,也许能从吴家带来些人气来,让史家也能人丁旺盛。 吴家的吴老爷,早就对史镇的史家仰慕已久,两镇虽然相距不远,但来往不 是很亲密,现在史忠方亲自托人前来说媒联姻,哪有不应之理,就这样史世 清与吴瑞玉的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史忠方丁忧期满,便要为史世清和吴瑞玉完婚了,并亲自为他们操办婚 事的。史世清在此之前虽然和吴瑞玉见过几次面,按那时的乡俗,未婚男女 是不能随便说话的,他们的见面都是史世清逢年过节时前去吴家参拜老丈人 之时相见的。吴瑞芳对史世清并不热情,史世清以为这是她害羞或要保持大 户人家小姐派头的原因。其实吴瑞芳对这门婚事是不情愿的,她是吴老爷的 独生女,而且是最小的,吴家又是吴镇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庭,因此她的 成长环境使她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表现出一种很强支配的欲望,伺候她的 丫环稍不如意就要受到责骂。她天资聪慧,学什么东西都特别快。她有过绚 丽的花一样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跟哥哥们一样走出吴镇,走出双阳, 到更远的地方去见更大的世面。她的大哥吴浩淼是她的榜样,因为他还去过 日本留学,回来后总是给她讲外面的新生事情,她听得都入迷了,她要哥哥 带她出去,她要成为一个女中豪杰,哥哥爽快地答应了。然而哥哥吴浩淼参 加了革命党,常常东躲西藏,要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回来一次,因此哥哥没有 实现带她出去的承诺。然而吴老爷怎么都不想让自己唯一的女儿走出去,他 虽然生活在吴镇,见过南来北往的各种各样的人,思想也没有史老太爷那么 正统,但他依然以为女孩子还是应该在家的好,也不能嫁得太远。史忠方派 人来提亲,他很是高兴, 一来,这个双阳县有名的富贵之家终于愿意和吴家 这样的后起大户联姻了,这是对吴家的认可,他知道吴家不论是财富还是家 族人员都超过了史家,但双阳人似乎还是认可史家的地位。而吴瑞芳却十分 的不情愿,她不想留在双阳这个偏僻的地方,可史镇是一个比吴镇更偏僻的 地方。再者, 她听人说史家这个大公子是一个不成器的人,不会有多大出息, 自己的一生和这个人联系在一起,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悲哀的结局。然而父亲 的决定是无法改变的,平时他虽然也很娇惯这个女儿,但在婚姻这样的大事 情上,他必须表现一个大家族族长的威严,吴瑞芳只能恨自己命苦,恨那个 向自己提亲的史忠方。婚事操办完毕,史忠方就得到朝廷的任命绍书,并得 到升迁任职知府。他便要重返湖北就任新职。这一次,他不准备将史世清带在身边,而是把史世清留在家中, 一来史忠方是个独子,无兄无弟,必须让 自己的儿子留下来照顾自己的母亲,另外家里这么大的家业也应让人看守, 二来史忠方很清楚知道这个儿子是没有希望成就功名的,只希望他能经营好 自家的祖业就足矣。
史镇人都夸史世清有福气,娶了一个天仙般的美女。然而史世清却没有 表现出应有的欢乐和幸福,因为从结婚的那天晚上起,他就感受到了吴瑞芳 的冷漠和高傲,这种冷漠和高傲完全不是姑娘小姐们初嫁时的害羞和故作清 高的表现,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内心深处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轻蔑和漠然,其 中似乎夹杂着憎恨和厌恶。对史世清来说,自己娶的最多是一个冷美人。开 始史世清还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等到吴瑞芳熟悉了这个家,也许会改变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冷漠和隔膜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地增长。 夫妻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情感交流,他们的对话总是在一种陌生的,将对方 推开的语境中进行的,史世清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这个妻子为什么会如此,更 不了解她需要什么。她总是说你们史家什么的,我们吴家什么的,似乎她永 远都不想将自己融入这个家庭中来,弄得史世清心灰意冷。他没有想到自己 躲开了父亲的威严,却又要面对这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讥讽和嘲弄。他 陷入了一种更失望郁闷的情绪之中。
然而,吴瑞芳却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寄托, 因为她发现这个史家管理太混 乱了,许多事情都没有了规矩,根本不像外面人传说的那样,史家是一个有 几百来年根基的上等人家。那是她嫁来后的一个月后,她回娘家住了几天, 又回到了这个埋葬她梦想的陌生的家庭,她回来的第一个早晨既然没有人给 她端洗脸水,她按捺住自己的不满,等了好一会,后来她确信不会有人端水 来了,她自己走出了房门,来到了老太太房间,问奶奶史家是否有佣人,史 家的佣人是否给主人端洗脸水,我吴瑞芳是史家的主人吗?当奶奶明白了吴 瑞芳为什么不满后,叹息了一声说,都是清儿惯坏了这些下人们,很多规矩 这些下人们都不讲了,我又老了,很多事管不了。吴瑞芳说不是还有管家吗? 他也不管事吗?他不管事当什么管家。这件事以那位伺候少奶奶的女佣被辞 退而得以平息。从此吴少奶奶便开始过问史家的事了, 她征得老太太的同意, 决定将史家进行一番大的整治。首先,她为家里定下了许多的规矩:家里人 的开支要统一管理,管家不能随意支配,必须经过自己的同意,每笔支出要都记清楚,每月要向她报账。家里人的零用钱要统一按规定支取,任何人不 得超支,有特殊情况要经过老太太的同意。每人每年的衣服添置也要定数量 和钱数,柴米油盐要由专人管理,制定标准,平时用多少,一般节日用多少, 大年大节用多少等要精打细算,不能随意乱用。另外,吃饭时主人和下人要 分开进行,下人吃饭在规定的地方,不能端着碗在院子里到处走。家仆和佣 人的工钱,要重新制定,按干活的多少、轻重来增减, 同时对那些不听主人话, 不服从管家安排,或做事不卖力的要克扣工钱。下人每天早起要向主人请安, 对主人说话要恭敬低首,不能大声大气,到外面不能乱传史家内部的事,家 仆们也不能在背后对主人说三道四,更不能掺和主人家的家事。她还制定了 对史家家仆们的惩罚办法,谁违背了她定下的规矩就要按规定克扣工钱,严重的要进行体罚。自从爷爷死了以后,史世清管理了史家三年,可这三年他 将史家的规矩乱了差不多,史家的家业被弄得乱七八糟,可吴瑞芳用了不到 三个月,史家被整治得有条有理,焕然一新。也正在此时,她要求下人称她 为吴少奶奶,她要显示自己吴家的尊姓,而不是依附于史家的荣耀。老太太 天性仁厚,没有计较这称呼,默许了吴瑞芳的一切行为。史家的上上下下以 及史镇的人都对史家的这个新媳妇投来敬佩和畏惧的目光。吴瑞芳管家的才 能让所有的人都折服了,史世清自然自叹不如,这更加大了他和吴瑞芳的距离。 老太太倒是十分的高兴,她不清楚孙子和孙媳妇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发现了 孙媳妇的泼辣和干练,史家正需要这样的能干媳妇,这是史家的幸事。
五
史世清在家成了多余之人,他没有什么事可管,也说不上什么话,原来 他就厌烦家里那些琐碎之事,现在突然空闲下来,他又有点不适应。因此他 就常常到镇上去,和一些朋友打打牌喝喝酒,吴瑞芳并不怎么管他,由着他去, 因为她看着他在家就有些心烦。但如果他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她就会斥责, 并将他赶到别的房间去睡觉。后来镇上有人组织业余戏班唱戏曲,本来人家 是想要他帮着筹点款,但他不但出了钱还积极参加,成了一名打鼓的先生。 他学得特别努力,接受得也特别快,他对那些曲谱和唱词记得特别牢,几乎 可以脱离戏本,全不像他背那些圣贤经书那么笨拙。很快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打鼓手。打鼓手是整个戏曲乐队的指挥,随着他的鼓起板落,锣声琴声唢 呐声或激昂或低沉地演奏起来,他感到特别的舒畅。此时的他总是微闭着眼睛, 随着乐队的旋律和演员的唱腔晃动着双手和上身,他完全沉浸在其中,感受 着戏曲中的悲欢离合和人物的喜怒哀乐,外部世界的、不愉快的事情全部离 开了他。
就这样,他度过了婚姻的最初几年,和妻子的关系依然是不冷不热,两 人的心灵之间依然存在一条长长的、深深的鸿沟。两人都十分清楚,这条鸿 沟是无法填平的,虽然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史成杰、二儿 子取名为史成仁,都是父亲给取的。现在父亲回家了,而且再也不离开了,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打发日子的方式,又要被打破了。他除了要面对冷漠的妻 子,又要应付威严的父亲。他清楚地知道, 父亲回家后绝不允许自己出去打鼓, 虽然只是业余的,但还是与戏子有关,这种下九流的行为,怎么能是史家这 样的书香门第的人干的事,做这种事有辱史家的声誉。
郁闷的史世清又像小时候一样经常到湖边徘徊,长久地望着茫茫的湖面 排解胸中的郁闷。他对这湖依然有一种说不清的迷恋,鄱阳湖虽然不像小时 候那样神秘,但仍然在诱惑着他。这一天他又无所事事地来到湖边,眺望着 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湖面,突然他被那两只官船吸引住了。这时已是春天了, 湖面的水已经上涨了不少,那两艘搁浅的船已经被上涨的水浮起来了,在那 里摇晃着。由于已有半年多无人过问,那船已经有些陈旧了,全不像刚来时 那样威武漂亮了。他的脑海顿时出现了一个令他自己都激动不已的大胆的想 法,他完全可以将这两只船改造成商船,他可以像他在湖北看到的那些商人 一样,行走于江湖之上,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他就 无法抹去,虽然他知道父亲很难同意他这样做,但他必须试一试,他要尽力 去争取。他马上回到家里,鼓足十分的勇气找到父亲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亲在书房里看书,同时在教两个孙子史成杰和史成仁读书,他在门口 叫了一声:“爹。”
史老太爷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在他的记忆中,这个儿子是从来没有主动 找自己说过话的,今天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向自己说。他等了一会,不冷 不热地问道:“有什么事吗?”
史世清在和父亲的目光对视的那一瞬间,开始犹豫了,父亲的目光像闪电一般直刺向自己的心脏,父亲似乎知道了自己要说什么似的,似乎已经看 穿了自己的一切想法。而且父亲的目光中充满了不信任感,他预感到父亲会 否决自己的任何建议和想法,他就这么愣愣地站在那儿,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父亲等了一会,又冷冷地说: “有什么事快说,我还要教孩子读书呢。没事 就玩你的去,不要影响你的两个儿子。”
史世清涨红着脸,用他平生最大的勇气开始说了,因为他知道他不说就 会失去机会,就永远不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干。他说: “我有一个想法, 想和爹商量一下。”
史忠方将书放下,看了一眼两个孙子,又看了一眼史世清。然后起身对 两个孙子说: “你们在这里好好背书, 我和你们的爹有话说,一会就回来。”
史忠方估计儿子和自己商量的事很重要,但他知道这个儿子不会有什么 好事,因此他必须避开两个孙子,免得让儿子在孙子面前难堪。史忠方在前 面走,来到他会见重要客人的房间,然后叫史世清把房门关上。“你现在可 以说你的事了。”史忠方依然面无表情地说。
史世清清了清嗓子,极力使自己能平静下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开始说: “爹现在回家了,没有了俸禄,我们史家不能坐吃山空。我想自 己也这么大了,从来没为爹分过忧,也没为家里出过力。因此我想为家里做 些事情。正好爹带来的那两只官船在那里闲着,我可以利用它,将他们改造 成商船,到外去跑跑生意,总能为家里补充财物。爹觉得如何?”
史忠方就知道这个不中用的儿子就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史家乃世代官绅 门第,书香世家,怎么着也没沦落到成为商贾之流。商贾之人乃唯利者是也,
怎么能保住史家的仁义之名?但史忠方还是克制了自己,他尽量保持平静地 说:“你可以为史家做许多事情,史家这么一个大的家业还没有你干的事吗?”
史世清说: “家里的事有瑞芳她管着,我哪插得上手。那两只船如果没 有人管,就会烂在水里的。”
“烂在水里你也别想去碰它。它本来就不是我们家的船,你操那么多心 干吗? ”史老太爷提高了声音,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你还好意思说,如果 不是你不务正业,史家会轮到一个女流之辈、一个外来人管家吗?你说得好听, 想为家里争点财富,其实是你的野性未灭,史镇装不下你了,你还想到外面 去疯。我告诉你,只要我没死,史家人就别想经商。我不想让史家的名声和、家业败在你的手中。史家虽然没有我的俸禄,但还有几百亩良田,足够我史 家的子孙们吃穿,你就给我死了这条心吧。”史老太爷说完站起来打开房门, 走出去了。留下史世清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到头了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