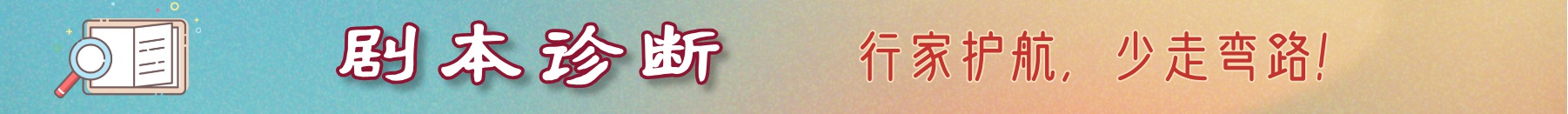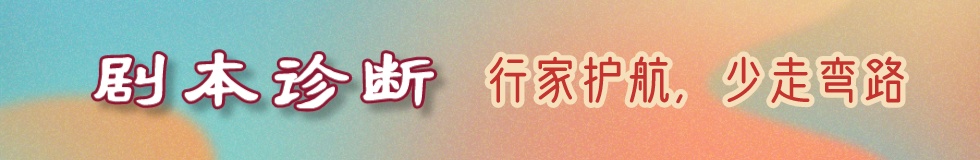权属:原创 · 普通授权
字数:64171
阅读:8577
发表:2016/5/5
20章 主旋律 小说
《几度风月几度情》第1章
1
3
4
2
5
6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她推着单车,他手拎着手皮包,两个并排着慢慢在大街上走。
旁人都睁大眼睛起来,或前或后的都睁着怪眼向他们望过来。
两个走着走着。你、我时不时相互掉转脸过来瞅瞅对方。
他黄立平又车转头问她道:你的眼睛可要真瞎了吧,戴的眼镜都有多少度了?
王玲玲:看你够骨瘦如柴的,狗眼倒还好!本老太可戴上350度的“老花镜”啦。
他可伸手敲了她头一下,说道:你这野丫头还真鬼哩,竟要跟本老爷磨起嘴皮子来了?真不要脸!去!滚了!滚远点!他说过竟伸手推起了她王玲玲。
周围的人一时间都咯咯捧腹大笑起来。但他们俩却显得“若无其事”。
片刻,她便细声小气地说:巍巍,你给调到机械厂里来工作,肯定比在发电厂里工作更紧张了些吧,看你这样子都瘦多了。
他也跟着变了口气说着:也不算怎么紧,不过是近此几天不注意感冒了。
她车转脸过来死死盯着他说:甭哄我了,谁不知道呢!
黄立平:是喽,记者嘛,什么新闻不出在她手上。
她口气又变了:噫!你这小厮---!
黄立平说道:哦!你这野丫头还不比我更烦哩。
他们来到了城边,黄立平很快去跟熟人借了架自行车来,两个并排着骑往家乡的方向去了。
30、在乡场外
片刻,他两个便一同刹住了车到一边去,因为他俩都已来到了公社(开始改为乡)了,两个先把单车推到一个僻静处,找个地方坐下来随便聊聊些无关紧要的话。
王玲玲:巍巍,咱们离开后又有好长一段时间啦,要是去年我见不着你至今,就可足足有一年多时间没见到面了吧。我下去采访那几天呢,偏偏又挤不出多余的时间跟你在一块儿吹吹牛。
黄立平也这样对王玲玲说:也许吧。不过,我也是难抽得时间和你坐一块谈谈哩。哪时候都总有人来找我。
王玲玲这样说:我知道,不过,你一定不晓得哟,去年好像是元月份了吧,我就写信给了你,叫你到我那儿去玩玩儿哩;我记得我在信中还要你在新年春节那几天来我家走走哦。可就是不明白你究竟收得信了没有,你竟然连个信都不回,我真恨死你啦,真恨死你啦。
黄立平故意对她笑着说:那就随你恨个够吧。信倒是收得的,可我就是不想回信给你,我看你有啥办法对付我。
王玲玲假装正经地说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往后就别挨我。
黄立平也假装故意扭头往一边去:我也懒得挨你---。
王玲玲:不客气!你以为自己得了个小官当就瞧不上人啦!其实嘛,谁稀罕你那臭厂,你滚吧!
王玲玲说罢,扭头一边去暗笑起来。从她背上的肉跳就可看得出来。
他这样逗她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现在机械厂不是成了“红太阳”吗?
她“以舌还舌”:谁承认,谁标榜---?
他暗笑着说:是省报!曾有位记者接连写了两、三篇文章进行报道过我厂呀。
王玲玲开始咯咯地笑起来。
他自己也故意抬高了嗓子说:你不知道,我黄某呀,如今已成了别人崇拜的“红太阳”啦。现在有谁敢同敝人——这么一位伟大的光辉形象相比呀!
王玲玲:好个阁下,好个---。请你,我请你去跟娃娃儿吹吧。甭在本老太面前呱呱叫,我烦!滚!
她王玲玲自己竟哈哈大笑起来。
他伸手指着她鼻梁骨说:噫?---还敢称老太!
他两个顿时爽朗大笑起来。
她佯装正经地说:你可别啰嗦啦。老娘肚子可饿了,很想吃饭了哩。
他也故意睁大眼对她说:你敢称老娘?我还不照样要称老爹!
旁人都睁着怪眼在看他们。他们翻手腕看看手表,时间已走到了六点半钟,天色渐晚,哪个的家也隔乡公所有五、六华里的路程哩。
他黄某说:看样子要黑在半道上啦。因为谁都离家有点久了,免不了应该先早点回到家里去,就算再如何好玩也得走,反正只有先回到了家去才随你玩个够了。
王玲玲: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哪里不可以玩?况且,人不吃饭能玩得了吗?所以得先把肚子填饱才是最要紧的。不能再玩啦。两个都抬着头仰望苍穹。
黄立平车转脸过来,问她芳芳:芳儿,你要哪天才回城去呢?
王玲玲挺俏皮地说:巍儿,我想回去了哪天就回去了哪天哩,你管得着吗?我大概是初三,就准要回去了。你呢,憨儿?
他一点都不笑地说:老爹我想过初四再回去哩。
她擂了他背上一拳:滚你的蛋!
他也抬脚上来挡住了她的手:瓜儿,去!去!去------
于是,两个即刻跨上单车各回各的家去啦。
31、在年夜饭桌上
农历腊月二十九。大年夜日子。芳芳家这一天才过晌午便燃放起了一串很响又很长的鞭炮。紧接着便开始吃“年夜饭”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笑逐颜开地吃着吃着,一直吃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王玲玲想:村里如今生活上确实也挺充满阳关啦。
这个时候,王玲玲又想起了自己还小时候,家里的日子真是怎样的艰难;她又想到了自己曾耳闻目睹过的每一桩桩小事,都不禁为之伤心不过。她自己在心里头默默地说了,那时甭说能有哪一年像今天这么开心。就是某年的三十夜那年夜饭还真让人焦愁没米下锅呀。
特别是在她才读到初三那一年——“文革”时的一九六九年,就太悲惨啦。甭说大年三十夜能有几颗米下锅就行,就是在刚刚收割后的“十月谷”日子里也多么担心明、后天就饿了肚子哟。这种担心肚子不会饱的生活偏偏一直持续了整整十年(即到七七年)才渐见好转。也是在这十年后队里才划了田分了地,才让农家自种自收了之后,日子才见一天比一天有所好转起来。只是越到这年头来呀,才真正让农家人尝到了甜头哩。若公家不这样做呀,农民哪有好日子过呀!
王玲玲的内心话:要是在当年也有如此好日子过就好啦。妹妹小青不也照样同我一样都上得了大学来吗?就为“家底”差了才毁了她小青这一生的前途呀。要是家底好点,即使当年她小青考不上一所大学去呀,顶多仅补课不超过一、两年就准能得到一所大学上的,可是------她小青的命运就这样惨。就哪怕她只上得了一所中专去都好呀,而一切却不能如愿以偿呀。这都是环境造成的,是自身条件加环境影响造成的,更是家庭经济拉后腿造成的。加上,还有传统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了她,使得小青一时间没什么奔头,教她小青终究成不了才,做不了什么事啊。
芳芳在家里人面前也说:在她小青高二毕业那一年,已是七七年了,当时她正好十八岁,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毕竟已成历史。从此时起,正是知识分子得以大展宏图的璀璨时代了;当年高中毕业下来的再也不用“上山下乡”支农去啦。党中央已把新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32、在火炉边
一家人吃罢饭,小青收拾碗筷到厨房去后,小青和小红便飞跑出门去看烟花了。
屋里就只剩下两老和芳芳围在火炉边烤火。
芳芳:老的虽然只有他们三个孩子,且如今他们三个谁都七高八大了,谁都长成了一百多斤的年青人啦!哪个孩子都走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这还用说谁还给老的增加负担呢?诚然,老的开始轻松多了,老的早就不再为要到哪天才养大了她们而总在忧虑,在焦愁着。当然老的并非不为后代的成家总在考虑问题啊。
当妈的兰英:自从盘古开天辟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后代们谁都得要有个着落了老的才安下心来。而且,对子女谁都能够成了家之后,其小家庭是不是幸福了,也是老人最值得关心且特别要关心的问题哟。无论是哪家老人,要是他们的后代都未成了去家呀,那可不知道还要焦心到何种地步去哟!而就是早成了家去的儿子、姑娘,若只要有哪一边在生活上不顺利呀,对于当公婆的,包括当外公外婆都恐怕难有一个晚上安下心来睡觉吧。
对于她芳芳家呀,两老实在担心孩子们,要到何时何刻才统统成了家去啊。因为她芳芳都二十八、九岁了,就连二妹小青也有二十三、四,用当妈的话来说:“在我才二十二、三岁时,芳芳都会走路了。”看来两个大姑娘早都走到了成家的年龄去啦。
她老爸王玉文:就连小儿子小红也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哩,谁都不小啦。可谁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对象哩。虽说她芳芳倒是有点“眉目”了,然而毕竟就如同把一小杯酒倒入大杯中,你还得要举起杯子把酒倒进嘴里又吞下肚里去才算得酒喝啊。她的“心愿”也莫不好比暗中取宝物。可以说,她芳芳目前还算未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那父母怎么不焦虑呢?只能为孩子们的“私事”多添白发啊。
芳芳内心想着:何况我又走到了这般年岁呀,要不是说我还能出得了门去找到了份工作做呀,那当爹当妈的不知道要真替我焦心到何种地步去哟。只是说我命运还算好,能有幸上得了一所好大学去读它四年来,并庆幸给分在省城一家报社里工作,要不然呀,老的不会有今天这种高兴哩。我真该感激祖上的功德,太感谢了祖先的保佑,使得王家做终能够享受得到“洪福齐天”。
当爹的王玉文终于说出口:不是这样吗?儿子得到专业学校上,姑娘也得到专业学校上,这还不是祖宗保佑又是什么呢?
当妈的李兰英也笑嘻嘻地说了:是喽!我们家三个孩子就有两个考上了专业学校去,老二小青也仅差一点就上得了大学去哩。
为着孩子们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他们老人已不知道真替孩子们焦虑了多少回去哩。他们老人哪怕是在“现吃现找米下锅”的年月里,无论怎样也要让孩子们多读了书。打从芳芳她能读好书到小青高中毕业了,家里哪一年的口粮都不够吃,可是,老的从不随便让孩子们辍学回家来干了农活误了学习。
(回忆)
当年,王家两老年岁不过四十岁就说了:作为家长,你要是随便让他们中途辍学回家来了,那等过了几年下来,尽管生活上稍微富裕了你再让他们重返学校去读书的话,那保证不到一两年去,他们以往所学到的知识,还不统统都要归还给了老师那才怪哩。
文革时的王家两老,人还显得较年青,她芳芳从初中跨到高中去的那些年头里,其中有一年就连三十夜都只有一升米(五市斤)过年,但两口子也不允许孩子们停学过。那个时候呀,哪家收粮进屋来都少得可怜,自然哪还会有哪几户能有粮食再借给你呀。哪怕是三十夜,他们家都只好煮南瓜来打发日子哟。芳芳她都不知有多少回对自己的老爹老妈说道,就准许她别再读书了,免得两老总负担着她。她要回队里来干农活,要多挣点工分,到秋收来才至于多称得到一些口粮回家来。
王家两老回忆说:正是她读到高一下半年,即在过春节后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很快就要开学了,她芳芳却不愿去报名,是因为家里太贫太困的缘故。
三月五号,她仍赖在家里整天跟老妈东爬坡上山去铲烧草木灰。后来这事让老爹知道了,当爹的竟抄起一根烧火棍追打起她芳芳,她芳芳尽管挨棒子打也仍然不愿上学校去报名读书。可两老又“软硬兼施”,天天吓唬了你不读书那随你到哪死去都行,我们就不准你回家来干农活。这样“折腾”了好几天,最后芳芳才不得不上了学校读书去了。
就在芳芳刚刚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家里却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灾难,正是因为这个大灾难呀,都让她家两老,还有芳芳本人,莫不“凄苦”了大半年。是的,整整有半年时间,两老都瘦了,芳芳更变得像“芦柴棒”似的。
她芳芳在自己的脑子头默默说了(画外音):我这个当大姐的并非只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呀,而是真的有两个弟弟。可为何偏偏现在就只剩一个弟弟了?
在一九七二那一年秋季,她芳芳已领到了学校的高中毕业证书后,就加入了“北上开发”的队伍。不到两个礼拜天光,火车便载着芳芳以及她的同学们越过了山海关,直奔“桃花源世界”那北国边陲去了。
这届高中毕业生就生活、战斗在这块辽阔而渺茫,几乎算千里无人烟的荒凉之地来安营扎寨了。他们走了好几天几夜的路也见不到几个村庄,个个都发出了这真是个不见人烟的“鬼地方”。镜头一闪,积雪厚厚的严冬来到了。
这个严冬,她王玲玲家突遭大难,大弟弟小红才十来岁,而小弟弟仅四岁。可小弟弟到了这严冬却生起了一场大病。区卫生院又关着门。
芳芳回忆说:那年头两老一分钱都没有,无法背上小弟弟上县城大医院去住院治疗。要说跟乡亲们借点钱来急用吧,可是,可怜的乡亲们呀,还更想来跟你借哩。
两老将家里唯一的一只小猫,一只正下蛋的母鸡卖掉了,才勉强得到手近十五块钱,这时才能把她小弟弟背上区卫生院去打打点针,开了几颗没多少用处的药片。
医生说:过几天你家孩子准会好的。
可他们两老一点也想不通,那十五块钱一用完,她的小弟弟便奄奄一息啦。
父母说:你的小弟弟就在这一年,且仅仅七天便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
芳芳回忆说:待到七六年冬,我从北大荒“释放”回家来知道弟弟辞世后,自己此时才那么痛苦不堪。我就只会哭,而辞世的早已辞世了。还能够咋办?
老爸王玉文告诉她:你小弟死的那年,两老在同你通信中没有在信里告诉你,致使你在过了四年多后回家来,还误把邻家的一个小孩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哩。只因后来二妹小青在里屋哭哭啼啼,你芳芳这才慢慢知道你小弟早已成仙去啦。
老妈李兰英:直到今天,你仍为自己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位亲人而深感悲痛,并时不时在偶然间想到了弟弟而感到伤心。但我们都觉得你们三个孩子如今都能像撑天大树一样长高长大了。
老爹也说:今天,老人已没再有什么可感到苦痛的啦,而且还为你们感到高兴,因为家里一个接一个考上了专业学校,让当爹当妈的不管走到了哪去都感到高兴,特别是你芳芳竟能找上了那么好的工作做,这简直是“全科女状元”了。你一个乡下人,农家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地位,就真的不错了。
老妈伸手捻她鼻子说:要是在以前呀,不是坐轿的还甭嫁去成个家哩。
从此后,小的高兴,老的更高心。一家子谁都笑逐颜开,因为在她芳芳还年幼时,两老就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到下一代身上了。但愿孩子长大后,谁都能够为父母亲争口气。这足以说明这一家子同头脑僵硬的那些农家大不一样呀。当她芳芳仅读到初中时,老爹老妈就不管家里有吃没吃,都竭力支持孩子们读书,并教育她和她的弟妹一定要明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芳芳点头。老的不单只关心着她,同样关心着她的二妹小青和兄弟小红。
她芳芳回忆说:我当时看家里实在太困难了,自己有不少回都为着家庭经济拮据而经常性要求老人,就让她干脆回家来干了农活。可是两老咋会答应呢?我为着老的当年在穿着上东吊一条西挂一片,自己都忍不下心来继续读书,直接从心底里感到痛苦到顶了,岂敢坚持上县城念书?可是,两老却无论如何也逼我继续读下去,并叫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随随便便退了学回家来。
稍停片刻,芳芳又说:那时两老都经常性说了我,“要是你退了学来家,不为老的争点气,那就请你滚出家门去吧。我们都随你流浪到哪儿去找饭吃都行。”我无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普通中学去读书,狠下心去苦读了几年。好不容易才熬完了中学,艰难地度过了那段令人多么痛苦而又令人多么伤心的岁月。
老妈也激动地说:可是你真不巧,仅一读完高中刚好毕业,偏偏那个年代又令你失望了。因为你芳芳不能立即上了大学去,不能很快替爸爸妈妈增光添彩。
老爸可摆手说:得知你去了北大荒之后,我们曾对你说,你甭灰心丧气;甭老觉得自己真的没什么前途了,就放弃继续学习呀。我们老的哪怕现去找米下锅过日子,也都为了让你们能上了学去哟!,等到一旦有机会再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吧。爸妈都深信你芳芳一定能考上大学去的。那么,老的将来也好享受 “晚年福”喽。
芳芳:我自己一点儿也不安心地虚度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当年的我确实好不容易地度过了那段最不愿度过的中学时代。因为我想起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上面偏偏不准许我们马上考大学再进新校园去,反而把全届毕业生都“下放”到北大荒“锻炼”去时,我自然而然便想起了辗转反侧,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
那个七二年,知青们从北大荒转移到大草原去又再返回的最后一年,随便四处流浪的同学们一路上凄凄惨惨。但大家同患难、相濡以沫。五个春秋后,变“天”了他们才得以返回家乡来。
芳芳说:只要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我的脑际便即刻飞奔到那片渺茫无垠的田野去了。那时,大家毕竟都走到妙龄青春期了。在这个大好时光里,大家却让忧伤的浓雾给笼罩着。并差不多被摧残完这段美好的时光呀。
芳芳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游踪几乎遍及四方八面。
芳芳:一个南方人都跑到了北方去,这固然是很不习惯。但一个人为了“饭碗”,到处“东奔西突跑”,当然也都是为了闯出一条光明路来呀,可是“光明路”却寻不着,反而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和失望。直到这些年,自己都总觉得几十年来未曾享受过舒心的日子,这都跟当年的长期不幸有关吧!
老爸也颇为感慨地说:这主要是,你呀一度在悲伤、悔恨、失望、烦恼直至痛苦中度过的。你曾因此伤心流泪并大哭过,至于什么是高兴、愉快、欢笑都几乎没有过。这是为什么?这都是历史的逆流,是跳梁小丑们一手造成的。
她老妈李兰英到了今天呢,你芳芳倒是没什么可以多多考虑的了。而就只剩下如何把工作干好,如何寻找自己未来的另一半——即终身相依相伴的心上人。你但愿自己这辈子过得幸福。那么你应该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做你伴侣呢?
李兰英:你曾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你的另一半应该是个啥样的小伙子过来娶你过去做老婆呢?面对现实,你从自己都快三十岁了的这般年纪,便促使你不得不慎重考虑一番了。因为打从元旦节以来,你芳芳就是个二十九实岁,三十虚岁的大姑娘家了。要是说你到如今都弄不到一份好工作,而只守家干农活的乡妹子呀,那人家不是说你都“老”吗?何况我们这儿还是落后农村哩。
老爸王玉文:因为在我们这个贫瘠的边远农村,就像你这般年纪的大姑娘家,本就该是位有两、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当然,多亏你能凭个人本事冲出了大山,冲出了贫穷。永远不再是农业户口了,还包括到你往后的孩子。作为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姑娘家,在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总得要考虑一番好好抉择呀。
老妈李兰英:如何完成得了家庭组建?今天你芳芳不能 “暂且不管”,因为你二妹小青迈到这新年就有二十四虚岁了。而你的兄弟小红也同样加了一岁,变成二十一岁哩。说起来,你们都应该快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才行。特别像你这样的老姑娘,更应该早点找得到自己的终身伴侣,快点把自己推销出去才好。
老人在跟芳芳开“玩笑”。
老爸:“玩笑”是假的,“现实”才是真的哩。只有谁都组建起了自己如意的新家之后才算安下心来哩。
在她读大学那几年,两老为她到处找婆家。她总是摇头摆手两老才罢手。那几年,有不少小伙子上门来求亲。那几年,有在家当农民的,有做生意的,还有在外做小工作的。但她芳芳都统统拒绝了。
芳芳想:哪个小伙子也很难中意哟。有些人嘛本来生得标,长得帅,嘴巴也不是一般的滑,可就总觉得他们同自己的心始终搭不上边儿。只要结了婚后,在小家庭方面肯定不如意。
芳芳说:这辈子若真的没人能够理解得了我的话,那芳芳就这样“算”喽,因为“心不印则意不合”,凡此种情况的男女硬要结合到一块儿来,则往后的日子肯定也会不好过啊。像这样,我芳芳咋又无论如何都必须结了婚去,唯有嫁了人才能够活得下去呢?就来直点吧,没真正了解就结婚的男女如同给判了无期徒刑的罪犯一样!
老妈李兰英:她芳芳向来都不随便谈恋爱,特别是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她都曾说过了,有不少对逛逛马路的恋人中你哄我一句,我骗你一言在消磨时间能有啥意思呢?而且,看你我所讲话的那“派头”且都是“味里味去”的,甚至于在不同程度上话里还带着几分孩子气哩。
老爸王玉文:闺女芳芳曾说,在省城里,确实有几个小妞几个护士真是傲慢的公主,而且,瞧那些话头又还讲究押韵的,则更令她恨透到顶啦。她早说过了:你要想说什么话呀就来个干脆吧,彼此间应甭隐瞒什么话才好哟,既然都来谈恋爱嘛。
刚刚毕业的某某大学生曾坦率地对同学说了:你我既然都算得上“知音”了,那彼此间有什么话还不好商量么?我对某些人专门拟出这样那样的条件感到可恶可憎。唉,真不可想象啦,现实生活竟同我所思所盼的真是两码事呀。难道人世间的生活就原本如此!
但她芳芳摇头了还再摇头。
女性解说员的画外音:在这个大年三十夜,她芳芳才真正感受到了幸福,感受到了家乡人民确实真正迎来了个美好的曙光啦。从村里激烈炮竹声的炸响中,她不无知晓乡民是走上幸福路了。她曾在心里头说过,要是换到那凄惨又悲凉的岁月,甭说天空中处处洒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就连追求一碗白米饭都很困难。
当年情景是:家家户户的厨房里,也听不到炒菜的响声和白米饭散发的香味。而且好几户农家莫不因为无米下锅而默默地哭泣着。
老爸感慨着说:当然,这仅是“动乱年代”的生活罢。现实着的今天,已经没有这种令人感到遗憾的生活了。这时候,何处不见高楼大厦林立?而且富人家中又何不正摆设着多么阔气的家私,甚至书柜上还堆放着一口大闹钟哩,你看看,那梳妆台上早摆放着两口四喇叭收录机作伴舞用的乐器哩。
该村几乎家家都大开音响大闹。
这晚才到七点过二十,村里大闹除夕夜活动便轰轰烈烈地举办了。这个小山村,这个百来户农家的小山村,却如同生活在桃花岛上。村中晒坝上,众青年的表演特别精彩,特别热烈。
芳芳可说了:如今每家每户都开始变得富裕起来了。总的来说,是队里把田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好。在近这两、三年来,上面更放宽了政策,让有力量的人可脱产到外面去跑跑点买卖。等到大忙季节来临时再返回家来赶做农活,人人可在村里搞“双抢双收”了。
很多人家在赶着马车拉山货做生意。
她爹王玉文:现在乡民确实富足了。那些在生活上显得较为如意的人家,几乎没有不通过“双抢双收”而得到富裕呀!
大年夜前,那些首先致富的农家都统统宰了猪杀了羊过年,并且多数都是两百来斤猪肉哩。包括他们王家在内,都是大猪。
她老妈李兰英:乡民为了在生活上能日比一日幸福,大家都爱做小生意。就是烤酒卖的都有好几家,有极个别卖酒户简直成了小酒厂啦。
年年快到三十夜时,无论远村还是近寨,都常有人过来或挑或背白酒回去过年。卖酒的农家门庭若市。
旁人都睁大眼睛起来,或前或后的都睁着怪眼向他们望过来。
两个走着走着。你、我时不时相互掉转脸过来瞅瞅对方。
他黄立平又车转头问她道:你的眼睛可要真瞎了吧,戴的眼镜都有多少度了?
王玲玲:看你够骨瘦如柴的,狗眼倒还好!本老太可戴上350度的“老花镜”啦。
他可伸手敲了她头一下,说道:你这野丫头还真鬼哩,竟要跟本老爷磨起嘴皮子来了?真不要脸!去!滚了!滚远点!他说过竟伸手推起了她王玲玲。
周围的人一时间都咯咯捧腹大笑起来。但他们俩却显得“若无其事”。
片刻,她便细声小气地说:巍巍,你给调到机械厂里来工作,肯定比在发电厂里工作更紧张了些吧,看你这样子都瘦多了。
他也跟着变了口气说着:也不算怎么紧,不过是近此几天不注意感冒了。
她车转脸过来死死盯着他说:甭哄我了,谁不知道呢!
黄立平:是喽,记者嘛,什么新闻不出在她手上。
她口气又变了:噫!你这小厮---!
黄立平说道:哦!你这野丫头还不比我更烦哩。
他们来到了城边,黄立平很快去跟熟人借了架自行车来,两个并排着骑往家乡的方向去了。
30、在乡场外
片刻,他两个便一同刹住了车到一边去,因为他俩都已来到了公社(开始改为乡)了,两个先把单车推到一个僻静处,找个地方坐下来随便聊聊些无关紧要的话。
王玲玲:巍巍,咱们离开后又有好长一段时间啦,要是去年我见不着你至今,就可足足有一年多时间没见到面了吧。我下去采访那几天呢,偏偏又挤不出多余的时间跟你在一块儿吹吹牛。
黄立平也这样对王玲玲说:也许吧。不过,我也是难抽得时间和你坐一块谈谈哩。哪时候都总有人来找我。
王玲玲这样说:我知道,不过,你一定不晓得哟,去年好像是元月份了吧,我就写信给了你,叫你到我那儿去玩玩儿哩;我记得我在信中还要你在新年春节那几天来我家走走哦。可就是不明白你究竟收得信了没有,你竟然连个信都不回,我真恨死你啦,真恨死你啦。
黄立平故意对她笑着说:那就随你恨个够吧。信倒是收得的,可我就是不想回信给你,我看你有啥办法对付我。
王玲玲假装正经地说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往后就别挨我。
黄立平也假装故意扭头往一边去:我也懒得挨你---。
王玲玲:不客气!你以为自己得了个小官当就瞧不上人啦!其实嘛,谁稀罕你那臭厂,你滚吧!
王玲玲说罢,扭头一边去暗笑起来。从她背上的肉跳就可看得出来。
他这样逗她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现在机械厂不是成了“红太阳”吗?
她“以舌还舌”:谁承认,谁标榜---?
他暗笑着说:是省报!曾有位记者接连写了两、三篇文章进行报道过我厂呀。
王玲玲开始咯咯地笑起来。
他自己也故意抬高了嗓子说:你不知道,我黄某呀,如今已成了别人崇拜的“红太阳”啦。现在有谁敢同敝人——这么一位伟大的光辉形象相比呀!
王玲玲:好个阁下,好个---。请你,我请你去跟娃娃儿吹吧。甭在本老太面前呱呱叫,我烦!滚!
她王玲玲自己竟哈哈大笑起来。
他伸手指着她鼻梁骨说:噫?---还敢称老太!
他两个顿时爽朗大笑起来。
她佯装正经地说:你可别啰嗦啦。老娘肚子可饿了,很想吃饭了哩。
他也故意睁大眼对她说:你敢称老娘?我还不照样要称老爹!
旁人都睁着怪眼在看他们。他们翻手腕看看手表,时间已走到了六点半钟,天色渐晚,哪个的家也隔乡公所有五、六华里的路程哩。
他黄某说:看样子要黑在半道上啦。因为谁都离家有点久了,免不了应该先早点回到家里去,就算再如何好玩也得走,反正只有先回到了家去才随你玩个够了。
王玲玲: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哪里不可以玩?况且,人不吃饭能玩得了吗?所以得先把肚子填饱才是最要紧的。不能再玩啦。两个都抬着头仰望苍穹。
黄立平车转脸过来,问她芳芳:芳儿,你要哪天才回城去呢?
王玲玲挺俏皮地说:巍儿,我想回去了哪天就回去了哪天哩,你管得着吗?我大概是初三,就准要回去了。你呢,憨儿?
他一点都不笑地说:老爹我想过初四再回去哩。
她擂了他背上一拳:滚你的蛋!
他也抬脚上来挡住了她的手:瓜儿,去!去!去------
于是,两个即刻跨上单车各回各的家去啦。
31、在年夜饭桌上
农历腊月二十九。大年夜日子。芳芳家这一天才过晌午便燃放起了一串很响又很长的鞭炮。紧接着便开始吃“年夜饭”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笑逐颜开地吃着吃着,一直吃到了晚上九点多钟。
王玲玲想:村里如今生活上确实也挺充满阳关啦。
这个时候,王玲玲又想起了自己还小时候,家里的日子真是怎样的艰难;她又想到了自己曾耳闻目睹过的每一桩桩小事,都不禁为之伤心不过。她自己在心里头默默地说了,那时甭说能有哪一年像今天这么开心。就是某年的三十夜那年夜饭还真让人焦愁没米下锅呀。
特别是在她才读到初三那一年——“文革”时的一九六九年,就太悲惨啦。甭说大年三十夜能有几颗米下锅就行,就是在刚刚收割后的“十月谷”日子里也多么担心明、后天就饿了肚子哟。这种担心肚子不会饱的生活偏偏一直持续了整整十年(即到七七年)才渐见好转。也是在这十年后队里才划了田分了地,才让农家自种自收了之后,日子才见一天比一天有所好转起来。只是越到这年头来呀,才真正让农家人尝到了甜头哩。若公家不这样做呀,农民哪有好日子过呀!
王玲玲的内心话:要是在当年也有如此好日子过就好啦。妹妹小青不也照样同我一样都上得了大学来吗?就为“家底”差了才毁了她小青这一生的前途呀。要是家底好点,即使当年她小青考不上一所大学去呀,顶多仅补课不超过一、两年就准能得到一所大学上的,可是------她小青的命运就这样惨。就哪怕她只上得了一所中专去都好呀,而一切却不能如愿以偿呀。这都是环境造成的,是自身条件加环境影响造成的,更是家庭经济拉后腿造成的。加上,还有传统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了她,使得小青一时间没什么奔头,教她小青终究成不了才,做不了什么事啊。
芳芳在家里人面前也说:在她小青高二毕业那一年,已是七七年了,当时她正好十八岁,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毕竟已成历史。从此时起,正是知识分子得以大展宏图的璀璨时代了;当年高中毕业下来的再也不用“上山下乡”支农去啦。党中央已把新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32、在火炉边
一家人吃罢饭,小青收拾碗筷到厨房去后,小青和小红便飞跑出门去看烟花了。
屋里就只剩下两老和芳芳围在火炉边烤火。
芳芳:老的虽然只有他们三个孩子,且如今他们三个谁都七高八大了,谁都长成了一百多斤的年青人啦!哪个孩子都走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这还用说谁还给老的增加负担呢?诚然,老的开始轻松多了,老的早就不再为要到哪天才养大了她们而总在忧虑,在焦愁着。当然老的并非不为后代的成家总在考虑问题啊。
当妈的兰英:自从盘古开天辟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后代们谁都得要有个着落了老的才安下心来。而且,对子女谁都能够成了家之后,其小家庭是不是幸福了,也是老人最值得关心且特别要关心的问题哟。无论是哪家老人,要是他们的后代都未成了去家呀,那可不知道还要焦心到何种地步去哟!而就是早成了家去的儿子、姑娘,若只要有哪一边在生活上不顺利呀,对于当公婆的,包括当外公外婆都恐怕难有一个晚上安下心来睡觉吧。
对于她芳芳家呀,两老实在担心孩子们,要到何时何刻才统统成了家去啊。因为她芳芳都二十八、九岁了,就连二妹小青也有二十三、四,用当妈的话来说:“在我才二十二、三岁时,芳芳都会走路了。”看来两个大姑娘早都走到了成家的年龄去啦。
她老爸王玉文:就连小儿子小红也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哩,谁都不小啦。可谁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对象哩。虽说她芳芳倒是有点“眉目”了,然而毕竟就如同把一小杯酒倒入大杯中,你还得要举起杯子把酒倒进嘴里又吞下肚里去才算得酒喝啊。她的“心愿”也莫不好比暗中取宝物。可以说,她芳芳目前还算未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那父母怎么不焦虑呢?只能为孩子们的“私事”多添白发啊。
芳芳内心想着:何况我又走到了这般年岁呀,要不是说我还能出得了门去找到了份工作做呀,那当爹当妈的不知道要真替我焦心到何种地步去哟。只是说我命运还算好,能有幸上得了一所好大学去读它四年来,并庆幸给分在省城一家报社里工作,要不然呀,老的不会有今天这种高兴哩。我真该感激祖上的功德,太感谢了祖先的保佑,使得王家做终能够享受得到“洪福齐天”。
当爹的王玉文终于说出口:不是这样吗?儿子得到专业学校上,姑娘也得到专业学校上,这还不是祖宗保佑又是什么呢?
当妈的李兰英也笑嘻嘻地说了:是喽!我们家三个孩子就有两个考上了专业学校去,老二小青也仅差一点就上得了大学去哩。
为着孩子们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他们老人已不知道真替孩子们焦虑了多少回去哩。他们老人哪怕是在“现吃现找米下锅”的年月里,无论怎样也要让孩子们多读了书。打从芳芳她能读好书到小青高中毕业了,家里哪一年的口粮都不够吃,可是,老的从不随便让孩子们辍学回家来干了农活误了学习。
(回忆)
当年,王家两老年岁不过四十岁就说了:作为家长,你要是随便让他们中途辍学回家来了,那等过了几年下来,尽管生活上稍微富裕了你再让他们重返学校去读书的话,那保证不到一两年去,他们以往所学到的知识,还不统统都要归还给了老师那才怪哩。
文革时的王家两老,人还显得较年青,她芳芳从初中跨到高中去的那些年头里,其中有一年就连三十夜都只有一升米(五市斤)过年,但两口子也不允许孩子们停学过。那个时候呀,哪家收粮进屋来都少得可怜,自然哪还会有哪几户能有粮食再借给你呀。哪怕是三十夜,他们家都只好煮南瓜来打发日子哟。芳芳她都不知有多少回对自己的老爹老妈说道,就准许她别再读书了,免得两老总负担着她。她要回队里来干农活,要多挣点工分,到秋收来才至于多称得到一些口粮回家来。
王家两老回忆说:正是她读到高一下半年,即在过春节后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很快就要开学了,她芳芳却不愿去报名,是因为家里太贫太困的缘故。
三月五号,她仍赖在家里整天跟老妈东爬坡上山去铲烧草木灰。后来这事让老爹知道了,当爹的竟抄起一根烧火棍追打起她芳芳,她芳芳尽管挨棒子打也仍然不愿上学校去报名读书。可两老又“软硬兼施”,天天吓唬了你不读书那随你到哪死去都行,我们就不准你回家来干农活。这样“折腾”了好几天,最后芳芳才不得不上了学校读书去了。
就在芳芳刚刚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家里却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灾难,正是因为这个大灾难呀,都让她家两老,还有芳芳本人,莫不“凄苦”了大半年。是的,整整有半年时间,两老都瘦了,芳芳更变得像“芦柴棒”似的。
她芳芳在自己的脑子头默默说了(画外音):我这个当大姐的并非只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呀,而是真的有两个弟弟。可为何偏偏现在就只剩一个弟弟了?
在一九七二那一年秋季,她芳芳已领到了学校的高中毕业证书后,就加入了“北上开发”的队伍。不到两个礼拜天光,火车便载着芳芳以及她的同学们越过了山海关,直奔“桃花源世界”那北国边陲去了。
这届高中毕业生就生活、战斗在这块辽阔而渺茫,几乎算千里无人烟的荒凉之地来安营扎寨了。他们走了好几天几夜的路也见不到几个村庄,个个都发出了这真是个不见人烟的“鬼地方”。镜头一闪,积雪厚厚的严冬来到了。
这个严冬,她王玲玲家突遭大难,大弟弟小红才十来岁,而小弟弟仅四岁。可小弟弟到了这严冬却生起了一场大病。区卫生院又关着门。
芳芳回忆说:那年头两老一分钱都没有,无法背上小弟弟上县城大医院去住院治疗。要说跟乡亲们借点钱来急用吧,可是,可怜的乡亲们呀,还更想来跟你借哩。
两老将家里唯一的一只小猫,一只正下蛋的母鸡卖掉了,才勉强得到手近十五块钱,这时才能把她小弟弟背上区卫生院去打打点针,开了几颗没多少用处的药片。
医生说:过几天你家孩子准会好的。
可他们两老一点也想不通,那十五块钱一用完,她的小弟弟便奄奄一息啦。
父母说:你的小弟弟就在这一年,且仅仅七天便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
芳芳回忆说:待到七六年冬,我从北大荒“释放”回家来知道弟弟辞世后,自己此时才那么痛苦不堪。我就只会哭,而辞世的早已辞世了。还能够咋办?
老爸王玉文告诉她:你小弟死的那年,两老在同你通信中没有在信里告诉你,致使你在过了四年多后回家来,还误把邻家的一个小孩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哩。只因后来二妹小青在里屋哭哭啼啼,你芳芳这才慢慢知道你小弟早已成仙去啦。
老妈李兰英:直到今天,你仍为自己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位亲人而深感悲痛,并时不时在偶然间想到了弟弟而感到伤心。但我们都觉得你们三个孩子如今都能像撑天大树一样长高长大了。
老爹也说:今天,老人已没再有什么可感到苦痛的啦,而且还为你们感到高兴,因为家里一个接一个考上了专业学校,让当爹当妈的不管走到了哪去都感到高兴,特别是你芳芳竟能找上了那么好的工作做,这简直是“全科女状元”了。你一个乡下人,农家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地位,就真的不错了。
老妈伸手捻她鼻子说:要是在以前呀,不是坐轿的还甭嫁去成个家哩。
从此后,小的高兴,老的更高心。一家子谁都笑逐颜开,因为在她芳芳还年幼时,两老就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到下一代身上了。但愿孩子长大后,谁都能够为父母亲争口气。这足以说明这一家子同头脑僵硬的那些农家大不一样呀。当她芳芳仅读到初中时,老爹老妈就不管家里有吃没吃,都竭力支持孩子们读书,并教育她和她的弟妹一定要明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芳芳点头。老的不单只关心着她,同样关心着她的二妹小青和兄弟小红。
她芳芳回忆说:我当时看家里实在太困难了,自己有不少回都为着家庭经济拮据而经常性要求老人,就让她干脆回家来干了农活。可是两老咋会答应呢?我为着老的当年在穿着上东吊一条西挂一片,自己都忍不下心来继续读书,直接从心底里感到痛苦到顶了,岂敢坚持上县城念书?可是,两老却无论如何也逼我继续读下去,并叫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随随便便退了学回家来。
稍停片刻,芳芳又说:那时两老都经常性说了我,“要是你退了学来家,不为老的争点气,那就请你滚出家门去吧。我们都随你流浪到哪儿去找饭吃都行。”我无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普通中学去读书,狠下心去苦读了几年。好不容易才熬完了中学,艰难地度过了那段令人多么痛苦而又令人多么伤心的岁月。
老妈也激动地说:可是你真不巧,仅一读完高中刚好毕业,偏偏那个年代又令你失望了。因为你芳芳不能立即上了大学去,不能很快替爸爸妈妈增光添彩。
老爸可摆手说:得知你去了北大荒之后,我们曾对你说,你甭灰心丧气;甭老觉得自己真的没什么前途了,就放弃继续学习呀。我们老的哪怕现去找米下锅过日子,也都为了让你们能上了学去哟!,等到一旦有机会再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吧。爸妈都深信你芳芳一定能考上大学去的。那么,老的将来也好享受 “晚年福”喽。
芳芳:我自己一点儿也不安心地虚度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当年的我确实好不容易地度过了那段最不愿度过的中学时代。因为我想起中学毕业的那一年,上面偏偏不准许我们马上考大学再进新校园去,反而把全届毕业生都“下放”到北大荒“锻炼”去时,我自然而然便想起了辗转反侧,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
那个七二年,知青们从北大荒转移到大草原去又再返回的最后一年,随便四处流浪的同学们一路上凄凄惨惨。但大家同患难、相濡以沫。五个春秋后,变“天”了他们才得以返回家乡来。
芳芳说:只要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我的脑际便即刻飞奔到那片渺茫无垠的田野去了。那时,大家毕竟都走到妙龄青春期了。在这个大好时光里,大家却让忧伤的浓雾给笼罩着。并差不多被摧残完这段美好的时光呀。
芳芳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游踪几乎遍及四方八面。
芳芳:一个南方人都跑到了北方去,这固然是很不习惯。但一个人为了“饭碗”,到处“东奔西突跑”,当然也都是为了闯出一条光明路来呀,可是“光明路”却寻不着,反而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和失望。直到这些年,自己都总觉得几十年来未曾享受过舒心的日子,这都跟当年的长期不幸有关吧!
老爸也颇为感慨地说:这主要是,你呀一度在悲伤、悔恨、失望、烦恼直至痛苦中度过的。你曾因此伤心流泪并大哭过,至于什么是高兴、愉快、欢笑都几乎没有过。这是为什么?这都是历史的逆流,是跳梁小丑们一手造成的。
她老妈李兰英到了今天呢,你芳芳倒是没什么可以多多考虑的了。而就只剩下如何把工作干好,如何寻找自己未来的另一半——即终身相依相伴的心上人。你但愿自己这辈子过得幸福。那么你应该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做你伴侣呢?
李兰英:你曾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你的另一半应该是个啥样的小伙子过来娶你过去做老婆呢?面对现实,你从自己都快三十岁了的这般年纪,便促使你不得不慎重考虑一番了。因为打从元旦节以来,你芳芳就是个二十九实岁,三十虚岁的大姑娘家了。要是说你到如今都弄不到一份好工作,而只守家干农活的乡妹子呀,那人家不是说你都“老”吗?何况我们这儿还是落后农村哩。
老爸王玉文:因为在我们这个贫瘠的边远农村,就像你这般年纪的大姑娘家,本就该是位有两、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当然,多亏你能凭个人本事冲出了大山,冲出了贫穷。永远不再是农业户口了,还包括到你往后的孩子。作为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姑娘家,在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总得要考虑一番好好抉择呀。
老妈李兰英:如何完成得了家庭组建?今天你芳芳不能 “暂且不管”,因为你二妹小青迈到这新年就有二十四虚岁了。而你的兄弟小红也同样加了一岁,变成二十一岁哩。说起来,你们都应该快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才行。特别像你这样的老姑娘,更应该早点找得到自己的终身伴侣,快点把自己推销出去才好。
老人在跟芳芳开“玩笑”。
老爸:“玩笑”是假的,“现实”才是真的哩。只有谁都组建起了自己如意的新家之后才算安下心来哩。
在她读大学那几年,两老为她到处找婆家。她总是摇头摆手两老才罢手。那几年,有不少小伙子上门来求亲。那几年,有在家当农民的,有做生意的,还有在外做小工作的。但她芳芳都统统拒绝了。
芳芳想:哪个小伙子也很难中意哟。有些人嘛本来生得标,长得帅,嘴巴也不是一般的滑,可就总觉得他们同自己的心始终搭不上边儿。只要结了婚后,在小家庭方面肯定不如意。
芳芳说:这辈子若真的没人能够理解得了我的话,那芳芳就这样“算”喽,因为“心不印则意不合”,凡此种情况的男女硬要结合到一块儿来,则往后的日子肯定也会不好过啊。像这样,我芳芳咋又无论如何都必须结了婚去,唯有嫁了人才能够活得下去呢?就来直点吧,没真正了解就结婚的男女如同给判了无期徒刑的罪犯一样!
老妈李兰英:她芳芳向来都不随便谈恋爱,特别是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她都曾说过了,有不少对逛逛马路的恋人中你哄我一句,我骗你一言在消磨时间能有啥意思呢?而且,看你我所讲话的那“派头”且都是“味里味去”的,甚至于在不同程度上话里还带着几分孩子气哩。
老爸王玉文:闺女芳芳曾说,在省城里,确实有几个小妞几个护士真是傲慢的公主,而且,瞧那些话头又还讲究押韵的,则更令她恨透到顶啦。她早说过了:你要想说什么话呀就来个干脆吧,彼此间应甭隐瞒什么话才好哟,既然都来谈恋爱嘛。
刚刚毕业的某某大学生曾坦率地对同学说了:你我既然都算得上“知音”了,那彼此间有什么话还不好商量么?我对某些人专门拟出这样那样的条件感到可恶可憎。唉,真不可想象啦,现实生活竟同我所思所盼的真是两码事呀。难道人世间的生活就原本如此!
但她芳芳摇头了还再摇头。
女性解说员的画外音:在这个大年三十夜,她芳芳才真正感受到了幸福,感受到了家乡人民确实真正迎来了个美好的曙光啦。从村里激烈炮竹声的炸响中,她不无知晓乡民是走上幸福路了。她曾在心里头说过,要是换到那凄惨又悲凉的岁月,甭说天空中处处洒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就连追求一碗白米饭都很困难。
当年情景是:家家户户的厨房里,也听不到炒菜的响声和白米饭散发的香味。而且好几户农家莫不因为无米下锅而默默地哭泣着。
老爸感慨着说:当然,这仅是“动乱年代”的生活罢。现实着的今天,已经没有这种令人感到遗憾的生活了。这时候,何处不见高楼大厦林立?而且富人家中又何不正摆设着多么阔气的家私,甚至书柜上还堆放着一口大闹钟哩,你看看,那梳妆台上早摆放着两口四喇叭收录机作伴舞用的乐器哩。
该村几乎家家都大开音响大闹。
这晚才到七点过二十,村里大闹除夕夜活动便轰轰烈烈地举办了。这个小山村,这个百来户农家的小山村,却如同生活在桃花岛上。村中晒坝上,众青年的表演特别精彩,特别热烈。
芳芳可说了:如今每家每户都开始变得富裕起来了。总的来说,是队里把田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好。在近这两、三年来,上面更放宽了政策,让有力量的人可脱产到外面去跑跑点买卖。等到大忙季节来临时再返回家来赶做农活,人人可在村里搞“双抢双收”了。
很多人家在赶着马车拉山货做生意。
她爹王玉文:现在乡民确实富足了。那些在生活上显得较为如意的人家,几乎没有不通过“双抢双收”而得到富裕呀!
大年夜前,那些首先致富的农家都统统宰了猪杀了羊过年,并且多数都是两百来斤猪肉哩。包括他们王家在内,都是大猪。
她老妈李兰英:乡民为了在生活上能日比一日幸福,大家都爱做小生意。就是烤酒卖的都有好几家,有极个别卖酒户简直成了小酒厂啦。
年年快到三十夜时,无论远村还是近寨,都常有人过来或挑或背白酒回去过年。卖酒的农家门庭若市。
到头了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