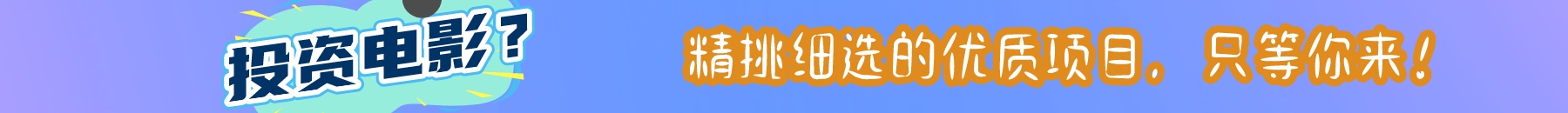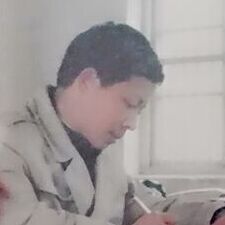爱情
小说
师娘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7、撑死胆大的
这一年的高考结束,文科班的学生考后都说自我感觉良好。于頫还是不放心,就让各科老师与考生共同估计了一下分数,确实感觉不错,自己很是高兴。但准确考分没有半个月时间是不会下来的,这段时间于老师就像猫挠心样难受,但也只能耐着性子等待。
这时,所有学校都放暑假了,幼儿园也放了。于頫才想起女儿丹丹下学期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就想到别的教师子女上一年级时,家长就已为他们提前将课本上的知识教会了,他却没有。这一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二是因为他不愿这样做。他觉得凡是学校要教的知识,家长就不必提前教,教了就是重复劳动,增加了孩子的课业负担;但课外知识还是要辅导孩子多学习的。以往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太少了,真是有愧于子女,他要利用这假期好好辅导丹丹背背《千家诗》一类的古典启蒙读物。他想,教育不管如何改革,优秀的传统读物还是要死记硬背的,只有背下来的东西,才算是自己的东西;胸无点墨的人,要想出口成章、下笔千言,那是很难做到的!他反对僵化的死记硬背,但他更反对一味反对死记硬背的教育观!他反对那些一味盲从的“愉快教育”,更担忧那些一直得到“愉快教育”真传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是不是真的还能愉快?
于頫老师做事很讲究时效性,连这暑假对女儿的辅导也不例外。上午九点,他在堂前挪一把骨牌凳做“课桌”,让丹丹端来小竹椅坐在“课桌”前,“课桌”上放着翻开的《千家诗》,随着他一字一顿地领读,乖巧的丹丹伸着稚嫩的小手指逐字逐字地指点着书上的诗句,跟随爸爸奶声奶气地念着……
上午十点,本是小店生意最旺盛的时间,但罚税以后,却冷淡得门开罗雀,加上学校放假,店里就更清闲。这时候,沈幽兰就放心地在厨房做午餐,或者在室外走廊搓衣服。每到这时,于頫已不再要女儿背古诗,也不让女儿看小人书,只让她去休息,让她去找小伙伴们玩。“别同小朋友打架,别忘了按时回家吃午饭,噢?”他抚摸着女儿的小脑袋,这样叮嘱之后,就又走向妻子所在的地方。
妻子来街上以后,家务事他是从来不料理的,只是当每餐捧起饭碗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时,见妻子还在忙里忙外,他心中才涌起那么一点愧疚,但他很快又被教学、班级管理那些没完没了的事情要做而一次次原谅了自己,为自己作了开脱;但这是暑假,除了为女儿尽些作父亲的责任外,他不能不为妻子尽些做丈夫的义务。妻子曾对他说过:“你不会做,我不怨你,但我忙的时候,哪怕你能站一旁看着,也是对我的尊重,对我的支持,我也是高兴的。”他知道这是妻子的内心话,也说得他很感动。现在是假期,见她在忙着,就也凑过去,象征性地做些帮忙的活儿。
这次妻子正在灶台上忙着做饭菜。于頫自知这不是他帮得了的活儿,就自觉地坐到灶口,忍着暑天灶口那炎炎烈火的炙烤,做着给灶堂添柴加火的活儿;为了不把事情做错,不把饭菜烧焦,他一边为灶堂加柴,一边不断地征求妻子的意见:“大火吗?”“小火吗?”“要不要再加柴?……”
沈幽兰要是在灶前炒青菜,就说:“炒菜要大火,不然青菜会发黄的。给外锅堂里加几根硬柴。”
于頫就在灶口柴堆上抽几支劈开的栗柴塞进外锅堂,外锅堂里立即发出呼呼的响声。他望着那旺盛的火苗,显得很悠闲,很惬意,就用火钳在灶口青砖上有一下无一下地轻轻敲着,发出单调而清脆地“嘎、嘎”声。
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过,灶门是灶公爷的嘴巴,那是敲不得的,敲了灶公爷就会发怒,就会在腊月二十三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告你的状!沈幽兰当然不信这些,也不制止丈夫去敲;但从这敲灶门的声音中,她听出了丈夫这些天的心情一定是很好——她模透了丈夫的脾气,只有在这轻松悠闲的时候,同他商谈家务事,他才会听得耐心,听得细心,才能谈得深谈得透,时不时还能想出一些令她不得不佩服的见解!
“唉!”她始终用这样的称呼同丈夫说话,“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可细想了?”
于頫就停住在灶口敲火钳的动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还是那无息贷款的事?”
沈幽兰正在翻炒青菜,见丈夫问,就说:“是的。石主任又来催问过几次了!”
于頫又用火钳在灶门上敲了两下,说:“这事啊,我反复考虑过,像我们这个家庭要开个大商店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沈幽兰翻炒青菜的手腕立即酸软下来。
“你想,造—个一流的商店,单新盖个店面没有一二十万元能行吗?单造店面不行呀,还得有充足的商品吧,商品不充足,顾客到你这个店里来了,要买的东西都没有,谁还相信你这是一流的商店呢?要想商品充足,没有个十万八万资金作运转行吗?这前后加起来,就得二三十万啦,你敢贷这么多款吗?”
沈幽兰说:“石主任主动找我贷的,我有什么不敢?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叫‘要想发,到银行拿;要想赖,到银行贷’!像秦兆阳那些企业就担心到银行贷不着,只要有一点空子,他们都会不惜一切钻进去,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只要贷到手,就是胜利。这年头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哟哟哟,快快快,灶堂里的柴退掉,退掉!哟哟,菜炒煳了……”
灶上灶下就慌乱成一团。
当一碗乌焦的青菜放在灶台时,沈幽兰又借机发起脾气,冲着蹲在灶口已被柴烟呛得连眼镜都垂挂到鼻尖上的丈夫说:“你真是郭大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就走到灶下,拉开于頫,说,“你还是去教你的书吧,这里是指望不了你!”就重新为灶堂点燃起彻底捣灭的柴火。
木然呆立在灶台一角的于頫知道妻子发脾气的真正原因,就一边看着她弓腰伸颈冲灶堂吹火的姿式,一边耐心地劝慰道:“这碗煳菜中午就给我吃吧。现在你把柴火架好我负责帮你看住,免得火大火小我把握不准。”见妻子还在向灶堂里吹火,就又说:“不是我的胆小,我们是不能跟那些企业厂长们比的,他们在位时百万千万地贷国家的款,一方面美其言是发展乡镇企业,另一方面个人也好从中大捞油水;到时候见势头不对,就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亏损的是国家,撇油的是自己;我们却不同,我们是个体,而且我又是个国家教师,你没听说有个说法,叫‘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变化太快,我们贷了款,到时候政策一变,要我们归还,我们是没法跑掉的,因为我还有国家的工资在他们手里押着。”灶堂里的火重新生着了,于頫重新规规矩矩坐在灶口的小凳上,见妻子又开始在灶台上忙碌起来,知道她的火气已小下来,就继续说,“到时候,乡镇企业贷款还不起是没事的,我们不还却不行,信用社是可以拿我的工资作抵押。到那时,我们又无后台,你想想看吧,那时的困难就比现在更大了!嗯,你说对不?”
沈幽兰虽说性情倔犟,但她毕竟是通情达理,觉得丈夫说得也是道理,何况已有罚税款的例子在先。“刚开店时,左所长不也是信誓旦旦地保证每月只收一块钱的税吗,后来还不是突然来个查税,又是补交又是罚款的。这上面的政策真是叫老百姓吃不透呢!”锅里氽的豌豆鸡蛋汤沸腾了,她看着那一粒粒在混沌的蛋汤中浮上浮下的豆粒,心想:“再说,这扶持‘万元户’是他们当干部的事,说不定就是在拿我们小老百姓当‘炮灰’使用,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平民老百姓哩!”
但她又是个很要脸面的人。她不能就凭丈夫的解释和自己的一番思考,就完全放弃那批无息贷款,何况店里正缺着资金复活呢。她终于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对灶下的丈夫说:“我看是不是这样,无息贷款还是要的,但不要贷那么多,更不要造什么一流的商店,就贷一部分款,把现有的厨房移到外面去,把整个披厦改成店堂,把门面也换成像‘知青店’样,我看这就贷不了多少款。你说呢?”
坐在灶口的于頫又用火钳轻轻地敲着灶门,沉思了一下,说:“这也是个办法。晚上我来测算一下,看需要多少资金,写个报告递上去。”
这就是机遇。报告递上去的当天,信用社石中旭主任就亲自领着一班人到实地考察了一番。虽说沈幽兰夫妻俩的设想并没能达到他们要建一流商场的要求,但真的按照沈幽兰的设想改建起来,这爿小店还是很有看相的。他们只对报告提了一条意见,那就是五万元贷款太少,至少要贷十万元,要不然改造后的商店就一定没有一个“万元户”的气势!石主任最后说:“这是何镇长的意见,不然,就取消这项贷款。”
沈幽兰同于頫一商量,想到了一处:“反正已闹得满城风雨了,叫贷十万就贷十万吧!好歹肉是烂在自家锅里。”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办事速度,修改后的报告递上去的第二天,十万元无息贷款就到了沈幽兰的帐上!
这一年的高考结束,文科班的学生考后都说自我感觉良好。于頫还是不放心,就让各科老师与考生共同估计了一下分数,确实感觉不错,自己很是高兴。但准确考分没有半个月时间是不会下来的,这段时间于老师就像猫挠心样难受,但也只能耐着性子等待。
这时,所有学校都放暑假了,幼儿园也放了。于頫才想起女儿丹丹下学期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就想到别的教师子女上一年级时,家长就已为他们提前将课本上的知识教会了,他却没有。这一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二是因为他不愿这样做。他觉得凡是学校要教的知识,家长就不必提前教,教了就是重复劳动,增加了孩子的课业负担;但课外知识还是要辅导孩子多学习的。以往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太少了,真是有愧于子女,他要利用这假期好好辅导丹丹背背《千家诗》一类的古典启蒙读物。他想,教育不管如何改革,优秀的传统读物还是要死记硬背的,只有背下来的东西,才算是自己的东西;胸无点墨的人,要想出口成章、下笔千言,那是很难做到的!他反对僵化的死记硬背,但他更反对一味反对死记硬背的教育观!他反对那些一味盲从的“愉快教育”,更担忧那些一直得到“愉快教育”真传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是不是真的还能愉快?
于頫老师做事很讲究时效性,连这暑假对女儿的辅导也不例外。上午九点,他在堂前挪一把骨牌凳做“课桌”,让丹丹端来小竹椅坐在“课桌”前,“课桌”上放着翻开的《千家诗》,随着他一字一顿地领读,乖巧的丹丹伸着稚嫩的小手指逐字逐字地指点着书上的诗句,跟随爸爸奶声奶气地念着……
上午十点,本是小店生意最旺盛的时间,但罚税以后,却冷淡得门开罗雀,加上学校放假,店里就更清闲。这时候,沈幽兰就放心地在厨房做午餐,或者在室外走廊搓衣服。每到这时,于頫已不再要女儿背古诗,也不让女儿看小人书,只让她去休息,让她去找小伙伴们玩。“别同小朋友打架,别忘了按时回家吃午饭,噢?”他抚摸着女儿的小脑袋,这样叮嘱之后,就又走向妻子所在的地方。
妻子来街上以后,家务事他是从来不料理的,只是当每餐捧起饭碗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时,见妻子还在忙里忙外,他心中才涌起那么一点愧疚,但他很快又被教学、班级管理那些没完没了的事情要做而一次次原谅了自己,为自己作了开脱;但这是暑假,除了为女儿尽些作父亲的责任外,他不能不为妻子尽些做丈夫的义务。妻子曾对他说过:“你不会做,我不怨你,但我忙的时候,哪怕你能站一旁看着,也是对我的尊重,对我的支持,我也是高兴的。”他知道这是妻子的内心话,也说得他很感动。现在是假期,见她在忙着,就也凑过去,象征性地做些帮忙的活儿。
这次妻子正在灶台上忙着做饭菜。于頫自知这不是他帮得了的活儿,就自觉地坐到灶口,忍着暑天灶口那炎炎烈火的炙烤,做着给灶堂添柴加火的活儿;为了不把事情做错,不把饭菜烧焦,他一边为灶堂加柴,一边不断地征求妻子的意见:“大火吗?”“小火吗?”“要不要再加柴?……”
沈幽兰要是在灶前炒青菜,就说:“炒菜要大火,不然青菜会发黄的。给外锅堂里加几根硬柴。”
于頫就在灶口柴堆上抽几支劈开的栗柴塞进外锅堂,外锅堂里立即发出呼呼的响声。他望着那旺盛的火苗,显得很悠闲,很惬意,就用火钳在灶口青砖上有一下无一下地轻轻敲着,发出单调而清脆地“嘎、嘎”声。
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过,灶门是灶公爷的嘴巴,那是敲不得的,敲了灶公爷就会发怒,就会在腊月二十三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告你的状!沈幽兰当然不信这些,也不制止丈夫去敲;但从这敲灶门的声音中,她听出了丈夫这些天的心情一定是很好——她模透了丈夫的脾气,只有在这轻松悠闲的时候,同他商谈家务事,他才会听得耐心,听得细心,才能谈得深谈得透,时不时还能想出一些令她不得不佩服的见解!
“唉!”她始终用这样的称呼同丈夫说话,“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可细想了?”
于頫就停住在灶口敲火钳的动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还是那无息贷款的事?”
沈幽兰正在翻炒青菜,见丈夫问,就说:“是的。石主任又来催问过几次了!”
于頫又用火钳在灶门上敲了两下,说:“这事啊,我反复考虑过,像我们这个家庭要开个大商店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沈幽兰翻炒青菜的手腕立即酸软下来。
“你想,造—个一流的商店,单新盖个店面没有一二十万元能行吗?单造店面不行呀,还得有充足的商品吧,商品不充足,顾客到你这个店里来了,要买的东西都没有,谁还相信你这是一流的商店呢?要想商品充足,没有个十万八万资金作运转行吗?这前后加起来,就得二三十万啦,你敢贷这么多款吗?”
沈幽兰说:“石主任主动找我贷的,我有什么不敢?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叫‘要想发,到银行拿;要想赖,到银行贷’!像秦兆阳那些企业就担心到银行贷不着,只要有一点空子,他们都会不惜一切钻进去,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只要贷到手,就是胜利。这年头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哟哟哟,快快快,灶堂里的柴退掉,退掉!哟哟,菜炒煳了……”
灶上灶下就慌乱成一团。
当一碗乌焦的青菜放在灶台时,沈幽兰又借机发起脾气,冲着蹲在灶口已被柴烟呛得连眼镜都垂挂到鼻尖上的丈夫说:“你真是郭大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就走到灶下,拉开于頫,说,“你还是去教你的书吧,这里是指望不了你!”就重新为灶堂点燃起彻底捣灭的柴火。
木然呆立在灶台一角的于頫知道妻子发脾气的真正原因,就一边看着她弓腰伸颈冲灶堂吹火的姿式,一边耐心地劝慰道:“这碗煳菜中午就给我吃吧。现在你把柴火架好我负责帮你看住,免得火大火小我把握不准。”见妻子还在向灶堂里吹火,就又说:“不是我的胆小,我们是不能跟那些企业厂长们比的,他们在位时百万千万地贷国家的款,一方面美其言是发展乡镇企业,另一方面个人也好从中大捞油水;到时候见势头不对,就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亏损的是国家,撇油的是自己;我们却不同,我们是个体,而且我又是个国家教师,你没听说有个说法,叫‘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变化太快,我们贷了款,到时候政策一变,要我们归还,我们是没法跑掉的,因为我还有国家的工资在他们手里押着。”灶堂里的火重新生着了,于頫重新规规矩矩坐在灶口的小凳上,见妻子又开始在灶台上忙碌起来,知道她的火气已小下来,就继续说,“到时候,乡镇企业贷款还不起是没事的,我们不还却不行,信用社是可以拿我的工资作抵押。到那时,我们又无后台,你想想看吧,那时的困难就比现在更大了!嗯,你说对不?”
沈幽兰虽说性情倔犟,但她毕竟是通情达理,觉得丈夫说得也是道理,何况已有罚税款的例子在先。“刚开店时,左所长不也是信誓旦旦地保证每月只收一块钱的税吗,后来还不是突然来个查税,又是补交又是罚款的。这上面的政策真是叫老百姓吃不透呢!”锅里氽的豌豆鸡蛋汤沸腾了,她看着那一粒粒在混沌的蛋汤中浮上浮下的豆粒,心想:“再说,这扶持‘万元户’是他们当干部的事,说不定就是在拿我们小老百姓当‘炮灰’使用,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平民老百姓哩!”
但她又是个很要脸面的人。她不能就凭丈夫的解释和自己的一番思考,就完全放弃那批无息贷款,何况店里正缺着资金复活呢。她终于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对灶下的丈夫说:“我看是不是这样,无息贷款还是要的,但不要贷那么多,更不要造什么一流的商店,就贷一部分款,把现有的厨房移到外面去,把整个披厦改成店堂,把门面也换成像‘知青店’样,我看这就贷不了多少款。你说呢?”
坐在灶口的于頫又用火钳轻轻地敲着灶门,沉思了一下,说:“这也是个办法。晚上我来测算一下,看需要多少资金,写个报告递上去。”
这就是机遇。报告递上去的当天,信用社石中旭主任就亲自领着一班人到实地考察了一番。虽说沈幽兰夫妻俩的设想并没能达到他们要建一流商场的要求,但真的按照沈幽兰的设想改建起来,这爿小店还是很有看相的。他们只对报告提了一条意见,那就是五万元贷款太少,至少要贷十万元,要不然改造后的商店就一定没有一个“万元户”的气势!石主任最后说:“这是何镇长的意见,不然,就取消这项贷款。”
沈幽兰同于頫一商量,想到了一处:“反正已闹得满城风雨了,叫贷十万就贷十万吧!好歹肉是烂在自家锅里。”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办事速度,修改后的报告递上去的第二天,十万元无息贷款就到了沈幽兰的帐上!
上一章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