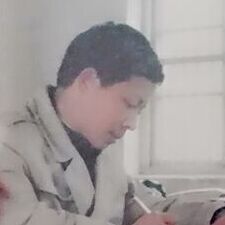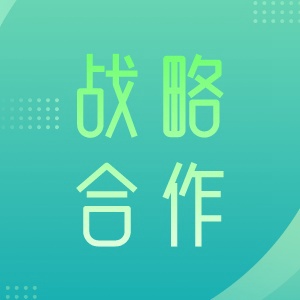爱情
小说
师娘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4、戴鸭舌帽的旁观者
堂哥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印证。
那天,于頫在家里满满请了一桌,供销社、税务所的主任所长都来了,就是工商所长不到。
这事前都是做了周密安排的。沈幽兰夫妻俩在社会上没有门路,就负责在家里搞酒搞菜搞招待;请人邀客的事,一律交给堂哥于殿去办。
堂哥于殿不仅在供销社工作时间长,同工商、税务这些部门打交道多,人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为人热情,且酒量大喝酒又爽快,“津巴布韦”是常事。堂哥属牛,别人见面不称呼他名和姓,都喊他“牛哥”,凡牛哥邀人喝酒,几乎是没人不到场的。“牛哥喊喝酒,要是不去,那不是‘狗子坐轿子——不识抬举’?”自从那天接受了弟妹交给邀客的任务,他马不停蹄给那些该邀请的一一打过招呼之后,就又是叮嘱店里的职工又是亲自出马,瞅着工商所长什么时候在孤峰街上出现。终有一天早上,堂哥正在旧货店门口清点废酒瓶,就见那个精瘦的工商所长推着自行车在街心小菜摊前张望,他就急忙停下手中活计,远远招手喊道:“所长,所长,过来!过来!”
工商所长似乎听到有人叫他,但一时又没听出叫喊的方向,就两手紧按自行车把,朝满街张望个遍,最后发现是收购站这边,就推车过来,说:“老牛,什么事?”脸上不冷不热,丝毫不见热情。
“哪天到我老三家喝酒去?”
“喝酒?喝什么酒?”
“喝酒就是喝酒,还问喝什么酒干吗?”
所长蹙一下鼻子,“吭”了一声,说:“现在的酒,没有一个是好喝的!”
堂哥知道这人的犟脾气,没法,只得如实把他弟媳想申请开店的事说了,最后再次邀请:“怎么样?我老三夫妻俩说了,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去坐坐,认识认识。”
所长就微微咧了一下嘴,缩一下细长的脖颈,说:“好,到时候再说吧。”就推着自行车走了。
可等到约定的时间,该请的人都到了场,唯独不见工商所长的身影。打电话到他单位,单位说他到县里开会去了;打电话到县里,县里说这天根本就没开会。大家就知道他不会来了,都一齐说:“开酒。等我们吃过喝过,多留些骨头,让他下回来一个人慢慢啃!”
供销社洪主任就笑着说:“这真叫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来了!”
于殿连忙说:“洪主任,话怎么能这样说呢?要不是我弟妹有事麻烦你们,平时请也请不到你们呢!坐,坐,坐,都坐。”
在一旁上菜的沈幽兰也忙说:“要不是我二哥和你们的关系好,凭我和于老师巴掌大的脸面,怎么能请得动你们呢!二哥,今天就辛苦你了,一定要把这些领导的酒陪好!”
那顿酒是猜拳行令耍酒疯,足足喝了三个多小时,谁也没提到开店的事。
工商所长不点头,营业执照拿不到手,其它一切努力都是空的。酒散之后,沈幽兰又同于頫商量起工商所长没请到的事。
“这年头变坏了,有权人现在讲究的已不是吃喝,而看重的是送礼!我看事情已到了这一步,干脆再花两个,送两个‘子’过去!”中学毕竟不是世外桃园,于頫对世风在变的事早有耳闻。那天晚上,他对幽兰说。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这杨所长是红鼻子还是绿眼睛,我们都没见过,你没听二哥说,他这人的头很难剃,他对你不了解,突然送钱给他,他要是坏你的事,把这事捅出去,我们开店的事就算彻底完了!”
于頫觉得幽兰这话有理,就问:“那你说怎么办?事情走到这个地步,难道就就此停了?”
沈幽兰说:“急有什么用?二哥不是说了,猴子不上树,多打一棰锣;由他去慢慢找杨所长。我不信那个杨所长的心是铁打的,就说不动他。”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沈幽兰开店的事仍然没有一点头绪。她曾几次气馁,想偷偷回到乡下去,去种乡下那分得的三亩“责任田”,去和婆婆一块儿生活;但她又不甘心,觉得既是上面政策允许了,事情办不成,这责任不应该是别人,而完全是自己努力不够,时机没把握好,工作没做到位!她知道丈夫性急,缺少耐心,怕他中途泄气,每见他着急的时候,她都劝解着他。
沈幽兰终于做了个要在孤峰街上长期住下去的打算。一天,她在街上买来了煤机灶,在走廊前支起了小锅小灶。于頫下课回来看见,问:“你这是干什么?”
沈幽兰说:“我算过帐,一天三餐在食堂吃饭吃菜,你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三张嘴把吃掉了!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哪能这样过口子?不如我们在家自烧自吃,那要节省得多。好歹我也闲着没事。”丈夫见她说得在理,只得点头答应。
沈幽兰成了每天必须上街买菜的主妇。
孤峰街是个“露水街”,集贸的时间很短,就是早上那么一阵子,严格地说,真正称得上“露水街”的,也只是从石拱桥南到供销社那不足百米的一节筒子街上。等早饭后,太阳升起,露水干了,孤峰街上的人就散尽了。孤峰铺虽说是个古老的集镇,但时至今日,真正住在街上吃商品粮的人并不多,就是那么五六百号人。因为人口少,所以就没有固定的蔬菜队种蔬菜专供街道上人们每天生活的需要。这些居民每天蔬菜的供给,完全是靠街边附近的农户。农户家有的是因某种菜在这个季节生长得特别旺盛,一时吃不完,腌多了又觉得是浪费,就由老人、女人,或是小孩拎着小篮小筐大清早提一些到街上来卖,卖了就到供销社买点配给的盐、肥皂之类的东西带回去;有的是属于能吃得了,但手头正缺钱用,舍不得吃,就将那些生长得最好的无虫无疤水灵灵油汪汪的蔬菜拎到街上来卖,将卖出的钱用到急需要用的地方去;有的是家庭要办大事,比方讲媳妇,盖房屋,天冷天热要添件新衣服,把那上市的好菜从牙缝里省出来,比方那头几茬的韭菜,新上市的青豆米,清早起来把割好、剥好,天见亮就拎到街上来,卖出的钱积攒住,留作办大事……因此,孤峰这条“露水街”上,周而复始的只能是:春季的菜苔、蒜苗、菠菜梗;夏季的豆角、辣椒、紫苋菜;秋季的南瓜、扁豆、洋茄子;冬天里的萝卜青菜……偶尔也有些水鲜和山货来卖,但那都是从山溪石缝里扒来的石鱼、石蛙、八胡子、麻骨愣;从山上拔的竹笋、掐的蕨根苔和趁雷雨后拣来的地衣……
幸好那时的荤菜,如猪肉鸡蛋之类,统统集中在食品站配给,免去了沈幽兰在街上买菜时的许多尴尬。沈幽兰是个省俭惯了的人,那时在乡下,每顿上桌的菜,除了自己种的青菜萝卜之外,最奢侈的就是蒸一个鸡蛋。她要把这碗连汤带水的鸡蛋舀给年老的婆婆吃,舀给年小的女儿吃。婆婆说:“兰子,你也舀着吃唦。光给我们吃有什么用?这个家里里外外靠的都是你呀,你也要惜护身体呀!”沈幽兰嘴上应着,但最后,一碗蒸蛋还全是给一老一小吃了。现在到街上来了,丈夫每月就拿三四十几块钱的工资,她能买好菜吃吗?她能舍得买好菜吃吗?
她很羡慕那些“双职工”人家的买菜。那些人从不买下脚菜,专捡新上市的菜买。要是有了鱼呀虾的,他们手一划,就连鱼虾带竹篮一起捞过去称了,然后再讨价还价……
堂哥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印证。
那天,于頫在家里满满请了一桌,供销社、税务所的主任所长都来了,就是工商所长不到。
这事前都是做了周密安排的。沈幽兰夫妻俩在社会上没有门路,就负责在家里搞酒搞菜搞招待;请人邀客的事,一律交给堂哥于殿去办。
堂哥于殿不仅在供销社工作时间长,同工商、税务这些部门打交道多,人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为人热情,且酒量大喝酒又爽快,“津巴布韦”是常事。堂哥属牛,别人见面不称呼他名和姓,都喊他“牛哥”,凡牛哥邀人喝酒,几乎是没人不到场的。“牛哥喊喝酒,要是不去,那不是‘狗子坐轿子——不识抬举’?”自从那天接受了弟妹交给邀客的任务,他马不停蹄给那些该邀请的一一打过招呼之后,就又是叮嘱店里的职工又是亲自出马,瞅着工商所长什么时候在孤峰街上出现。终有一天早上,堂哥正在旧货店门口清点废酒瓶,就见那个精瘦的工商所长推着自行车在街心小菜摊前张望,他就急忙停下手中活计,远远招手喊道:“所长,所长,过来!过来!”
工商所长似乎听到有人叫他,但一时又没听出叫喊的方向,就两手紧按自行车把,朝满街张望个遍,最后发现是收购站这边,就推车过来,说:“老牛,什么事?”脸上不冷不热,丝毫不见热情。
“哪天到我老三家喝酒去?”
“喝酒?喝什么酒?”
“喝酒就是喝酒,还问喝什么酒干吗?”
所长蹙一下鼻子,“吭”了一声,说:“现在的酒,没有一个是好喝的!”
堂哥知道这人的犟脾气,没法,只得如实把他弟媳想申请开店的事说了,最后再次邀请:“怎么样?我老三夫妻俩说了,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去坐坐,认识认识。”
所长就微微咧了一下嘴,缩一下细长的脖颈,说:“好,到时候再说吧。”就推着自行车走了。
可等到约定的时间,该请的人都到了场,唯独不见工商所长的身影。打电话到他单位,单位说他到县里开会去了;打电话到县里,县里说这天根本就没开会。大家就知道他不会来了,都一齐说:“开酒。等我们吃过喝过,多留些骨头,让他下回来一个人慢慢啃!”
供销社洪主任就笑着说:“这真叫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来了!”
于殿连忙说:“洪主任,话怎么能这样说呢?要不是我弟妹有事麻烦你们,平时请也请不到你们呢!坐,坐,坐,都坐。”
在一旁上菜的沈幽兰也忙说:“要不是我二哥和你们的关系好,凭我和于老师巴掌大的脸面,怎么能请得动你们呢!二哥,今天就辛苦你了,一定要把这些领导的酒陪好!”
那顿酒是猜拳行令耍酒疯,足足喝了三个多小时,谁也没提到开店的事。
工商所长不点头,营业执照拿不到手,其它一切努力都是空的。酒散之后,沈幽兰又同于頫商量起工商所长没请到的事。
“这年头变坏了,有权人现在讲究的已不是吃喝,而看重的是送礼!我看事情已到了这一步,干脆再花两个,送两个‘子’过去!”中学毕竟不是世外桃园,于頫对世风在变的事早有耳闻。那天晚上,他对幽兰说。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这杨所长是红鼻子还是绿眼睛,我们都没见过,你没听二哥说,他这人的头很难剃,他对你不了解,突然送钱给他,他要是坏你的事,把这事捅出去,我们开店的事就算彻底完了!”
于頫觉得幽兰这话有理,就问:“那你说怎么办?事情走到这个地步,难道就就此停了?”
沈幽兰说:“急有什么用?二哥不是说了,猴子不上树,多打一棰锣;由他去慢慢找杨所长。我不信那个杨所长的心是铁打的,就说不动他。”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沈幽兰开店的事仍然没有一点头绪。她曾几次气馁,想偷偷回到乡下去,去种乡下那分得的三亩“责任田”,去和婆婆一块儿生活;但她又不甘心,觉得既是上面政策允许了,事情办不成,这责任不应该是别人,而完全是自己努力不够,时机没把握好,工作没做到位!她知道丈夫性急,缺少耐心,怕他中途泄气,每见他着急的时候,她都劝解着他。
沈幽兰终于做了个要在孤峰街上长期住下去的打算。一天,她在街上买来了煤机灶,在走廊前支起了小锅小灶。于頫下课回来看见,问:“你这是干什么?”
沈幽兰说:“我算过帐,一天三餐在食堂吃饭吃菜,你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三张嘴把吃掉了!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哪能这样过口子?不如我们在家自烧自吃,那要节省得多。好歹我也闲着没事。”丈夫见她说得在理,只得点头答应。
沈幽兰成了每天必须上街买菜的主妇。
孤峰街是个“露水街”,集贸的时间很短,就是早上那么一阵子,严格地说,真正称得上“露水街”的,也只是从石拱桥南到供销社那不足百米的一节筒子街上。等早饭后,太阳升起,露水干了,孤峰街上的人就散尽了。孤峰铺虽说是个古老的集镇,但时至今日,真正住在街上吃商品粮的人并不多,就是那么五六百号人。因为人口少,所以就没有固定的蔬菜队种蔬菜专供街道上人们每天生活的需要。这些居民每天蔬菜的供给,完全是靠街边附近的农户。农户家有的是因某种菜在这个季节生长得特别旺盛,一时吃不完,腌多了又觉得是浪费,就由老人、女人,或是小孩拎着小篮小筐大清早提一些到街上来卖,卖了就到供销社买点配给的盐、肥皂之类的东西带回去;有的是属于能吃得了,但手头正缺钱用,舍不得吃,就将那些生长得最好的无虫无疤水灵灵油汪汪的蔬菜拎到街上来卖,将卖出的钱用到急需要用的地方去;有的是家庭要办大事,比方讲媳妇,盖房屋,天冷天热要添件新衣服,把那上市的好菜从牙缝里省出来,比方那头几茬的韭菜,新上市的青豆米,清早起来把割好、剥好,天见亮就拎到街上来,卖出的钱积攒住,留作办大事……因此,孤峰这条“露水街”上,周而复始的只能是:春季的菜苔、蒜苗、菠菜梗;夏季的豆角、辣椒、紫苋菜;秋季的南瓜、扁豆、洋茄子;冬天里的萝卜青菜……偶尔也有些水鲜和山货来卖,但那都是从山溪石缝里扒来的石鱼、石蛙、八胡子、麻骨愣;从山上拔的竹笋、掐的蕨根苔和趁雷雨后拣来的地衣……
幸好那时的荤菜,如猪肉鸡蛋之类,统统集中在食品站配给,免去了沈幽兰在街上买菜时的许多尴尬。沈幽兰是个省俭惯了的人,那时在乡下,每顿上桌的菜,除了自己种的青菜萝卜之外,最奢侈的就是蒸一个鸡蛋。她要把这碗连汤带水的鸡蛋舀给年老的婆婆吃,舀给年小的女儿吃。婆婆说:“兰子,你也舀着吃唦。光给我们吃有什么用?这个家里里外外靠的都是你呀,你也要惜护身体呀!”沈幽兰嘴上应着,但最后,一碗蒸蛋还全是给一老一小吃了。现在到街上来了,丈夫每月就拿三四十几块钱的工资,她能买好菜吃吗?她能舍得买好菜吃吗?
她很羡慕那些“双职工”人家的买菜。那些人从不买下脚菜,专捡新上市的菜买。要是有了鱼呀虾的,他们手一划,就连鱼虾带竹篮一起捞过去称了,然后再讨价还价……
上一章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