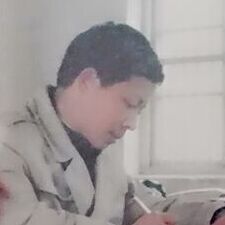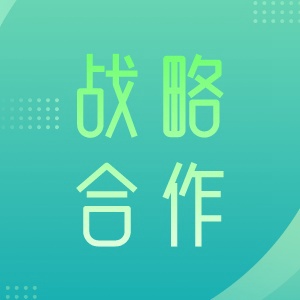爱情
小说
师娘
-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邵树人书记听说沈幽兰新婚之夜父母双双离世,大为震惊,当天就与峰亭大队书记宋群安通了电话,约定登门去看望他的学生也是他这次在孤坑生产队搞“小段包工”试点的主要招集人沈幽兰!
毫不讳言,邵树人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能从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学老师而突然升迁为一个既要管理着全社政治经济文化又要管着二万多人吃喝拉撒大事的公社党委第一把手,这不能不让很多的人感到吃惊和怀疑。其实说穿了,道理也是极其简单,那就是机遇。
“文革”初期,邵树人在峰亭小学被红卫兵轰下讲台后不久,全公社的教师就集中到孤峰中心小学,先是参加政治学习,后来就在内部搞“斗批改”,再就是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到处揪斗“当权派”,到处“破四旧,立四新”……邵树人以他那魁伟的身材沉稳的气质和写得一手漂亮钢笔字的金字招牌,当然地很快就被举荐进司令部的决策机构,于是就在此后的一次次对公社那些“走资派”、“当权派”的谈判、审讯、批斗中,让他那沉稳的性格、深邃的思想和那说话的语速虽然是不紧不慢不卑不亢但却有着极其敏锐的思辩力、慑服力等众多方面的素质就不仅是得到充分展示,而且简直就是展示得淋漓尽致,使他人不得不折服和敬佩!于是,在此后无论是同“当权派”的谈判还是在批斗“走资派”的发言揭批中,只要是他在发言,不仅是所有在场的听众,就连当时那些“当权派”、“走资派”也无一不被他那提问或是揭发时严密的语法逻辑和条分缕析的推论而惊讶钦佩得刮目相看五体投地,就不得不惊呼:啊,原来孤峰公社这教师队伍中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竟有如此的人才!而这其中一个人就不仅是钦佩,更是眼前一亮,就觉得自己是继哥伦布之后又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这个人就是当时孤峰公社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的党委第一书记童仲。在后来的“革命大联合”中,童仲书记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和理由竭力举荐邵树人进了孤峰公社革命委员会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
尽管后来有很多人对“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的邵树人能坐上公社革委会第一把椅子的位置有很大质疑,但已是县委书记的童仲在全县万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看一个干部不能看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入党,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干,而重点要看这个干部一贯是怎样做,做的是不是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不是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为邵树人减了压,拍了板,定了调,为他在孤峰公社登上一把手的位子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作为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只要能做到把“抓革命促生产”多卖爱国粮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作为历史使命去很好地完成,就一定能在县里市里甚至可以在更高层次的大小会议上受到表扬或是领上一张红彤彤的大奖状或者是锦旗!当然,身为党委书记的邵树人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每当他看着别的一把手在那隆重的场面满面春风的接受领导的褒奖而他却只能是坐在台下为他们鼓掌时,他又何尝不是带有分羡慕几分嫉妒!然而,或许是因为他的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或许是由于我们老祖宗那几千年遗传下来的“民以食为天,官以民为本”的古训过多地渗进了他这位教师出身的灵魂深处而造就了他想改也难以改掉的秉性, 加之他整年行走在孤峰这块厚实的土地上,日日时时所看到和所想到的上面那种隆重的授奖场面和农村这懒散劳动场合的极具讽刺性的对比,作为一个统管着二万多人吃穿住行的领导者,孰轻孰重,孰是孰非,他不得不沉思,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断!
他多么向往土地改革、合作社,甚至包括人民公社初期那些岁月。那时真是家家爱集体,心齐力量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是何等的高涨!然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很快就派生出一个“吃大锅饭”的怪胎,社员“上工像背纤,下工像射箭”,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就更是让人变得尖滑、散慢、懒堕,社员出工不出力,窝工、混工现象日趋严重……
那是他的学生沈幽兰亲自告诉他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春三月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到了,家家户户又开始饿肚子了。那些日子,在家做饭的老人,每到傍晚时分,就早早拿着饭箩、脸盆、簸箕来到队屋稻场,焦急等候领回大麦穗回家炒熟做饭。可那些正在田间刁割刚黄半爪的大麦穗的社员却不急不躁,一如既往地在消极怠工,男社员车水马龙般找田坎屙屎撒尿,女人除了跑茅厕,就是同男社员说说笑笑打情骂俏……此时的他们,并不是忘记了家家户户的老人正饥肠漉漉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手中的新麦回去下锅做饭,他们是要把这天上工的时间一分一秒慢慢地给消磨尽消磨完!
那天,邵树人听完幽兰讲的这个真实故事,就仰看长天,半晌无语!
沈幽兰看到如此情形,知道老师是在为人心的涣散在痛苦,在思考;她本不敢打搅她的老师,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句:“邵书记,现在的社员都是出工不出力,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为吃饭问题犯愁啊?”那时,她已完全不敢想象着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近神话般的日子了。
邵树人似乎对这事早有思考,见学生提问,就立即回答道:“根本问题还是个劳动制度问题!
那时的沈幽兰当然不懂得这些大道理,就问:“老师,什么是劳动制度?”
邵树人就把马克思所说的“农民投入的前提就是农民的积极性,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核心就是保障农民的利益”这套几近绕口令似的高深论理不仅是连说了两遍,而且还作了详细的解释,而后才极其痛心地说:“而我们现在的劳动制度呢?不是设法去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而是鞭打快牛,干多干少一个样,社员在这样制度的驱使下,不偷懒不消极怠工那才是怪事呢!”
也就在那次,邵树人书记把他长久的思考和从小道上得来的消息综合成自己一个非常的想法而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告诉了他这位可信的学生。
“老师,这个任务能交给我吗?”
当见学生睁着那双好看的杏仁眼站在自己面前焦急地等待回答时,邵树人那个突出的喉节上下滑动了两下,还是忍住没说。
这不是他不信任这位学生,而是这种任务的落实是要担当极大风险的!
“老师,这是让我家乡的人不饿肚子的大好事,我敢干!”沈幽兰似乎明白老师迟迟不回答的原因,就再次补充了一句。
如果邵树人当时哪怕还有一丝丝别的办法,他也决不会把这个要承担极大风险的任务交给他的这位学生;但他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好办法。
“我听丁书记说过,上次你在处理陶坑那个采茶事件中,就已显示出很好的工作智慧;这个任务你当然能完成。”邵树人在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后,又提醒道:“但这次和那次是有很大不同处,这次试点可能要担当更大的政治风险!”
“老师,我不怕,我会有办法的!”见邵书记已同意把任务交给她这位刚工作不久的学生,沈幽兰高兴极了,就如童年读书时在老师面前做了个撒娇的调皮动作。
很快,邵树人在同峰亭大队书记宋群安做了一番思想工作统一了口径,将沈幽兰从方坑片调回孤坑生产队,专职负责“小段包工”的试点工作。
这试点工作原是准备在开春后启动的,不曾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沈幽兰的双亲去世了!
“小沈还有这份心思来做这项工作吗?”邵树人在去看望沈幽兰的路上还一直是极其焦虑地思考着。但当他和宋群安来到于家见到沈幽兰通过一段简单的安慰和交谈之后,他在同情之余就更是敬佩她这位学生!
“邵书记,”沈幽兰在公众场合是从来不称邵树人为老师的,“宋书记,我八婶说得对,父母在我刚出嫁就双双走了,这是两位老人在爱护我,在支持我的工作。试点的事就按原来的计划办,队里的社员会我已经开过了,开展的具体措施我已同队长商量过了!”
当两位书记一再问到在“小段包工”试点中会有哪些困难时,沈幽兰首先想到了两个人,这一个是整天不忘给自己那“两片瓦”长发抹水的刘可太,一个就是柳英;但因为柳英已是她的二嫂了,家丑不可外扬,她只说了刘可太。“没事,那毕竟是少数人,一人不拗众,我们会做好他工作的!”说过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
其实,搞试点工作的最大难度远不止刘可太和柳英这两个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沈幽兰当然一时还不知道,那就是金霞金老师。
毫不讳言,邵树人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能从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学老师而突然升迁为一个既要管理着全社政治经济文化又要管着二万多人吃喝拉撒大事的公社党委第一把手,这不能不让很多的人感到吃惊和怀疑。其实说穿了,道理也是极其简单,那就是机遇。
“文革”初期,邵树人在峰亭小学被红卫兵轰下讲台后不久,全公社的教师就集中到孤峰中心小学,先是参加政治学习,后来就在内部搞“斗批改”,再就是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到处揪斗“当权派”,到处“破四旧,立四新”……邵树人以他那魁伟的身材沉稳的气质和写得一手漂亮钢笔字的金字招牌,当然地很快就被举荐进司令部的决策机构,于是就在此后的一次次对公社那些“走资派”、“当权派”的谈判、审讯、批斗中,让他那沉稳的性格、深邃的思想和那说话的语速虽然是不紧不慢不卑不亢但却有着极其敏锐的思辩力、慑服力等众多方面的素质就不仅是得到充分展示,而且简直就是展示得淋漓尽致,使他人不得不折服和敬佩!于是,在此后无论是同“当权派”的谈判还是在批斗“走资派”的发言揭批中,只要是他在发言,不仅是所有在场的听众,就连当时那些“当权派”、“走资派”也无一不被他那提问或是揭发时严密的语法逻辑和条分缕析的推论而惊讶钦佩得刮目相看五体投地,就不得不惊呼:啊,原来孤峰公社这教师队伍中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竟有如此的人才!而这其中一个人就不仅是钦佩,更是眼前一亮,就觉得自己是继哥伦布之后又发现了一块新大陆!这个人就是当时孤峰公社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的党委第一书记童仲。在后来的“革命大联合”中,童仲书记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和理由竭力举荐邵树人进了孤峰公社革命委员会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
尽管后来有很多人对“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的邵树人能坐上公社革委会第一把椅子的位置有很大质疑,但已是县委书记的童仲在全县万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看一个干部不能看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入党,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干,而重点要看这个干部一贯是怎样做,做的是不是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不是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为邵树人减了压,拍了板,定了调,为他在孤峰公社登上一把手的位子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作为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只要能做到把“抓革命促生产”多卖爱国粮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作为历史使命去很好地完成,就一定能在县里市里甚至可以在更高层次的大小会议上受到表扬或是领上一张红彤彤的大奖状或者是锦旗!当然,身为党委书记的邵树人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每当他看着别的一把手在那隆重的场面满面春风的接受领导的褒奖而他却只能是坐在台下为他们鼓掌时,他又何尝不是带有分羡慕几分嫉妒!然而,或许是因为他的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或许是由于我们老祖宗那几千年遗传下来的“民以食为天,官以民为本”的古训过多地渗进了他这位教师出身的灵魂深处而造就了他想改也难以改掉的秉性, 加之他整年行走在孤峰这块厚实的土地上,日日时时所看到和所想到的上面那种隆重的授奖场面和农村这懒散劳动场合的极具讽刺性的对比,作为一个统管着二万多人吃穿住行的领导者,孰轻孰重,孰是孰非,他不得不沉思,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断!
他多么向往土地改革、合作社,甚至包括人民公社初期那些岁月。那时真是家家爱集体,心齐力量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是何等的高涨!然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很快就派生出一个“吃大锅饭”的怪胎,社员“上工像背纤,下工像射箭”,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就更是让人变得尖滑、散慢、懒堕,社员出工不出力,窝工、混工现象日趋严重……
那是他的学生沈幽兰亲自告诉他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春三月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到了,家家户户又开始饿肚子了。那些日子,在家做饭的老人,每到傍晚时分,就早早拿着饭箩、脸盆、簸箕来到队屋稻场,焦急等候领回大麦穗回家炒熟做饭。可那些正在田间刁割刚黄半爪的大麦穗的社员却不急不躁,一如既往地在消极怠工,男社员车水马龙般找田坎屙屎撒尿,女人除了跑茅厕,就是同男社员说说笑笑打情骂俏……此时的他们,并不是忘记了家家户户的老人正饥肠漉漉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手中的新麦回去下锅做饭,他们是要把这天上工的时间一分一秒慢慢地给消磨尽消磨完!
那天,邵树人听完幽兰讲的这个真实故事,就仰看长天,半晌无语!
沈幽兰看到如此情形,知道老师是在为人心的涣散在痛苦,在思考;她本不敢打搅她的老师,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句:“邵书记,现在的社员都是出工不出力,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为吃饭问题犯愁啊?”那时,她已完全不敢想象着那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近神话般的日子了。
邵树人似乎对这事早有思考,见学生提问,就立即回答道:“根本问题还是个劳动制度问题!
那时的沈幽兰当然不懂得这些大道理,就问:“老师,什么是劳动制度?”
邵树人就把马克思所说的“农民投入的前提就是农民的积极性,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核心就是保障农民的利益”这套几近绕口令似的高深论理不仅是连说了两遍,而且还作了详细的解释,而后才极其痛心地说:“而我们现在的劳动制度呢?不是设法去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而是鞭打快牛,干多干少一个样,社员在这样制度的驱使下,不偷懒不消极怠工那才是怪事呢!”
也就在那次,邵树人书记把他长久的思考和从小道上得来的消息综合成自己一个非常的想法而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告诉了他这位可信的学生。
“老师,这个任务能交给我吗?”
当见学生睁着那双好看的杏仁眼站在自己面前焦急地等待回答时,邵树人那个突出的喉节上下滑动了两下,还是忍住没说。
这不是他不信任这位学生,而是这种任务的落实是要担当极大风险的!
“老师,这是让我家乡的人不饿肚子的大好事,我敢干!”沈幽兰似乎明白老师迟迟不回答的原因,就再次补充了一句。
如果邵树人当时哪怕还有一丝丝别的办法,他也决不会把这个要承担极大风险的任务交给他的这位学生;但他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好办法。
“我听丁书记说过,上次你在处理陶坑那个采茶事件中,就已显示出很好的工作智慧;这个任务你当然能完成。”邵树人在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后,又提醒道:“但这次和那次是有很大不同处,这次试点可能要担当更大的政治风险!”
“老师,我不怕,我会有办法的!”见邵书记已同意把任务交给她这位刚工作不久的学生,沈幽兰高兴极了,就如童年读书时在老师面前做了个撒娇的调皮动作。
很快,邵树人在同峰亭大队书记宋群安做了一番思想工作统一了口径,将沈幽兰从方坑片调回孤坑生产队,专职负责“小段包工”的试点工作。
这试点工作原是准备在开春后启动的,不曾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沈幽兰的双亲去世了!
“小沈还有这份心思来做这项工作吗?”邵树人在去看望沈幽兰的路上还一直是极其焦虑地思考着。但当他和宋群安来到于家见到沈幽兰通过一段简单的安慰和交谈之后,他在同情之余就更是敬佩她这位学生!
“邵书记,”沈幽兰在公众场合是从来不称邵树人为老师的,“宋书记,我八婶说得对,父母在我刚出嫁就双双走了,这是两位老人在爱护我,在支持我的工作。试点的事就按原来的计划办,队里的社员会我已经开过了,开展的具体措施我已同队长商量过了!”
当两位书记一再问到在“小段包工”试点中会有哪些困难时,沈幽兰首先想到了两个人,这一个是整天不忘给自己那“两片瓦”长发抹水的刘可太,一个就是柳英;但因为柳英已是她的二嫂了,家丑不可外扬,她只说了刘可太。“没事,那毕竟是少数人,一人不拗众,我们会做好他工作的!”说过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
其实,搞试点工作的最大难度远不止刘可太和柳英这两个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沈幽兰当然一时还不知道,那就是金霞金老师。
上一章
下一章
声明: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授权后转载须注明出处:"转自华语剧本网 www.juben.pro"。 [ 如何申请转载 ]
登录 后再戳我哦